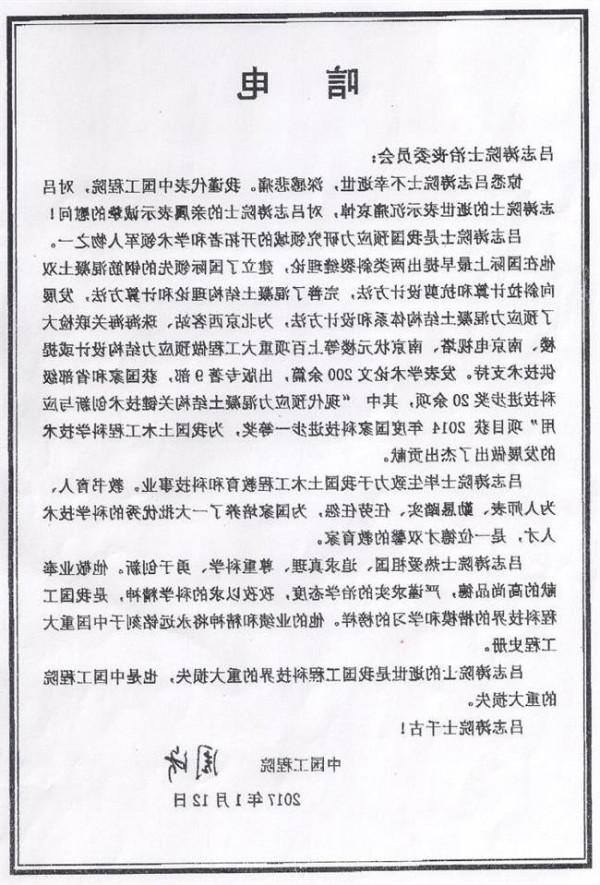朱光亚是什么学家 文革时红卫兵抄朱光潜家:看到什么就拿什么
核心提示:抄家更是家常便饭,红卫兵就不用说了,就连街道里的老太太也到我们家里抄家,看到什么就拿什么。我们家房子本来挺多的,那时候也住进了很多跟我们根本不相干的人。
本文摘自《在不美的年代里 》 作者:陈远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人物简介: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我国现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早年接受中国传统?育,1918年,考入香港大学教育系,1925年冬,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哲学、心理学和西方艺术史,最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以论文《悲剧心理学》获得法国博士学位。
193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从1946年冬起到1986年逝世以前,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美学和西方文学。
朱光潜的学术成就主要在美学领域。重要著作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和《西方美学史》;译作有黑格尔的《美学》、克罗齐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
这些论著和译作对奠定我国美学研究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朱光潜还写有《谈文学》等讨论文学写作和翻译技巧的论文集,以内容丰富、深入、切实、文笔流畅、易懂,深受读者喜爱。
口述:朱世乐
父亲当时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话,在共产党的眼里他当然是反动的;但是要走的话……
在别人看来,父亲是更有理由离开大陆选择到台湾去的,很多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留下来。这种选择,我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我患骨结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厉害。那时候对于那种病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是用链霉素来治疗。
链霉素都是进口的,很难买到,也很贵,一支链霉素相当于一袋白面的价钱。别人说:也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我才能够存活下来,一般人家,得了这种病都医治不起(作为教授,父亲当时的工资是很高的)。医生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移动。
就这样,父亲和母亲想了半天,觉得我的身体不行,受不了旅途的颠簸。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蒋介石派了飞机接一些教授离开北京,其中包括父亲。父亲当时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话,在共产党的眼里他当然是反动的;但是要走的话,我的身体又?一个问题,同时,他也不愿意做寄居在别的国家的"寓公",另外,共产党也派了一些地下工作者动员父亲留下来,说他会有很好的前途。当时的很多人都被动员过,包括沈从文伯伯。
就这样,父亲留了下来,留在北京。那时候,父亲经常跟沈伯伯一起从鼓楼旧市买一些小瓶小罐回来,回来的时候,沈伯伯总有礼物给我:"朱世乐啊,我给你带了一个小瓶子回来。"那些上面刻着龙或者别的花纹的小瓶子,给了一个固定在石膏床上不能动弹的小孩子很多的欢欣。后来他们每次回来,我都要问沈伯伯:"给我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解放之后,父亲成了各次运动当然的"运动员",我也曾经问过他:"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对于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你应该负责的,那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但是我体会到,如果当时他选择去欧洲的一些国家,生活得也许会好一些。
1993年,我到德国进修基因诊断,为了更多地了解父亲,我曾经沿着父亲在欧洲走过的足迹去游历。在那些地方,我遇到了一些父亲过去曾经共事过的老学者以及知道他的青年美学家,他们得知我是朱光潜的女儿之后,都热情地招待了我。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对父亲另一方面的印象:一个很好的知识分子。
在我的脑子,只有那张没有得到的电影票时隐时现……
我1942年出生,解放的时候我七岁,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沙滩。父亲在沙滩的灰楼里上班,那里还有一个民主广场。有的晚上,民主广场会演电影:挂一个幕布,两边都可以看的那种。就是这样的电影,也是要票的。到了演电影的时候,哪个小朋友有票,都会让其他的小伙伴羡慕不已。
我们在一起议论着谁谁有票了。但是我总是没有票,有一次,小朋友们在议论的时候,我说:"我也想去啊,我爸也没给我拿票!"他们对我说:"你爸还给你拿票呢,他站在四个桌子上呢,他顾不上给你拿票。"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站在四个桌子上"。后来我大学毕业,在北大生物楼后面的墙根底下接受毕业教育。我们开会的时候,看到造反派正在一片空地上批斗陆平,让陆平在太阳底下晒着,七八月份下午三两点的太阳很毒,我看到陆平的脚下,汗水流了整整一圈。
我想,怎么可以对人这样呢?实在是有点残酷。突然,我想起了小时候我曾经羡慕过的别的小朋友的电影票,还有父亲的"站在四个桌子上呢"!这两件看起来没有联系的事情,那一刻在我的脑子里凸显的十分清晰。不过在那个年代里,我又敢说什么呢。
50年代美学界对父亲大围剿,对他的美学思想进行清算,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十分深刻,在我的脑?,也只有那张没有得到的电影票时隐时现。我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受到批判,只模模糊糊地知道:父亲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搞的美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唯心主义的鼻祖。
父亲说:"这次大概把我漏了吧。"
"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上中学。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伟长一家的遭遇。钱伟长的夫人孔祥英,是我们清华附中的校长。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北大,当时没有公共汽车,每天走路往返,中午就在学校的食堂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