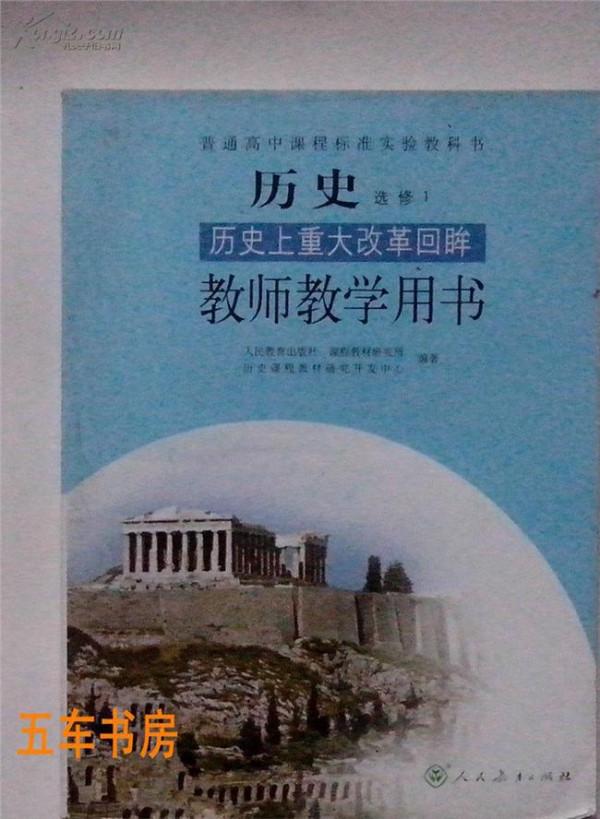韩少功自选集 看70年代人的阅读世界:摘自韩少功《漫长的假期
看70年代人的阅读世界:摘自韩少功《漫长的假期》 从 萧三郎 作者:萧三郎 三联书店出版的《70年代》一书中,韩少功有一文章《漫长的假期》,我很喜欢。文中谈到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 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
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正如现在,我们身处康乐时代,却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因为那可能成为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一代人的漫长历史假期早已结束。 1.谈到读书,韩少功有次在大学讲课,顺便做了次读书情况调查。结果是:读过三本以上法国文学的?(约四分之一学生举手)读过,《红楼梦》的?(约五分之一学生举手)看过,《红楼梦》电视剧的?(略过半数)。
这还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调查结果。 2.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
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韩少功带的是《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 3.“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
这是指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两百多种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类书目里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的女儿等都是知名异端。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于文学方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凯鲁亚克)、《厌恶》(萨特)、《局外人》(加缪)、《解冻》(爱伦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1972年“皮书”恢复出版,虽限于“内部”,但经各种渠道流散,已无“内部”可言。
加上公开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一类,还有《摘译》自然版和社科版两种杂志对最新西方文化资料的介绍,爱书人都突然有点应接不暇。 4.韩少功回忆起1967年秋漫长假期里的偷书故事:“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
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看,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直到多年以后,韩少功读到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才似乎觉得有些眼熟,依稀记得那闷热年代图书馆里早已和这些阅读不期而遇过。
5.那年代,图书在黑市交换。比如一套《水浒传》可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
有一次,高二某同学徐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赫鲁晓夫主义》,书传到韩少功手上,还没读完就不翼而飞。书的主人急得差点要撞墙。韩少功提出赔他一本巴金的《家》,他不要;赔他《安徒生童话集》,他也要;赔三大本邮票,他还是不要。
百般无奈之下,韩少功只好把一只手表戴在他手上,暂时安抚他痛苦的心。 6.红卫兵们爱诗。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 7.插友里有一工人胡某,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韩少功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
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大家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
8.还有一位去江西省插队的青年,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案,他坐牢两年多,但他在监房里还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学英文的办法是,找一本词典,每天背下一页,就撕去这一页,待整本书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