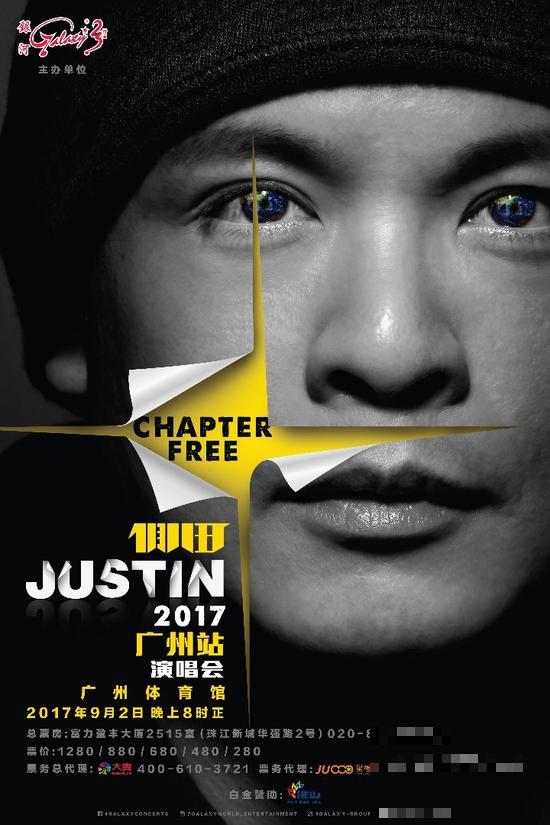林风眠冯叶 冯叶:回忆我的父亲冯纪忠义父林风眠
那个冬天,电视台采访,隐隐约约,北大门在暮色中挺立,回首而望,宋代方塔秀拔。曲折漫长的甬道上,苍苍老父独步,向我、向我们、向广场前行,一步步、一步步。多少年的坚持、多少年的信念、多少年的风骨,离我更近更近。
这个冬天,我亲爱的爸爸,已经离我远去。但是我是多么希望您能伴着我再次走进“方塔园”,说说怎样以宋代“甬道”之“势”,贯通整个园区,以自由表达个性的“何陋轩”现代设计理念“与古为新”的啊!
坐在“何陋轩”内,周围高高低低,独立又谐和的弧形挡土墙上,光影不停地变动,带我进入往事的隧道……
小时候特别多病的我,真没让人省心。天黑了,您气喘吁吁地赶来幼儿园接我,气喘吁吁地回家煮热晚饭,气端吁吁地带我看病,您喂我吃药的焦虑样子至今仍未忘却。每天清晨六点,总是您轻轻的离家关门声唤我起床上学。因为我常生病,我们只能住在离大医院近些的市中心,可是您却每天要挤换两辆公交车上班,路上少说也要一个小时,您试过让人挤伤肋骨,试过被推下车,重重地倒在离头只一两厘米的石柱旁。
每年总有那么多次,炎夏隆冬,你带学生下乡劳动做农活,做毕业设计,次次两三星期,您说其他教授有的年纪大了,有的身体不好,可是您心脏也有病啊!年少的我看着瘦瘦的您背着铺盖摇摇晃晃地出门,又要去挤车了,总是有着莫名的恐惧和担忧。
后来您晚年深受类风湿关节炎之苦,虽说是与1965年“设计革命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中受的折磨有关,但这么多年来的辛劳应该也脱不了干系的吧。不过再怎么样,您都不在我面前说个累字,没有任何抱怨。总是和颜悦色地听我叨叨一天的琐事。
记得那年才六、七岁,看到弄堂里其他小朋友在养蚕,也买了几条回家。又不知放哪儿好,找了个瓶子就搁里头了。您看到后说,这样不行,蚕宝宝带来了就要好好照顾,又告诉我该怎样辨识我家院子里的桑树,怎样清洗桑叶。第二天下班后您买了些硬纸板回家,听我妈说,那晚您没怎么睡。
清早,我一睁眼就看到了一只白白的、漂漂亮亮、简简洁洁,形似一片树叶,上面还有着透气小孔盖子的大盒子。您对我说,因为我的名字是叶,所以就做了一片叶子给我,让蚕宝宝们有个好好的家。
我的蚕宝宝后来都结成大大白白的茧,又都变蛾飞走了呢。您教会我尊重生命,也让我知道生活中的美,直到今天,那只漂亮叶型盒子好像还在我的眼前。那一年应该就是您写《空间原理》的一年,也是您在带学生下乡中因营养不良,过度劳累得了浮肿病的一年。
后来我们搬了去离我义父林风眠家近些的茂名路,在厨房的破旧小桌上,您又渡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每次上大课前,等我们都睡下了你才走进厨房备课,“不能总是讲同样的内容,要有新的突破”。半夜醒来的我,总看得到门缝下的光漏。
为了怕迟到,“让学生们等”,彻夜未眠的您 5点多就出了门。这是自1947年回国后,由当年考试院核准,在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就担任正教授多年的您,对教学的认真。这般对学生的爱护之心,”文化大革命”磨难,也未浇灭您的热忱,只要见到学生,您还是笑得特别灿烂。
那年我三岁,您正想着替我妈妈找一位深造的绘画老师。就在那时,儿童读物“小朋友”封底刊登了义父林风眠老师的一幅画。您当即决定,妈妈应该拜他为师。那时您已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而义父却迫于无奈辞离杭州教授一职,家属亦都离沪,沉寂多年。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上南昌路义父家,我就滑倒,摔了个大跟斗。而他回访同济新村我们家那次,据说我当他的面重重摔了玩具钢琴,以示不满。这件事后来总让他当成笑话,说我坏脾气。谁想到他会这么疼我,认我做义女,又教我画画呢?
只要没有旁人,每次您上义父林风眠家里,他都拿出刚画的,平时不让人瞧的画请“纪忠先生讲讲看”。而我渐渐地从在您们身边转来转去的小女孩,长大到可以安安静静坐在一旁看画旁听的十一二岁的大姑娘了。元旦前夕,你们也会开瓶酒,买几碟熟菜,一盒蛋糕庆祝。那时我也能分到一小杯酒,说是祝杯之用,我也喝了。现在想来,爸爸妈妈义父和我四个人一起过的那些个节日是多么的开心啊!
其实那些年,我还小,不知道,最辛苦的是一直坚持不加入任何政治党派,只做学术的您。只要一来“运动”,身为建筑系系主任的您就会首当其冲,受到批斗,从“内定右派”,到1965年的“设计革命化运动”,同济建筑系索性硬生生派人去拆已经建成的杭州花港茶室,说是这房子有“封建思想”,七零八落地重造,接着又把一顶浪费国家财产的污名扣在您的头上,唉,相煎何甚那。
逼您去工地,去乡下劳动,不让您教课。所以难得在义父家一起贺节看画的您,心中的愁苦,大概也只能在我们一家团聚,在林风眠的画中,在三五好友的艺术探讨中忘却吧?
转眼就是1966年,您让人侮辱了、折磨了,打伤了、义父林风眠平时只拿给您看的那批画,我看着他一张一张亲手毁了、我们两家同天同时被抄家了、我生肺炎了、您给关进学校隔离了、一关就是八个多月。义父突然被抓进冤狱了……我大表伯没了、傅雷伯伯没了、我叔叔没了、我舅舅没了……
义父林风眠被抓后,妈妈和我急得到处找人帮忙打听。天冷了,听说只穿汗衫短裤进牢的近七十岁的老人怎么过。后来看守所寄出了凭单到我家,我们才能在指定日子里凭这封信进去送日用品。差不多一个月也只能有一次。那时除了审问他的外调人员,没有家属可以同里面的人见上面,没有凭单也不能随便送东西进去的。
过了好久,您没回家,义父也没放出来,除了我大姨偶尔偷偷上门关心关心外,就只我们娘俩在家企盼你们的平安了。妈妈腰闪了,日夜不能眠。十三四岁的我只能照着书本给她整晚地推拿、拔罐、艾灸。又过了些日子,我们去打听的时候,有人轻轻地告诉说义父的案子“很严重”,是历史问题。
还有人好心地劝说,千万不要再去送东西了,会惹祸上身的。妈妈病了,崩溃了,发髙烧。到了送东西的那天,她实在去不了了,也不放心让我去,“或者少送一次没有关系的吧”。那天幸亏爸爸您回家了,我很少看到您发这么大的脾气,您坚定又大声地说:“他们胡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我绝不相信林先生有什么历史问题!你们在家,我去送!”就这样,您去了第二看守所送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段时候就正是义父由一所转到二所后,专案人员上私刑逼供,反铐他双手,逼他签字,逼他承认莫须有“罪行”最厉害的那几个月,不是爸爸您的坚持,不是您凭着建筑师的洞察力,凭着对一位朋友、一位艺术大家的无限信任,有谁能这么肯定一位相识时已经五十多岁朋友的过往历史呢?在那段最受折磨的日子里,义父说他清楚地记得就是那天,盼啊盼,比平时晚了好些时候,东西才送到,看着我替他缝的衣服上歪歪斜斜的针脚,终于放下心中的石头,知道大家都活着。
他在冤狱的四年多里,我父母没有中断过一次往牢里送东西。
好不容易”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义父离开了上海,没多久写信要我去。一年后在您支持下我去了香港,那时哪像如今这样来去方便的,又没视频通话等,真有些生离死别的感觉。您和妈妈当时只能送我到广州,连深圳都上不了。
您深深地叹着气,紧紧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让我不要哭。多少多少年后,与学生的访谈中,我才知道,当时您的心中,是怎样地满倘着血啊,您说道,“女儿走了,就像挖走了我心头的一块肉”。亲爱的爸爸,现在我更明白这种感觉了,您走了,我的心彻低碎了。
那年冬天,您漫步开阔广场,小草从石缝间探头,像是听到了莫扎特长笛的呼唤,为初冬带来几分绿。大大小小的石块,灵活有致的台座,您是以思念远方的女儿,您的掌上明珠之情,托起了宋塔,托起了明壁,托起了古树吧?照壁的横、方塔的竖,堑道的曲、水面的阔、草坪的广、方塔的静、“何陋轩”的动,恰如您所爱的巴赫赋格曲,沉着大气、和谐有致、诗意盎然。
那年的冬天,天公作美,大雪封园,为协助策划“冯纪忠和方塔园”展,我拖着脚架,背着相机,抱着手提录像,独自穿梭在皑皑白雪里,巍巍宝塔宁肃,枝头压雪不屈,竹林伏地不折。方塔园里,黑白显明;何陋轩内,时光冉冉,自由的高低弧墙,优雅地各安其职,未失个性。空间与光影,随着时间流逝默默转动,松江旧民居沉重的庑殿顶的变奏, 缓缓漂浮、升华。我的“意”,融入于自然,相忘于静寂。
亲爱的爸爸,冬天又来了。义父走了、您走了、妈妈也走了。什么时候再能像往时一样与你们喝一杯酒,听您说一段古、念一首诗、唱一首曲、赏一幅画呢?
人生中的眩丽不再,只留下凝重的墨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