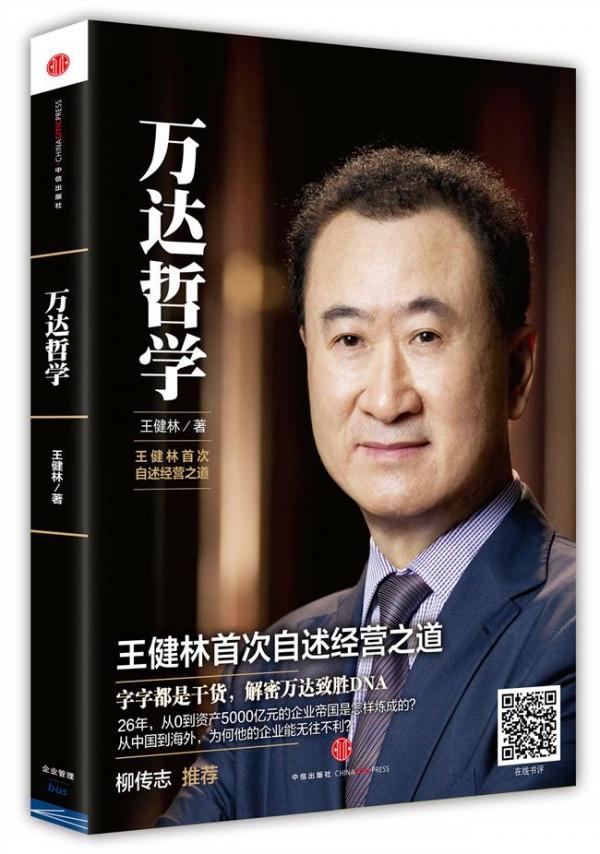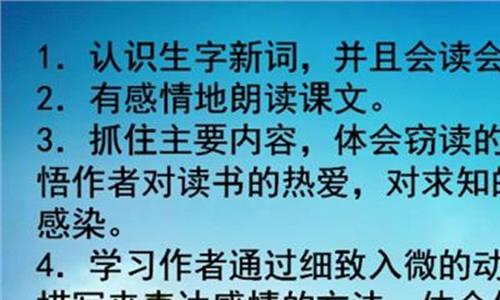陶东风读天鹅绒监狱 陶东风:读《天鹅绒监狱》
匈牙利作家、思想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用“天鹅绒监狱”来描述斯大林模式支配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在上世纪70年代(一般被称为“后极权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及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正是最恰切不过了。
这个美妙的“天鹅绒”与可怕的“监狱”组成的带有悖论意味的新词,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天鹅绒监狱仍是监狱,有一般监狱的特点,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禁忌之地;但它和一般监狱不同,有精美舒适的天鹅绒表层,而不是裸露粗糙的钢精水泥,因而让很多人觉得安全、温暖和舒适。
它是监狱却仿佛不是监狱。然后,“我们躺在天鹅绒上一起脸不红、心不跳的说谎,一起其乐融融的表演。这些谎言是新的黏合剂,让这本已脆弱的监狱更加牢固。”本书对后极权时代的新闻检查制度、文化的国家化、政府与艺术家基于利益基础上的共谋等问题作了深刻而独到的剖析。
在言论自由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没有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会反言论自由、为新闻检查辩护(想想马克思的那篇批判普鲁士新闻检查令的著名文章)。新闻检查制度不仅已经臭不可闻,而且常常因为人的逆反心理而产生自我挫败的效果,即所谓越禁越香,越禁越流行:你越是禁止什么,我就越是相信什么。
你说形势一片大好,那情况一定是糟透了,糟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了。由此,有些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审查制度是一枚‘徒劳且有缺憾的’武器,它的使用会反过来促进那些它原本着意防止的事务。”
但《天鹅绒的监狱》告诉我们:到了“20世纪的社会极权主义”时代,情况已经不是这样简单了。因为审查制度也在升级换代、与时俱进,甚至成为了一种所谓的“新审美文化”——准确说是一种“新审查文化”。本书作者开宗明义地说,这个姑且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就是他的《天鹅绒监狱》探讨的主题(尤其是此书第一章“无伤亡的审查文化”)。
旧审查文化是刚性的强制文化,是审查者与被审查者激烈、公开对抗的文化;与此不同,新审查文化不再表现为国家对文化、对作家和知识分子言论的单向粗暴的干预,不再是“批评家们所反感的那种审查形式”,而是一种审查者和被审查者沆瀣一气、密切合作、互利双赢的文化。因此,真正值得探讨的,是“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观察。
新审查文化的特点首先是:这是一种看上去不像是新闻检查的新闻检查,不像统治的统治,不像极权的极权制度,是极权主义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哈拉兹蒂指出:“我宁愿不把这种文化刻画为一种审查制度,这么做会掩盖其新颖性。
正确的理解是,我们的审查制度形成了一种意在根除审查制度的自相矛盾的文化。”“我们的新文明,不仅与真正的艺术自由精神相背离,而被认定为与自由背道而驰的传统审查制度亦是相距十万八千里。”“只有当新方法不奏效时,过去的粗暴方式才得以启用。
”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也指出,后极权社会的“(思想)审查不再是由笨拙的政治机构来进行,而是成为艺术家、读者观众和政治人员共同参与的合作结果。这是一种‘进步了的审查’”。
新审查制度具有柔性特征,它不再是赤裸裸的暴力压迫,“不再是单纯地迫使反对者噤声,而是确保知识分子更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知识分子较之从前感觉要松快许多。”他们即使在诉说在体制内的“不幸遭遇”时,也显得无比快乐,因为在另一个意义上,他们就是这个新审查制度的受益者。
他们一边诉说自己的“不幸”,一边又极其自觉地审查自己的观点是否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并无比积极、夜以继日地填写各种表格,申报国家资助的项目和奖励。因此,这种新制度“更隐蔽且更危险”。审查者和被审查者达成了统一战线,两者之间的“共同利益”意味着“审查制度不是简单的文化创造着的镇压场,而是他们天然的家园。”
这个把统治者与知识分子捆绑在一起的基础是什么呢?是赤裸裸的利益。在后极权时代,那些热衷于官方荣誉(奖励、项目课题等等)的知识分子真正看重的不是它的学术含金量(谁都知道它并不代表真正的学术水平),而是它附带的各种利益,特别物质利益。
从而,新审查文化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奖励达到惩罚的目的,通过物质刺激达到精神控制的目的,通常情况下,它的惩罚是悄悄的、不见诸媒体的,而奖励则是大张旗鼓的。它对文化创造的干预常常是通过所谓“扶持”表现出来的。
因此,哈拉兹蒂写到:“我谈到的不光是惩罚,也包括奖励和支持,特权和雄心”,“吸引我的不只是制约艺术家的种种外在规定,我更关心的是拽低艺术家想象力,使其不断沉沦的地心引力。”
众所周知,相比于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国家对文化和艺术是极端重视的,它把文化艺术纳入计划积极扶持,把一批艺术家(当然是听话的艺术家)包养起来,它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繁荣文艺。哈拉兹蒂写到:“艺术品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蓬勃发展。
东欧历史上从未展出过如此之多的艺术作品。文化馆,电影制片厂,剧院,还有艺术家殖民地处处爆满,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而“让人难以忍受的事实是,在这个无懈可击的审查制度下竟然没有一个艺术家拒绝过任何来自国家的荣誉或嘉奖。”“没有一个”说的有些绝对,但是大抵符合事实。
新审查制度通过物质手段解决精神问题,通过金钱手段解决思想问题。事实证明,通过非思想、非意识形态的方式解决思想和意识形态问题,常常效果更好。一方面是不讨论,不争论,不搞大批判;另一方面是撤职,降薪,不让你分房子和评职称,停播禁演,吊销书号,直至撤销出版社或杂志社。大约正是因为服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获得极大的附带利益,这种胡萝卜加大棒、恩威并重的新审查技术把无数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引入瓮中。
新审查文化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无耻:挂羊头卖狗肉,打着“自由”之名行专制之实。哈拉兹蒂语带讥讽地写到:在原始极权社会,那些老牌的审查官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可以通过吹嘘为文化自由而战的斗争,来为自己的镇压行为正名”。
而现在,“审查官吸收了被审查者的意识形态,暴徒学会了其受害者的语言”。这种无耻的具体表现,就是后极权国家的新闻检查行为即使与它自己的宪法也是抵触的:它的宪法里公然也写着保护“言论自由”。由此导致它的新闻审查具有秘密性、不公开性和非法律化特征。
我们看到的不是明确公布的关于新闻检查的法规条例,而是临时不公开下达的指令,或者电话通知(而且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嘱咐“不准记录”),一般每周传达一次。这些禁令只有业内人士知道而没有文字的东西(这也是学者们研究新闻检查制度常常觉得资料困难的主要原因)。
之所以采取这样类似特务活动的方法,原因在于这些检查制度没有法律——即使是自己的法律——的依据,不合法。
于是我们看到,与极权主义时期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迫害“反革命分子”不同,后极权时期对于异端思想者的打击常常是悄悄进行的,而且是以非政治、非意识形态的名义进行的。“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成为被批评者‘扩大社会影响’,使得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徐贲)
第四,由于规则不透明,由于潜规则比显规则更加重要也更加随意,后极权社会的新闻审查常常通过作者或出版者的自我审查、“自我把我”来完成的。自我审查的基本标准是不能涉及“敏感”问题。至于什么是“敏感”问题,常常没有明文规定全靠大家“心里有数”。
因此,在后极权社会中,大家过的是“心里有数”生活,许多事大家心里明白,只是不能说。那些媒体工作人员由于不能准确把握“什么不能说”,大多数人会出于“安全”考虑从严掌握。
也有少数人会试探“极限”,在试探过程中尝试着打“擦边球”。这两种趋向往往会形成两类媒体工作者的差别,从严掌握者是“吃得开的”或“能混的”,打擦边球者是“不识时务的”甚至有被视作“异类”的危险。“心里有数”是所有后极权时代知识分子都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
最后,新审查制度的第五个特点就是犬儒主义:这是通过非思想的手段解决思想问题的必然结果。审查者和被审查者都是这样的犬儒主义。被审查者不是因为不相信某个观点而放弃这个观点,而是因为坚持这个观点就会评不上职称;也并不是因为相信某个观点而主张这个观点,而是因为这种主张可以涨工资提职称。审查者也同样如此,他们大段大段地删除的“敏感文字”或许正是他心底里欣赏和认同的。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指出,意识形态的假面化、虚伪化、装饰化和表演化是后极权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哈维尔在他的《无权者的权力》中通过一个蔬菜水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在洋葱和胡萝卜之间放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案例,对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哈维尔问道:他为什么这样所做?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他真的热心于联合全世界无产者么?这个伟大目标和他的日常生活、和他的水果店的生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哈纬尔的回答是:“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的水果点经理从来没有思考过他帖在窗户上的标语,它们也不是用来表示他们的真实想法。
”那么为什么仍然还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是“上面”的要求,是大家都遵守的规则,是虽然滑稽但是却不能不例行的公事,“如果他想拒绝,这可能带来麻烦。
”他就会因此而被指控不忠诚,更重要的是,他的日常生活就会因此而受到牵连。这样,已经不被人们忠诚信奉的意识形态,虽然已经装饰化,但是却依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们的生存已经存在密切关联。
水果店老板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想生存就必须这样做。” 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效忠是实用主义的,它是一个“挡箭牌,保护硕果店的经理免遭潜在的告密者”这保密意识形态不在是通过它的逻辑力量或道德感召力赢得人们的信奉,而是通过它所携带的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力而迫使人们表示服从。
在此,表示效忠(帖标语)已经成为纯粹的表演,但是却又是不能不反复进行的表演。水果店老板的标语的真实含义(我是一个听话的顺民)与它表面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经完全没有关系。虽然已经没有人相信,但是却不能不装模作样地表示效忠——因为它与生存之间的深刻联系,这解释了后极权时代意识形态的另外一个基本特点:人们是出于利益的计算服从意识形态,他们对意识形态没有信奉但是却非常畏惧,但是服从意识形态却使得人们。
正如哈分析的,如果不维持这种谎言,如果水果店的老板直接说:“如果说极权主义时代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效忠是发自内心的(虽然从根本上说是被欺骗的或被实施了催眠术),意识形态通过征服人们的心灵信仰而发挥控制作用;那么后极权时代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效忠就是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而迫使人们接受(或者至少不公开对抗)。
这表明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采取犬儒主义的方式加以应付。
他总结说:“意识形态是与世界联系的华而不实的途径。它给人们提供那种有关身份、尊严和道德的错觉,同时更容易地将他们和这些东西分开来,作为某种超个人的和客观东西的储藏所,它使得人们既向世界也向自己欺骗自己的良心,隐瞒自己的真实地位和他们不光彩的‘权宜之计’。它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又是给那些合法地存在于各处的东西表面上夸大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