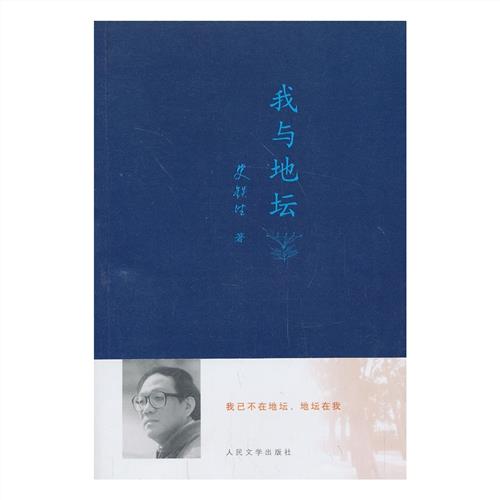史铁生我与地坛 从《我与地坛》中看史铁生对于生命的深思与求索
“汗水倾泻过的本地不容丢掉,我常常觉得这是我的姓名的昭示,让前史铁相同的生着,以便不断地去看它,不是不断去看这些文字,而是凭借这些踉跄的足迹不断看那一贯都在写作着的心魂,看这心魂的或许与去向!”这是闻名作家史铁生关于自个姓名的解说。
在中国当代文坛里,史铁生无疑是最具有哲学思维的作家之一,他以其特有的朴素平平的文风、勤勉敏锐的思索、广博宽厚的胸襟和最真挚的言语表达哲学思维,闪烁深邃而清澈的才智之光。他的散文《我与地坛》体现出一个鲜活的生命在面临磨难时对人生的殷切考虑,包含着作者个别生命的共同领会。他刚强地上临实习生计窘境的自觉认识和勇气,使他的散文散发着共同的哲学魅力。
就个别生命而言,史铁生的终身无疑比常人承受了更多的磨难。他于1951年出世在北京,往后便阅历了动荡不安的“文革”期间,1969年18岁的他前往“延安”插队变成一名知青,不到三年便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厄运突如其来,他在“最傲慢的年岁上遽然残废了双腿”,在这么沉重的冲击下,他找不到作业,也找不到别的将来,从此如断翅之鸟般没有期望,只想着一个字“死”。
他摇着轮椅,来到“为一个魂不守舍的人把悉数都预备好的地坛”,“一连几个小时专注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相同的耐性和办法想过我为何要出世”。
他在这座历经400年沧桑的古园里取得了生命的启示,“窥看了自个的心魂”,并在“生与死”的考虑中深入领会到了“生命存在的含义”,并认识到人生即是向死而生的存在,所以要“活”,而且“有含义的活”。所以,他“带着簿本和笔”,“找一个最不为人打扰的旮旯”,将这些生命的感悟记载下来,发明了《我与地坛》。
可是,通观《我与地坛》,作者并没有由于自个的厄运而深陷于苦楚当中无法自拔,也并没有由于磨难的摧残而挣扎、嗟叹,反而是像地坛通常安静、安然。作者像一个安静的旁观者通常,在地坛古园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静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喧闹理一理缤纷的思绪,去窥看自个的魂灵”。
他将古园的“石门”、“落日”、“雨燕”、“冬雪”、“古柏”、“草木”,这些天然生命的物象都看遍,领会着历经四百多年的陈旧地坛、古殿檐头脱落的玻璃、门壁上淡褪的朱红与坍圮的高墙玉栏,这些地坛生命的改动痕迹与大天然的作业规矩,领会着这儿的风霜雨雪、四季轮回。
这悉数景象被在史铁生的笔下看似寒酸、历经沧桑,却饱藏了生命的生机与生机,充溢了情感与意蕴,在娓娓道来的描绘中让人感触到了生命本真的无穷与奇特。所以他说,由于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个的命运。
残损和磨难或许是人类的不能承受之重。可是史铁生说:你能够诉苦天主何故要降请多磨难给这人世,你也能够为消除各种磨难而斗争,并为此享有崇高与自豪,但只需你在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苍茫:参加国际上没有了磨难,国际还能够存在吗?一个失掉不同的国际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肥力的沙漠。
或许这国际的存在自身就需求磨难吧,这么想来,磨难也变得顺其天然,承受也变得顺其天然。那一对从中年到晚年的配偶、那位不断挂着扁瓷瓶喝点酒的老汉、那个坦率扑鸟的汉子、那个天天穿过园子上班的中年工程师、那位命运欠安的不断参加却不断绝望的长间隔跑兄弟,与作者一同畅怀痛骂又相互叮咛“先别死,再试着活一活”……作者仔细查询并描绘这些实在的生命存在,看着他们的生命改动,从这些不相识的游人、兄弟当中领会着生命的含义。
好像是在通知我,悉数都是那样出其不意,又在意料当中,或许这即是生命的实在的当地与含义地点:它持久是条单行线,咱们已然走过就不能回头,可是关于将来咱们还有持续挑选的权利和机遇,咱们需求做的即是坚持不扔掉,而且让它变得更有含义。
记住在上课的时分,胡山林教授从前讲过:“人生道理深含于人生景象的最深层,或许说矗立在人生景象的最高处,窥破了人生真恰当然是高兴的,但通常也是苦楚的”。地坛的四季轮回、人世世相以及无穷的母爱,使史铁生“死而复生”,感悟到生命存在的含义,这是一个苦楚的进程可是也是一个不断逾越的进程。
死是个霎时刻的事,生却要漫长得多、弯曲得多,是更高一层的精力探求。夏尔·杜波斯曾说: “人的确是一个场合,仅仅是一个场合,精力之流从那里经过和穿越”。史铁生并不是阿Q般的自我安慰,而是将最实在的苦楚与感悟放在心里,让它们跟着时刻穿行,可见他面临磨难、承受磨难的勇气与意志。
终究,他说,我来的时分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想法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国际变马上成了不要命的恋人,而对一个恋人来说,不论多么漫长的韶光也是少纵即逝,那时他便了解,每一步每一步,正本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
他说,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他说,当太阳平息着走下山去收尽凄凉残照之际,恰是他在另一面焚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他说,世界以其不息的愿望将一个歌舞炼成永久。
这些都浸透他对生命的不灭的期望与酷爱之情,他将人生的各种顺境或意外都融入永久,将生命的进程描绘的触目惊心!然后动情地诘问:“当然,那不是我。可是,那不是我吗?”他将个别融入整体的生命当中,将生命归入永久当中,这是多么阔大的境地与胸襟。
史铁生以其残损的身体在《我与地坛》中探求着生命存在的含义,在苦楚当中感悟到生命永久之光芒,将精力的自我救赎与生命的永无止境联络到一同,使自个的磨难变得缺少为道,对意外的承当变成了生命体的自我逾越,作者因生命的存在而满怀希冀,并不舍地探求,这种心里改动让人震慑,“生”也因这一份坚决而变得恒远漫长,扣人心弦!( 河南大学文学院 葛明媛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