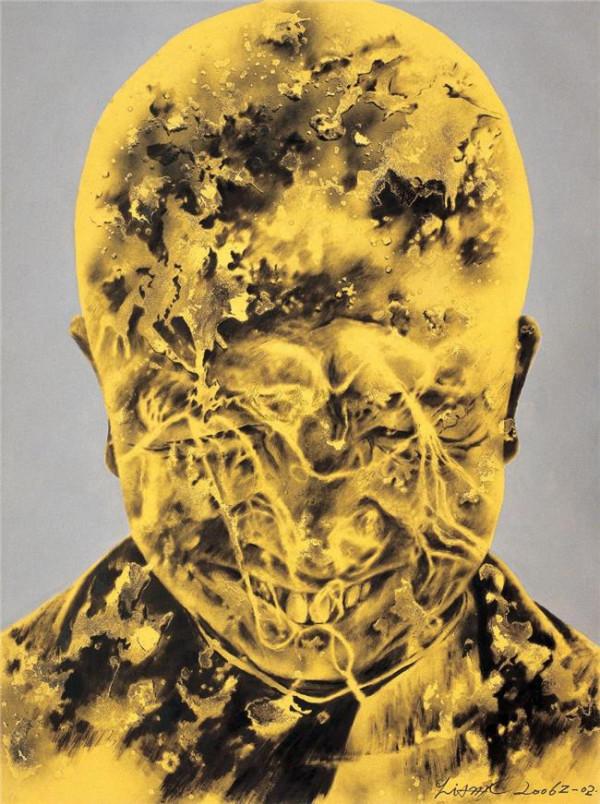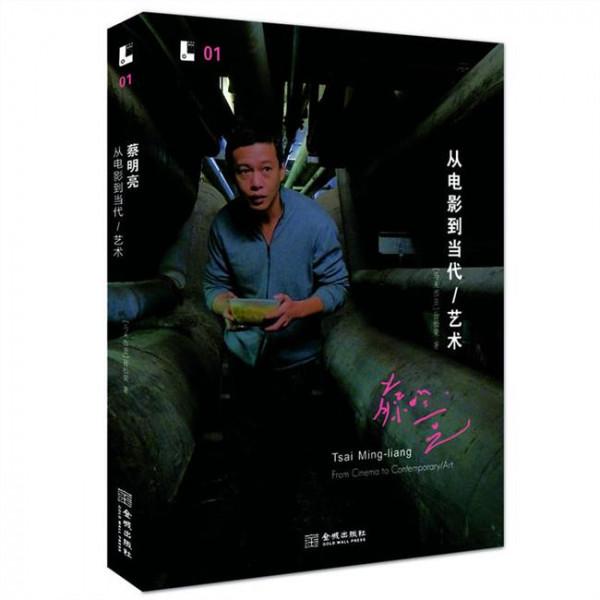朱彤台湾 台湾《当代艺术新闻》专访邱志杰、左靖、朱彤
《当代艺术新闻》:能否介绍一下此次三年展的缘起与背景。
左靖:2002年9月,第一届中国艺术三年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办,策划人是彭德和李小山。这既是中国第一个三年展,也是唯一的一个由民间资本投资的,仍将按时举办第二届的大型综合性展览。投资人葛亚平先生自1990年代末开始介入当代艺术的展示与收藏工作,其创办的南京红色经典艺术馆在这几年的当代艺术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荦荦大者,就是成功举办第一届并积极筹办这届三年展。
中国艺术三年展作为一个日趋成熟的大型综合展览,它在自己不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主要关注当代艺术的本土化进程,参展艺术家限于海内外的华人,不妨可以把它说成是在走另一条国际化的路线。
第二,它是一个漂流的三年展。首届在广州,这一届放在南京。
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三年展将在不同的城市间漂流。第三,它是一个民间机构投资的展览,而国际上的双年展、三年展一般来说都是由政府投资的。这次展览投资方将承担所有的费用,并且给艺术家提供一定的创作经费。
《当代艺术新闻》:本届展览的策展人是如何选定的?
左靖:策展人的选定,其间经历了一个过程。由于我本人一直参与三年展的策划工作,包括第一届和这届。2003年底,在投资人葛亚平先生与我及其他一些策展人经过反复讨论与协商后,我们确定本届展览的核心是全面推介年轻一代艺术家。
这也是基于 1990年代中后期,生于1960年代底以后的青年艺术家们开始浮出水面,作为新世纪中国新型青年文化的一股复兴力量,他们正以暧昧复杂的多元化面貌,在视觉艺术、文学和音乐等领域,书写着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全新章节。
在策展人与艺术家关系上,比如历史记忆和生活境遇等方面,我们也想寻找一种时间上的趋同性。所以,在策展人的年龄上,我们认为必须年轻化,我们邀请了南京本土的新锐策展人朱彤先生,以及在当代艺术创作、写作及策展三栖均极为活跃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邱志杰先生加盟。
这样,就由我们三人组成了策展小组。我和朱彤生于1970年,邱志杰是1969年的,这可能也是所有双(三)年展最年轻的一支策展团队。
《当代艺术新闻》:此次三年展的入选艺术家的年龄段段定在68年之后出生,请问年轻艺术家是否足以代表当代艺术的发展状况?代群的区分对艺术创作有根本性的影响吗?
朱彤:当然,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年龄底线了。我个人认为不应该过多的对于定在1968年这个年龄的底线展开过多的想象,其实定在1968年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并不十分彻底。虽然1968年这个年龄线还是略显保守,但很多这个年龄段出生的艺术家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艺术家,他们当然已经活跃在国际当代艺术舞台上,但是把他们放回到中国的代际语境中来解读依然是意味深长的。
稍年轻的一代的很多人仍然为了艺术理想和生存而奋斗,但是他们在艺术上的那种开放性、尖锐性和活力正在日渐闪现。
就这个展览而言,我们并不想做成个江湖大会式的展览,更不想对中国当代艺术状况做一个盘点。我们更想展现的是年轻一代艺术家的艺术和生活状态。
我们需要这种有活力的东西。代群的区分和艺术创作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年轻一代艺术家的作品会呈现出一些共性的特质,这些特征的体现和当代的青年文化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中体现了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个时代给予年轻人太多的想象和空间了。
《当代艺术新闻》:那么68后艺术家跟上海香格纳画廊做的60一代艺术家,与现在呼声很高的80一代艺术家有什么根本区别?
朱彤:我个人是比较反对现在提某某一代的什么艺术家。在过去,这种提法似乎有他的合理性,就象提50年代、60年代一样。而今天我们拿70年代做一个分析,我觉得这代人就有三个阶段:一,70左右出生的人其实和60年代出生的人生活经历、教育背景都有很大的相似性。
而75年左右出生的人与70年出生的人有很多的不同,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的人又有什么样的区别?过去我们总喜欢用十年来形容一个年代,而今天可能三、五年就是一个时代,体现在艺术方面可能会更加明显。
50、60年代出生的人具有狂热的理想主义精神。虽然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是建立在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治背景之上的,但这一代人在今天却有着双重的痛楚。首先是他们的理想主义和现实的障裂,他们感到在今天明显面对的一切都与他们早年的理想主义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另一层是来自理想失落以后不得不面对眼下这个所谓的商业世界,甚至是道德社会所摈弃的东西。
他们要重新对原有的价值体系进行调整。
所以,导致这代人的行为方式会比较极端,双重痛楚带来的麻木使得他们有一种“歇斯底里的破坏欲”。体现在当代艺术上太多极端的作品,大多定格在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身上。但在80年代的年轻艺术家就很少有这类作品出现,在这背后是有它的内在原因的。
特别是要提一下,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经历了传统理想主义的尾声,又是中国现代性建设的直接目击者,然而,时代始终没有给这代人一个完整的时间,让他们来建设属于他们的价值体系。
所以体现在这代人身上就明显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然而80年代出生的人就完全不同。早期的理想主义精神在他们身上完全是丧失的。他们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消费文化极度蔓延的环境中共同成长,新一轮的道德和伦理已不再是早期“社会主义伦理道德”。
他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的准则,如对金钱的认识等等。体现在这代人身上,他们有对物质疯狂的崇拜欲,但他们却缺少对物质有真正意义的认识,商业化社会正导致新一轮的“道德危机”,这可能是他们要补的重要的一课。
《当代艺术新闻》:此次三年展的策划人为了遴选年轻艺术家进行了全国实地考察,在走访了众多艺术家工作室之后,考察的心得如何?请问68后艺术家是否有某些令人意外的整体趋势?或者有那些地域差别带来的某些整体性趋势的不同?
左靖:你说的是“滚动的三年展”计划,这也是被别的媒体誉为本届三年展最具特色的地方之一。当时的考虑是,如何使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考察更富于成效,使考察与遴选艺术家的单功能一变为传播策展理念与各区域间艺术家作品交流互动等多功能。
我们决定,以后每到一地,都将向当地艺术家展示我们前面所考察地区的艺术家作品,以便更好地结合“未来考古学”的主题进行交流,使之互通声气。从考察的情况看,各区域的当代艺术创作及展示确实存在着展示方式、媒介的形态倾向以及美学上的不同特质。
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比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先锋电影运动:德国以表现主义著称于世,法国有印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分殊,苏联则以蒙太奇学派蔚为大观……具体到我们去的20个左右的城市,比如杭州,这个区域的艺术家目前存在着一个开放性的群体,他们的作品形式几乎全是录像艺术。
在作品的内容及表现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同质性。这是因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录像艺术肇始于1990年代初的杭州,即便后来这一领域的杰出人士如杨福东、邱志杰、颜磊奔赴他方;杭州仍有元老级的张培力以及吴美纯坐镇,后来邱志杰又回中国美院任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的努力,录像艺术首次纳入了中国的美院教育。
邱杨等人在国内外鼓吹呐喊,张吴等人在内沉潜于研究教育,这一得天独厚的场域,使得杭州一带的艺术家自然而然地直奔录像艺术而去……对之的考察与梳理,本身就具有某种考古学的意味。其他地区也因为自身的历史与传统,物质之重(轻)与精神之轻(重)交织相生,地域差异与整体趋势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互动状态。
《当代艺术新闻》:展览的主题是比较晦涩和矛盾的“未来考古学”,未来充满偶然性和不可把握性,请策划人谈下对这个主题的解释和思考
邱志杰:请看看这次中国艺术三年展的一张海报所呈现出来的气氛——那上面是80年代的少儿科普年画,主角的胸前挂着“先锋”牌照相机,带着头盔坐在奔往月球的太空船上,画面充满了“走向未来”的憧憬。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未来有非常丰富的想象,甚至于出现了未来学这样的学科,出现了专门的未来学家。
像“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这样的概念都是在那个阶段开始深入人心的。但是那个时代的未来是一种可以逻辑地推导出来的结果。但是今天历史走到2005年时,我们发现,未来比以前更模糊,更不明确。
由于技术的进步、国际政治格局的改观、经济生活模式的变动,今天的这些年轻人建构未来的想象方式变的闪烁和不可捉摸。从前大家对未来是个普遍乐观的态度。
而今天的年轻艺术家们以他们艰难的工作向我们呈现他们的精神状态。今天的年轻艺术家的工作或许成熟或许不成熟,我们却不可能用一种必然出现的未来的指标来对他们的状态加于裁决,相反,他们的工作将构成我们的未来想象的基本素材。我们必须以一种提前的带有历史感的眼光来反思他们今天的工作。这种历史感并不是逻辑推理和价值判断,而是一种建构的主动性的意识。
这也正是“未来考古学”这样一个表面上自相矛盾的概念的内在隐喻力量:既然我们不可能像上一代人们那样非常逻辑去推导未来。我们就应该像考古学家那样小心翼翼,我们应该先去收集具体的实物,然后在实物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模型,让历史来验证我们的猜想。这是策展人们所理解的“考古学”。
《当代艺术新闻》:这个主题的提出是否有对当下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性?艺术家们又是如何理解的呢?跟策划人的初衷是否一致?
邱志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急剧地商业化,艺术家的思考也不可避免地陪卷入这个过程。和上几代艺术家不同,商业上的成就也很自然地纳入了年轻人的成功的范畴。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关键词,已经由过去的“革命”,变成了今天的“成功”。
“成功”是什么?是“有房子、有车子、有老婆、有孩子”的“新四有新人”,也就是一种中产阶级理想。这种理想中的未来想象是可以理性地预测和把握的未来,可以通过购买保险来规避风险,可以分期付款类预支未来的幸福,甚至是对未来的多种可能性的漠视和不思考。
所以说,当我们提出“未来考古学”的时候,本身就是对这样一种现实局面的再思考。我们是在重新提醒未来的不可预知性,未来的风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我们对于未来应有的责任感,这也是我们介入今天的现实的基石。
展览主题提出之后,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很多年轻艺术家的积极反响。他们认为这是对于他们的生存和创作状态的有效定位。由于技术的进步、国际政治格局的改观、经济生活模式的变动,今天的这些年轻人建构未来的想象方式早就变的闪烁和不可捉摸。
现实生活并不能够锁定他们的历史感和未来想象的想象力。应该说,“未来考古学”这样的概念本身不是描述性的,而是建构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我们有一种“初衷”,我们所受到的近千份方案本身就是对于这样一种初衷的应和。
《当代艺术新闻》:展览的筹备工作进行到目前为止,请问策划人对展览最为满意和期待的哪些因素是哪些?
左靖:“未来考古学”作为这届三年展的主题,考古学的某些方法自然也成为观察68后艺术家的一种视角。与传统考古学不同的是,遍及全国的“田野考察”,我们接触到的是一群群鲜活的艺术家,走进工作室、出租屋,面对面的交谈、争执……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探求,使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境遇与精神状态,艺术与生活的或离或弃在这里一目了然,如何将这些完美地转化为一种创造性的构想以及在展览中实现这种构想是我们最为期待的事情。
《当代艺术新闻》:请谈一下展览总体结构的划分,请分别解释一下四个主题展的概念。
邱志杰:这次的“未来考古学”将在“透支”、 “转基因”、“失忆”和“未来日记”这样四个小标题的名目下展开。这一组四个概念应该对应未来考古的不同地层,或是同一个断代中的不同功能区。毋宁说,他们本身是一些理论假设,或者是一些发掘工作中假想的甬道。
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来说,它们既是一种生活策略,又是一些美学策略。它们是更具有风险性的交易更加频繁的经济生活模式,也是将身体和心理经验更多地与技术和媒体相交缠的准备。失忆则是对于文化和身份的暂不定位,也是对于个人经验和历史叙述的双重不信任感;“未来日记”可能是一种以上的写作策略,但听上去它更多的是一种拒绝假设的基本态度。
《当代艺术新闻》:设置《1 1》单元看起来是在挑战展览模式,《在校实验》则像是在争取绝大多数的美术院校,它们是对既定权威的利用还是颠覆?请问策划人对这个两个单元的设置的意图是什么?
邱志杰:挑战展览模式的部分工作主要是体现在《现·场》和已经基本完成的《滚动的三年展计划》。《1 1》这个特展将邀请若干富有经验并具有持续影响力的艺术家(不设年龄限制),由他们每人各自提名一位年轻艺术家与其就文化观念和创作方法,以作品的方式展开对话。
这个研究型的创作尝试意在构建一个跨代际的对话和对比的平台,籍以探测“趋同与求异”、“影响与焦虑”在青年艺术家的自我定位中的作用机制。《在校实验》这个特展将重点呈现当代艺术思潮对在校的艺术学院学生的影响,特别是当代艺术教育进入中国传统的美术学院体制对当代艺术格局的巨大改变。
应该说,年轻艺术家从前辈师长那里和从学院那里所接受的权威性的影响,同时也在为他们制造着必要的焦虑,这是中国艺术中正在日渐更新的造血机制。如果力量无限,我们当然希望争取绝大多数的美术院校来参加,可惜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当代艺术新闻》:三年展预计的规模如何?它的筹备工作的状况如何?费用支出与投入的具体操作情况如何?
邱志杰:目前看来,在主体展中参展的艺术家已经达到90人,再加上几个特展,参与的新老艺术家名单肯定要超过百人。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原计划,工作量随之大增,原定的300万的预算也将大大突破,我们的主办方为展览的成型付出了很多,也有决心最后完善整个展览。
艺术家们的理解和支持始终是我们做好这次展览的最大前提,他们的付出是巨大的,相比之下,我们策展人所作的工作微不足道。目前筹备工作已经进入画册编辑和展厅空间安排的阶段。
《当代艺术新闻》:那你们最担心什么问题?
左靖:作为一个展览,如何使之更好地贴近策展意图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哪里有展览,哪里就有困难,更何况是这么一个大体积的展览。我们必须要与各种困难做斗争,比如资金、比如习惯势力、比如人际关系、比如我们的局限……
《当代艺术新闻》:这个展览是否会成为一个新艺术家的艺术大派对?它成为一个“三年展”的合法性是什么?
朱彤:展览对艺术家来说就是一个节日。展览也好派对也好,最终是要看它是否有“意思”。合法性要看从哪个层面来看,有一些商业性的画廊和机构也在推出年轻一代,但他们看中的也许是这些艺术家的商业升值空间,近几年涌现的许多关于年轻艺术家的展览,我们这个展览去了这么多的地方,面对面走访了大量的年轻艺术家,收到了近千份艺术家的作品方案,我觉得对学术的要求和艺术家的参与度就是最大的“合法性”。
《当代艺术新闻》:请问策划人对艺术家选择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
朱彤:当然首先是符合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我们更喜欢选择一些比较“新的”、“有创造力”的作品。
邱志杰:首先是立足于选择新人新面孔,这部分艺术家,注重的不光是他们是否曾经创作出一两件可圈可点的作品,更在于他们的创作方法论的展开,是否呈现出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有一些有相当名气和积累的艺术家,则是倾向以作品为单位,取舍得标准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提供让人们耳目一新的新的系列。
《当代艺术新闻》:参展名单里有很多的陌生名字出现,请问策划人如何发掘新人?
邱志杰:我们用工作室专访和公开征稿相结合的办法,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跑,接触到很多新人,同时我们也在艺术杂志和网站上很早就发布了三年展的消息,开通了讨论专区和的专门接收展览方案的邮箱。并且非常早就公布了策展人的名单和他们的通讯方式,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尽最大可能敞开大门。事实上,有一些艺术家是通过网络上邮寄来的方案和作品确定下来的,艺术家生态群之间的互相推介也往往非常有效。
朱彤:挖掘新人、推出新人是这一、两年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就这个展览而言,我觉得我们做了些比较踏实的工作,我们并没有在某的咖啡馆轻松的定下艺术家的名单,而是花了几个月时间走访了全国20几个城市和地区去了解他们,发现他们。这就是你可能看到的名单中有很多并不是大家熟知的名字。但是他们的作品是值得期待的。
《当代艺术新闻》:新人对已经成名的艺术家有何冲击作用?
朱彤:艺术的发展就是这样,总是不断涌现出新人。
邱志杰:艺术家从“新人”到“成名人物”的周期正在大大的缩短。新人的出现,会使一些只是暂时填补了空白的现在在舞台上的人物淡出。但是,另一方面,正真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地位会因为新人新作的出现进一步得到证实和巩固。所以,并不完全是一个“冲击”的作用。这两种结果都是我们乐见的。
《当代艺术新闻》:又如何弥补新人缺少现场控制经验的不足?艺术家与策划人如何合作?
朱彤:的确,年轻的艺术家缺少对现场控制的经验,特别体现在装置类的作品中,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在展览的前期准备工作中对艺术家的方案进行周密的商讨,提供一切帮助艺术家在现场实施方案的各种可能性的条件。尽管这样做会比较繁琐一些、累一点,但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到目前为止我们和艺术家的合作非常愉快。
邱志杰:对我来说,现场只是展览的一个阶段而已。就算是他们在现场控制方面有一些欠缺,也比一个四平八稳的安全的展览更有价值。展览发生之后的若干年后,这里所出现的艺术家能够真正成为中国艺术的中流砥柱,这才是最重要的。何况这也未必,新人未必就没有“经验”,他们所拥有所带来的将是新的角度上的“经验”,也是我们应该更积极一点,反过来去适应这些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