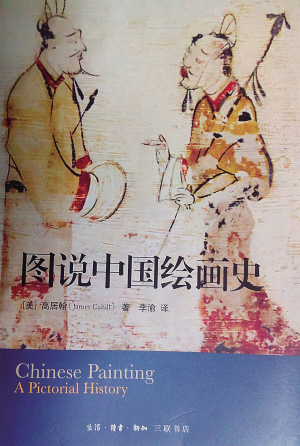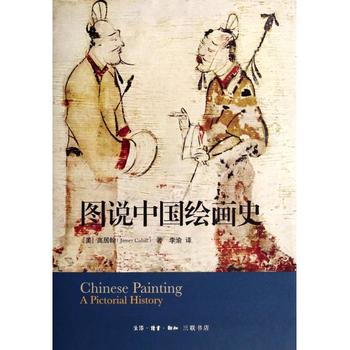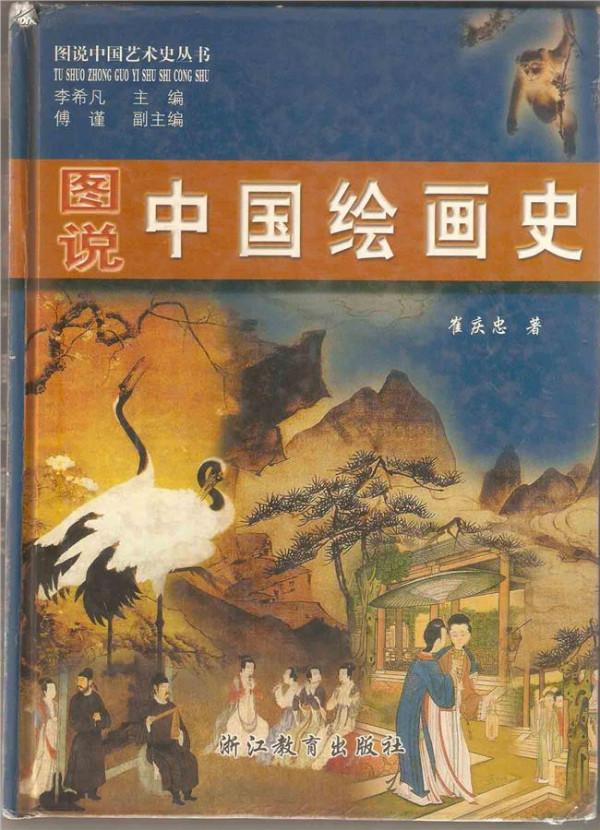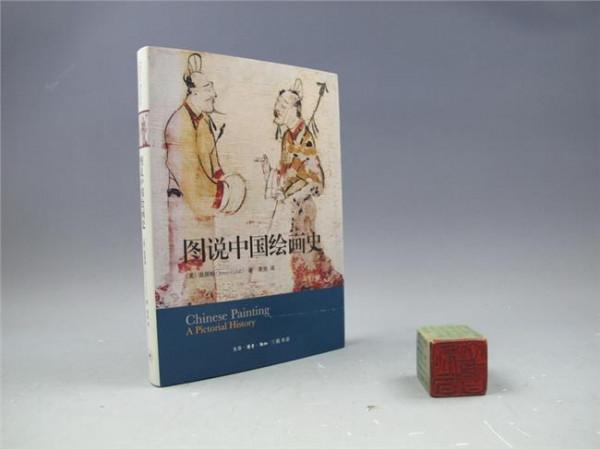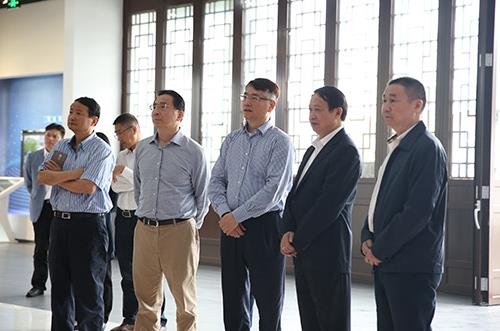中国绘画史高居翰 一个美国人的“中国绘画史”
《图说中国绘画史》 高居翰(美)/著 李渝/译 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4年4月 第1版
尾尾/缩写
无论如何,我们完成了这本书,1960年出版,而且即刻获得普遍好评。人们最常说的是,“书读起来好像读小说一样”,有些美术史论学者也许会认为这评语是侮辱,可我那时,以及现在,都觉得是赞美;它使用了一种现在被认为是不太荣誉的“叙事艺术史”的写法,却使书读起来轻松又愉快。
——高居翰
宋代山水:郭熙的《早春图》
从11世纪进入12世纪初期的南宋,是中国绘画史上事端特多的时期。为了了解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探究一下当时各画派各大师的活动情况:保守派和创新派、复古派和怪诞派、院画家和业余画家,各人都在以不同的风格创作着,繁复得令人称奇。
生活在这段时期的郭熙是一位重要画家。郭熙不只在绘画上超人一等,他还写了一篇中国最重要的山水理论。他说,一个真正喜爱山水的人,也许困于现实情况而不能使梦想成真,遨游于山石林泉间,但是他可以神游于图画中。能够画出这种山水的人,本身一定要和山水建立亲和的关系,观察山水在阴阳四时,昼夜晨昏间的变化。敏感而有技巧的画家要捕捉到所有现象。
郭熙的落款杰作《早春图》,画于公元1072年,是现存唯一能在雄伟气势上与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并驾齐驱的作品。但是它的雄伟是另一种不同的雄伟,是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中的骚动景象,而非对自然之永恒秩序加以肯定。
土石的形式有意过分膨胀到圆肿的地步,它们相互融凝渗透,好像是辽阔的有机体的一部分。强烈的不安定感激荡着画面。一种忽粗忽细的线条紧张地颤抖着;似乎有一片不自然的光从底层泛起,映亮了石块;阴影在某个层面上神秘地折闪着;这些现象愈发使画面不稳定起来。
而最不稳定的,是壁岩好像经历了万古的侵蚀似的,一律都从底部切开了。有些地方看来好像是画家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原定计划。例如他把最右边,原本应该作为楼阁基地坚稳的陆面,变成了危峻的悬谷,向下方开出一角隐蔽的世界,乍隐乍现。郭熙性情内可能有什么成分使他厌恶稳定吧。
五代及宋人物:周文矩的《宫乐图》
唐宋交替时期短暂而混乱,是为五代。当这五个短暂的朝代在黄河流域此起彼落的同时,南方比较稳定的两个政权,后蜀和南唐,成为流亡艺术家及其赞助人的庇护地。南唐定都南京,控制了江南大部分地区,从公元961年持续到公元975年,后亡于宋。
李煜是南唐著名的诗人皇帝。他宣称自己是唐代宗室,认为南唐朝廷是唐的正传。李煜宫廷中的主要格调典雅而唯美,在皇室赞助下进行创作的画家们多少也反映了这种风味。李煜画院中的人物画家追随了唐代传统,摹仿张萱和周昉的宫景图画特别流行。他们把贵族的闲逸生活描绘得细腻无比,完全配合了这脆弱的偏安之地的文化趣味。
周文矩是南唐最著名的人物画家,画风摹仿周昉。但是一部编于12世纪的画目在比较两人时,认为周文矩“纤丽过之”。既无落款也不知属何人之笔的《宫乐图》表现了周文矩最喜爱的题材。画家就算不是周文矩,这幅画似乎也要比那些被鉴定为周文矩的作品更像其时代或者其画派的作品。
在这里,四位妇人正在吹箫弹筝,玩笛弄瑟。一名侍从在旁击板配乐,组成了合奏团。另外五人用瓷碗饮着酒;她们都微醺了;最左边的一位已经要侍从撑扶着。她身后的妃后戴着一顶精致华丽的凤冠,手持一把圆扇;只有这位妃后正襟危坐,保持着尊严。
毫无疑问,这些人物都仿自周昉,然而唐代的丰腴之感多少已在其身上消失。早期风格中的修长曲线,已被锋锐的圭角所代替。线条本身也在这儿那儿轻微地折动着。
但是如果把这些风格上的细节放在一边不谈,我们可能就要相信(此画似乎也正有这个意思),自周昉以后,没有什么大事发生过。色彩依旧鲜艳,女士们也丰美如旧。艺术家和他的模特儿们都摆出了同样一种宁静而自信的模样,好像唐代从不曾灭亡过。李煜幻想自己持续了一个久已遗失的光辉传统,在这一点上,南唐院画家们恐怕真为李煜尽了不少力。
吴派:沈周的《策杖图》
明代第一个世纪过去了,文人画派没有任何显著的新发展。紧接着元末四大家的一代产生了几位有能力的画家,但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满足于摹仿前人,和集前人之大成。文人画派继续活跃着,局限在江南一带,特别是在苏州附近。
苏州这时已成为士大夫文化的中心。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小批画家终于重新把文人传统建立成中国绘画中的主力。这些画家生活在苏州附近的吴县,因此也就被称为吴派。他们大部分出身世家,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浸融了洋溢于明代中期社会里的安全感和优越感。
他们之中很少人展现出像无数元代画家所具有的那种反社会倾向,或者好似明末和清初的独创主义画家们所表现的那种热烈的突破精神。稳健与平衡才是他们绘画的主要调子,并由创始人沈周奠定下来。
沈周出生于苏州望族。他在成长过程中,从两种经验里获得了不少好处:与亲朋之间大量的学者、诗人、画家为友以及受到良好的教育。此外,他自己也同时具备了学者和画家两方面的才分,对于能够拿到手的,或者可以看到的书籍和绘画又有学习的热情。
他有好几位老师。从摹仿他所仰慕的前人画风中,也学会了一些技法。他一生不断“仿”宋元各大师,这一点他是自己明说了的。但他绝不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他的作品以他独特的技巧和风味画成,革新了旧的风格。
把沈周摹仿倪瓒的作品《策杖图》和倪瓒的山水拿来做一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类“仿作”中的独创成分。这是个很有用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被常人误解的中国画家的“仿古”训练究竟是什么。沈周保存了倪瓒的基本体式:河岸兀立着枯树,远处叠卧了几座山峰。
唯一被沈周加进画面的树下老人是这样的安详而无心,恐怕就是倪瓒——一个从不在山水中画人物的人——也不会在意这种打扰吧。倪瓒大部分技巧都保存在这里,例如点在坡石上的疏落的苔点,这是倪瓒的特征之一。
在勾勒坡石面和其他实体轮廓的皴笔方面,沈周以抖动的长线条替代了倪瓒柔和而挺直的宽线条。这种线条看似松闲,却充满了柔韧的张力,因此早期画风中的闲逸感也就不存在了。但是两者构局上的不同却是最有意义的地方。
沈周从这位元代大师那儿取得了大部分素材,却建造出崭新的局面,结构紧密,规模庞大,有力地透露出山势的骚动和冲劲。中央最高一棵树的树顶有意留成秃枝,直入河口。河口把上景坡岸匀成两半。这样一种几近轴柱对开的构造法,这样一种令人感到不安的平衡,是非正统的,甚至就其时代来说,也是大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