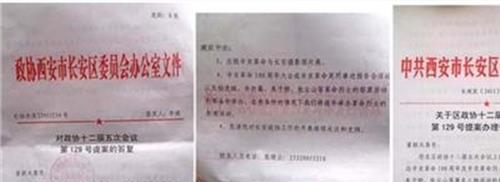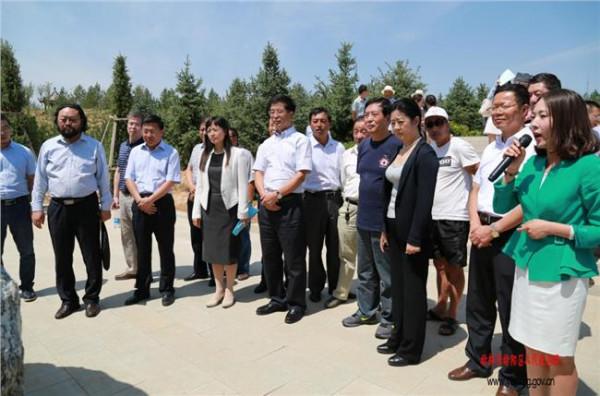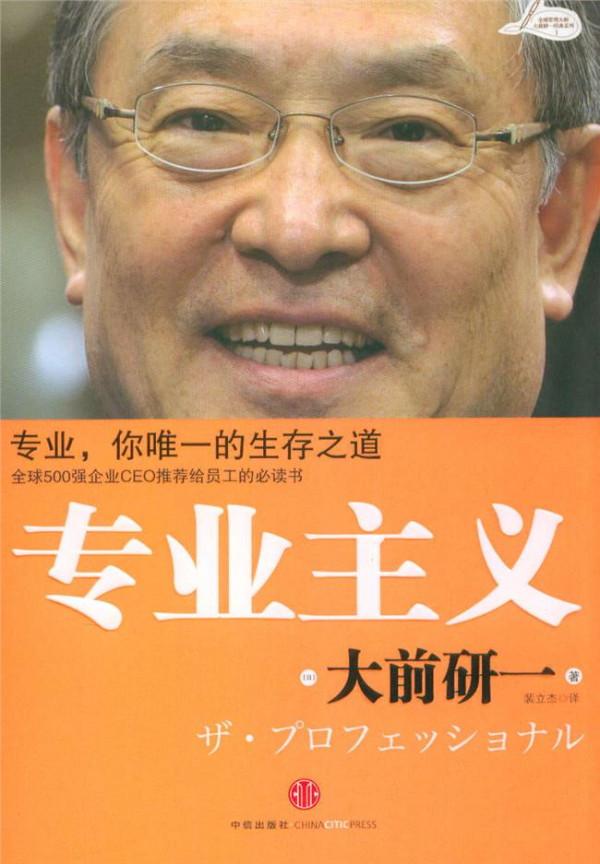评论张季鸾 刘宪阁:张季鸾是怎样写评论的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所知道的张季鸾,是通过他在报端尤其是《大公报》留下的社评文字,以及朋辈友人和报社同事们留下的回忆建构起来的。而近年来,又陆续发现一些相对比较边缘性的人物和记载,也或多或少地留下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和材料。比如,在最近获赠的湖湘文库《近代湖南出版史料》乙编第二册中,就读到一段唐际清谈张季鸾写评论的记载。
这段回忆为《报学杂话》系列之一篇,原本连续刊于湖南《大公报》1940年6月18日至1941年7月21日(和天津那个《大公报》无关)。现经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黄林先生编辑整理,收录于湖湘文库之乙编。杂话的作者署名为唐际清,详细经历待考。
不过据网络等有关资料,可知或为湖南武冈人,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曾为天津《益世报》等有所撰述。主持过南京《扶轮日报》的笔政,后应萧同兹之邀,出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编辑;抗战爆发后,又出任该社湖南分社主任等职。果如此,则能与杂话系列,特别是这里要介绍的第二十七篇中的相关记载对应上。
在这篇杂话中,唐氏称,早年“服务于天津报界时,常以评论做法就教于张(季鸾)胡(政之)二公”。两位先生所谈,和他执笔此文时读到王芸生的演讲词《新闻记者怎样立言》“大致相同”。不过也有几件事,为张、胡二人“平日所经验和身体力行者”。唐际清觉得有必要补充记录,“以供评论记者之参考”。他特别记下了张季鸾先生关于怎样写评论的几点看法。
其一,张先生认为,报纸要有价值,必须“评论”有权威。而评论何以有权威呢?王芸生所谓“帮助多数人”说话诚为主要条件之一,但张季鸾以为还不够。提出切忌“唱高调”、“乱批评”。不唱高调,则因为主张切合实际,容易为政府采纳,见诸实施;不乱批评,亦即不随便发言,张先生以为,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如此则对社会可以发生较好的影响;而善意的批评,也更容易为被批评者所接受。
衡之天津《大公报》的社评,可知先生所论不唱高调、谨慎发言之不虚。
其二,张先生又说,评论记者的起码条件,“要有人格与修养;千万不可有火气,但千万不可没有情感。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有同情心与侠义心”。否则,写出来的评论,不是骂人,便是冷酷,那是绝对不行的。此点和相关回忆,特别是张季鸾自己的一段评述相印证:“做记者的根本,是要对人类大众,小一点说,先对于中国同胞们,有深厚的同情!
因而立下了救世的决心!他们有苦痛,应该给申诉,应该设法安慰。凡社会的不平和罪恶,应该反对,应该冒着危险,去替人类们、同胞们用言论斗争。不应该屈服于恶势力,或者同流合污!这一种仁慈义侠的精神,是新闻记者根本的根本。”
其三,张先生主张:“平时少论国际时事,多论地区政治和社会问题。”而最要紧的,是对某个问题的批评或讨论,必须提出办法。他自认为,天津《大公报》评论的特点,就是能够言之有物,提供办法。
其四,张先生认为,评论记者最感困难的,不在评论的内容,而在选取什么题目或者说题材。所以他每天下午到编辑室,先浏览中外报纸及杂志,找到一个评论题目后,就搜集有关资料,略加思索整理,一篇社评大致有了腹稿。到晚上十二点,如果没有突发事件要发表极具时间性的评论,则明天社论预定的腹稿,不到两小时就可以写成了。
唐际清拿张季鸾说的这几点,去读天津《大公报》的社评,觉得可以说是“若合符节,都做到了”。而在杂话系列的另一篇中,他更钦佩张先生当时为《大公报》桂林版所寄的重庆通讯。因为里面有不少珍贵资料,“一般读者想知道而不知道者”;更重要的是,通讯最怕冗长,让读者不得要领。
而作为深入政治内层的记者,张先生“知道的一定比发表的多若干倍,而能选择可以发表的许多精要事实,用简明生动的语言,写长短合度的政治外交通讯,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