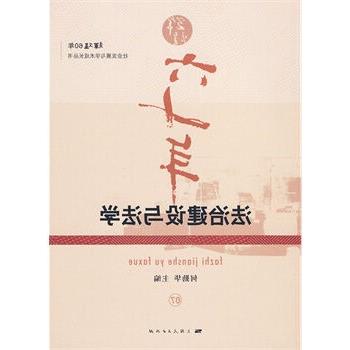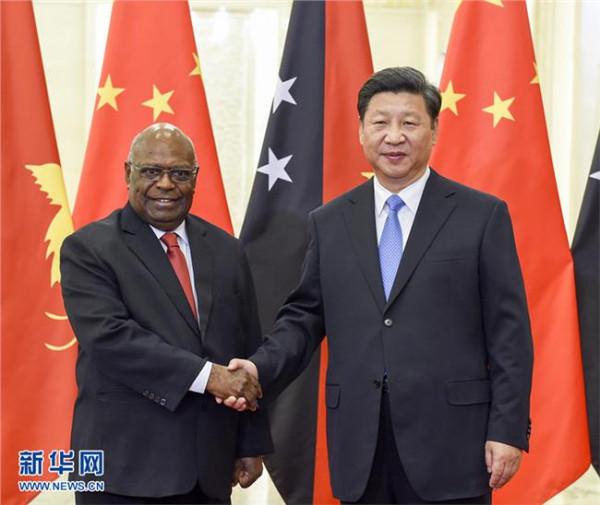儿童文学李东华 李东华:新中国60年儿童文学的精神走向
教化、快乐与救赎——新中国60年儿童文学的精神走向
中国儿童文学从现代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与中国新文学一道诞生、成长的,新中国60年则占据了三分之二的里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儿童文学发展史,就是成年人‘儿童观’的演变史”(王泉根《论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因而我们要探究,作为儿童文学创作主体的成年人,一直以来用什么样的目光打量“儿童”,它划出了儿童文学发展的无形的精神边界。
鲁迅、周作人、冰心、叶圣陶这些文学大师,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奠基者,新中国60年的儿童文学正是承继了他们的精神流脉。他们看待儿童的眼睛闪烁着三种不同但又相互交织的目光:一、这个“儿童”是抽象的,他是民族国家的化身,代表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未来。
也正因此,中国儿童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忧患意识和神圣的责任感,“十分注重对儿童进行精神教化的功能,即通过道德评价的主题传递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传递本民族的人格理想”(汤锐《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
二、这个“儿童”是具体的,是不同于成年人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孩子,儿童文学应该从儿童本位出发,符合儿童的心理特征和阅读期待,解放儿童的天性,愉悦他们的身心。
“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高洪波语)。尽管对儿童独立人格的尊重并不完全等同快乐文学的观念,但必须以之为基础才能发展出注重游戏精神和娱乐功能的儿童文学理念。三、这个“儿童”是象征意义上的,象征着一尘不染的清净世界,和被污染的成人社会恰成鲜明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成年人实现自我救赎的精神家园,甚至,“童年是一种思想的方法和资源”(朱自强语)。
因而,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对童心和童年的礼赞、膜拜与思考。
这三种看待儿童的目光会对儿童文学的走向产生不同的影响,但同时它们又是相互渗透的。由于社会语境的不同,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种种因素或间接或直接作用于儿童文学创作,会使其中的某种倾向在某个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甚至发生变异,走向极端化、绝对化。但经过大浪淘沙和岁月磨洗的经典之作,则基本是那些融合了这三种精神诉求的优秀之作。
对“童心”的“教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1949-1966),是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期。“50年代以降,在广大少年儿童中产生广泛影响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品,几乎无一不是教育型的”(樊发稼《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儿童文学卷》导言)。
因为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少年儿童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祖国的“花朵”,儿童文学义不容辞地要承担起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任。因此,浓厚的教育色彩正是“教化”思想在这个年代的具体表现。
从外部环境来看,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儿童文学读物从数量到质量都无法满足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从儿童文学的内部发展来说,“教育性”在任何时候都是儿童文学重要的功能,只是要把握好一个度。这个时期的作家身经新旧两个社会,有些直接参与了民族解放的斗争,他们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和人生经验,有着严肃的创作态度。
同时,他们不懈地向世界儿童文学尤其是苏联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学习和借鉴,不断丰富和提升自己的创作技巧。在沉甸甸的现实生活和厚重的传统文化的支撑下,这种“教育性”就因为饱含了人生的体温和丰沛感人的爱国主义情怀而不致沦为空洞的说教。
尽管“教育性”是当时每个儿童文学作家所要遵守的艺术标尺,但并不是说他们的心中就泯灭了对“儿童性”的清醒的坚守。张天翼当时就提出儿童文学一要“有益”,同时还要“有味”(《给孩子们》序)。严文井则反对“由乏味的说教代替生动的形象”(《1954-1955儿童文学选》序)。
陈伯吹则在《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也正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虽然难免会沉淀着那个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但仍然有着浓郁的童真童趣,有着对儿童心理深入和准确的把握,甚至今天特别重视的幽默品格,在《“没头脑”和“不高兴”》《猪八戒新传》等篇什中也有鲜明的体现。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衡量一种文学,并不根据它的意图,而是在于它的实际表现,它的思想、智慧、感性和风格”(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典型的当属张天翼的短篇小说《罗文应的故事》。对于罗文应好玩、好奇的儿童天性,按照当时流行的艺术法则,作者当然是持批评态度的,但因为作者严格地遵照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忠实而客观地描绘了罗文应的一举一动,于是一个活灵活现的顽童形象,就超越了作者简单的是非判断,栩栩如生地站在了我们面前。
这虽然只是一些片段,但依稀让人看到了林格伦笔下的淘气包埃米尔的神韵,而杨红樱等作家所塑造的马小跳等各类淘气包们,也不能不说和罗文应有着近亲关系。只是罗文应“生不逢时”,生在20世纪50年代,只能是个被教育的对象;而马小跳诞生在21世纪,所以能大受追捧。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儿童游戏精神的刻画描摹自那时起已有很多神来之笔,即便它们有时被作为反面教材存在着。另外应该说明的是,儿童文学作家们由新生政权所激发的昂扬、嘹亮的基调也带进了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阳光”、“春天”、“向日葵”、“燕子”、“海浪”这些明媚的意象和图景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带给了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以特有的单纯、明朗之美。
尽管如此,“十七年”儿童文学创作最值得人警醒的一点还是如何避免沦为政治的附庸,避免从“教化”走向“教训”。这一时期的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和校园题材为主。这些作品的主旨通常是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对他们身上的缺点(通常连儿童的好奇、好动等天性也视为缺点)进行委婉的批评,通过批评—帮助—克服这样一个过程,最终使小主人公实现“进步”。
这样的作品容易流于简单化、概念化。而“左”的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已经开始干扰儿童文学创作,以至于儿童文学的教育性走向了极端化和绝对化,成为政治说教。
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当时某些作品“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向着“文学性”和“儿童性”复归
“文革”中,只有极少数的作家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最突出的就是李心田的革命历史题材中篇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乏善可陈。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中国儿童文学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新时期成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成就最大、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
1978年10月,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江西庐山召开,随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努力做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工作》的社论。备受鼓舞的儿童文学界在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上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向着“文学性”和“儿童性”复归。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儿童文学理论上众声喧哗、创作上佳作迭出的年代,其中短篇小说创作尤为突出。作家们在不同领域里激情满怀地开疆拓土,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接受西方文艺思潮的洗礼和熏陶,以“寻根”的心态回望中国传统文化,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理想探索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探求人类童年文化的底蕴,把中国儿童文学推向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在题材、体裁、主题、艺术手法等方面均有不小的突破。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整个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最强音是曹文轩发出的:“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这是“教化”这一理念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新的时代表述。这种理念的最直接推动力是十年“文革”后中国和西方在经济、文化上所面临的巨大差异。
儿童文学作家们面临着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相似的精神困境,对于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巨大焦灼,使他们开始探索究竟少年儿童具备什么样的性格,才能使我们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80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品向人们表明:它喜欢坚韧的,精明的,雄辩的孩子。它不希望我们的民族在世界面前是一个温顺的,猥琐的,老实厚道的形象。它希望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族是开朗的,充满生气的,强悍的,浑身透着灵气和英气的”(曹文轩《觉醒、嬗变、困惑:儿童文学》)。
显然,对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渴望已经超越了对“儿童”作为一个具有血肉之躯的个体的关注。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表情是批判的犀利和反思的深沉。
儿童文学作家们把矛头指向“左”的政治思潮,指向落后的愚昧的观念,指向虚伪的成人世界,指向僵化的学校教育,指向中华民族积淀了几千年的文化性格;而这一切对立的势力都是扭曲了、压抑了“儿童”的心灵和性格的罪魁祸首,正是这一切使那个原本“开朗的充满生气的强悍的”“儿童”变成了“温顺的,猥琐的”孩子。
所以他们要拨云见日,“寻找小小男子汉”,还这个“儿童”以充满阳刚之气的本来面目。《班主任》《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我要我的雕刻刀》《三色圆珠笔》《寻找回来的世界》《第三军团》以及沈石溪风格硬朗的“动物小说”和刘先平充满探险意味的“大自然文学”……无不以一种粗犷而野性的力量重新雕塑着“儿童”的灵魂,以使这个“儿童”能够有能力负担起复兴民族大业的重任。
孙云晓于20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将中国独生子女的脆弱和日本孩子的强悍作鲜明对比,正好击中了中国人的隐忧,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这一现象恰好说明,这一创作理念能够在儿童文学界和读者中一呼百应,决不是偶然的,它的轰动效应是和整个时代的情绪和期待完全契合的。
新时期以来宽松、包容的创作环境,也让其它各种艺术流派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以郑渊洁为代表的“热闹派”童话得到了广大小读者的肯定,高洪波提倡的“快乐文学”以及他在儿童诗里对幽默、诙谐艺术元素的应用,在这个时期都表现得相当抢眼。
他们投射到孩子身上的目光,视线已经下移,从俯视到平视——把孩子当成朋友,去掉那些功利性的说教,解放孩子的天性、想像力,给孩子们带来轻松、快乐的笑声。这道下移的视线预示了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观念的转变,它在这个季节里成长、壮大,必将在下一季大放异彩。
“市场化”的快乐原则值得思考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大潮以及电视、网络等新兴体媒的兴起,儿童文学和整个文学界一样,曾出现一段沉寂、彷徨的时期。1995年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扶持“三大件(长篇小说、少儿文艺、影视文学)”后,儿童文学界经过一段摸索之后调整了创作策略,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更加贴近少年儿童生活,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儿童文学进入了多元共存的时代。老中青少作家四代同堂,中国儿童文学已经有了一支稳定的高产的创作队伍。这些作家人生阅历不同,艺术主张各异,既有对纯文学创作的痴情和坚守,也有对类型化写作、通俗化写作的热情与尝试,共同形成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声部的创作格局。
这是个“儿童性”得到极大解放的年代。儿童文学开始大面积地追求快乐的原则,从对“大我”的关注悄悄转向对“小我”的探究,从对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转向了对个体日常生活经验的发掘。从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等一系列小说到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小说,是这一艺术流派的代表性作品。
这个时代的艺术开始偏好轻松、幽默的基调和飞扬的想像力,90年代后期浙江少儿社推出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推出的“大幻想丛书”,正是对这样的时代脉动的呼应。
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少儿社推出了“自画青春”系列长篇小说,郁秀出版了长篇小说《花季·雨季》,随后是新世纪以后韩寒、郭敬明等少年作家的迅速崛起。
这一现象显示了小读者对于从个体经验出发,了解自我、关注自我的渴望。进入新世纪后图画书的兴起,说明儿童文学的分类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注重在“儿童文学”这个笼统的大的分类之下,每一个小的群体的具体需求,从另一个层面讲,这是“市场细分”原则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具体体现。成年人投到儿童身上的目光,这时候也掺杂进些许讨好的意味。
“儿童文学”对快乐原则的张扬,并不意味着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已经退居幕后。在儿童文学作家们一直坚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里,我们看到了它顽强的影子。张之路的科幻小说《非法智慧》对科学这把双刃剑进行了深度思考;秦文君在新世纪突然推出了《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天棠街3号》等对我国教育体制的弊端、对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刻追问的批判意味浓厚的长篇小说,大有回归上世纪80年代的意味,可惜在市场的喧嚣中这两部优秀之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伍美珍和刘君早面对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推出了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报告文学集《蓝天下的课桌》;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和《青铜葵花》,其唯美的品格和对苦难意识的挖掘,是对他一贯的美学主张的坚守。
在新世纪里,曹文轩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已经从“塑造未来民族性格”变为“为人性打底子”,这是一次耐人寻味的转变。他在写下了《大王书》系列幻想小说之后,又出版了《我的儿子皮卡》系列。这个一贯和当下的现实生活拉开距离,总是把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的作家,第一次把镜头拉得如此之近,回到当下生活的现场,而且也采用了系列小说的形式,一共要出16册。
作为一个风向标式的作家,他个人的转向,有时候可能意味着整个儿童文学的一种集体转身。也许因为离得太近,还很难估价这种转向在儿童文学史上的意义,可是,这至少表明时代变了,儿童文学原有的美学原则和价值理念,都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可能。
儿童文学的下一个热点将是什么?虽然这60年来,不乏有优美动听的对童年、母爱、大自然的歌颂,但这种颂歌往往流于表面和肤浅,和冰心、丰子恺等一代大家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思考童心、童年相比,当代儿童文学对于“救赎”这个主题的探索始终不冷不热,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
当生活在文明社会的都市人重新思考乡土、大自然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童年”能否成为成年人的一种思想资源,成为他们精神的栖息地?或许“救赎”这个主题会有一天突然热闹起来,成为人们追逐的话题。一切都不得而知。
但是,在商业化的背景下,这种“儿童性”在极大解放的同时,也导致了消费童年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旦和金钱结合,就会完全以孩子喜欢不喜欢为标准,这个“儿童”在大人们的眼中也就完全变成了文化产业中的取款机。他们眼中的这个“儿童”不需要教化,更不可能成为成人实现自我“救赎”的精神资源,只要打着“快乐”的旗号,用廉价的笑声换来钞票就行。
那么,和当初“政治挂帅”对儿童文学的戕害一样,如今的“市场化”必然成为拉扯儿童文学偏离正常轨道的强大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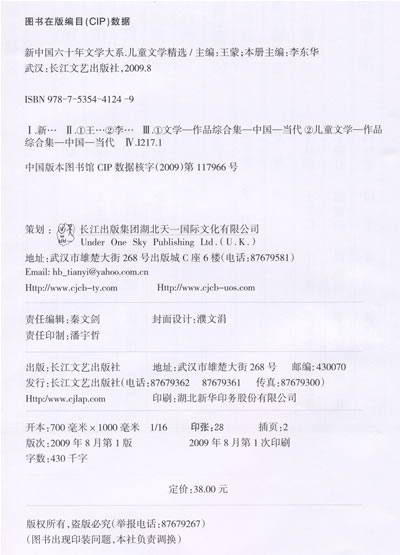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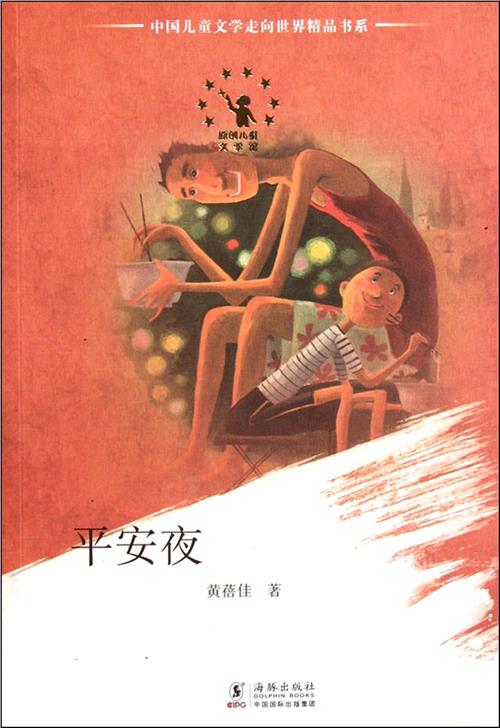







![[14/8/2010]难忘的旋律:新中国50年代电影歌曲精品连播(原声原唱)](https://pic.bilezu.com/upload/3/35/335245d7bb9f68da8f364d294de109fa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