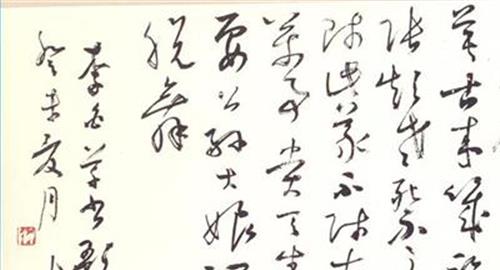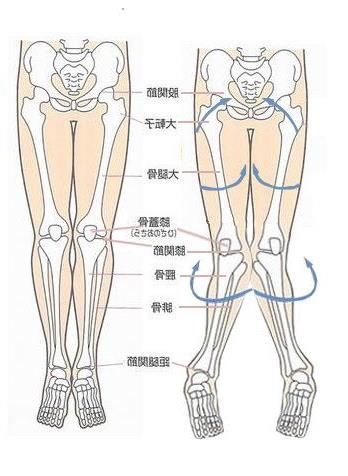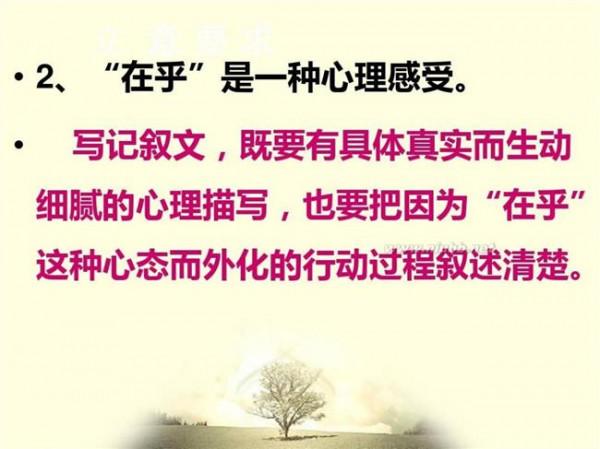近三十年的散文孙郁 《近三十年散文掠影》 ——孙郁
从文言到白话,从平民语到文人笔墨,从党八股到小布尔乔亚之文,汉语言在20世纪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实用主义一直是汉语身上的重负,以致其审美的功能日趋弱化了。
六七十年代,汉语的表达是贫困的,文字的许多潜力都丧失掉了。所谓新时期文学,恰是在这个贫困的时期开始的。"四人帮"垮台后,中国重新开始了梦的书写。那时还是观念的现代的转型,个体意识的萌动还是后来的事情。
到了80年代,文化的自觉意识在学界和文坛蔓延,随笔、杂文的风格也渐趋多样化。开始的时候,还是文字的合唱,鲜见独异的声音。一切还是被观念化的东西所包裹,后来就渐渐神采四射,有深切的词语登上舞台。最初引人关注还只是社会问题层面的话题,个体生命的呻吟是稀少的,几年后自省式的短章才不断涌现。当时的作家沉浸在思想解放的神往里,全然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痕迹。
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变,一个八股的时代正在隐去。五四风尚、明清小品、俄苏笔意、意识流、现代主义等在人们的笔端流出。世界突然五光十色了,人们知道冲出囚牢的意义。有趣的是,那时候给人们带来兴奋的不是青年,恰是那些久经风雨的老人。
巴金、冰心、曹禺、钱锺书、胡风……这些人大多经历过个人主义精神的沐浴,后来转向国家叙事,晚年又重归个体情趣。巴金以讲真话的胆量在呼唤鲁迅的传统,冰心在预示着美文的力量,钱锺书的谈吐不乏智者的神姿。
那时报刊的文章在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如唐弢、黄裳的写作把旧有的文人气吹到了文坛,他们的文字是典型的报人风骨,留有民国文人的趣味,没有被当代的文风所同化。孙犁的文字在晚年越发清俊,以爽目、坚毅、优美的短篇洗刷着历史的泥垢。
孙氏的作品,有田野的清风,没有杂质,一切都是从心灵里流出来的。一方面有作家的敏感,另一方面则流动着学人式的厚重。他在许多地方模仿鲁迅的思路,又自成一家,给世人的影响不可小视。
贾平凹、铁凝等人都从他那里获得了启示。我们从刘绍棠、从维熙等人的作品里甚至也能呼吸到类似的新风。杨绛的笔锋是锐利清俊的,她对知识阶级的人木三分的透视,乃学识与智慧的交织。那里有西洋文学的开阔与晚清文人的宁静,有时带着寒冷的感觉,有时是彻悟后的闲情,将文字变成智者的攀援。
较之那些哭天喊地的文学,她的不为外界所动的神态,消解了世俗的紧张。五四时期是青年的天下,新时期却是老人尽显风姿的日子。历史像开了一个玩笑:"旧人物"展示了丰沛的土壤,在这个土壤里,中断了的五四遗产重新闪现着。
学问家的写作在这个时期是风骚俱现的。季羡林、金克木、费孝通、冯至都以自己的短章让世人看到文字的魅力。他们放松心境地倾诉内心的情感,留下的是别类的心得。述人、谈己、阅世,渗透着生命的哲思。不都是哀怨,有时坚毅的目光照着世界,使我们在这样的文字面前感到世上还有如此宽阔的情怀,不禁欣慰。王蒙曾呼吁作家的学者化,其实就暗含着对汉语书写的灵智力的召唤。
在老人的书写群落里,张中行与木心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们曾被久久湮没着,无人问津。可是这些边缘人的出现,给散文界的震动非同小可。80年代,张中行的作品问世,一时旋风滚动。到了2006年,木心被从海外介绍过来,引起了读者的久久打量。
张中行的思想是罗素与庄子等人的嫁接,文章沿袭周作人的风格,渐成新体。他的文字有诗人的伤感也有史家的无奈,哲人的情思也是深埋其间的。意象是取于庄子、唐诗,思想则是怀疑主义与自由意识的。在他的文本里,平民的情感与古典哲学的高贵气质,没有界限。他的独语是对无限的惶惑及有限的自觉,文化的道学化在他那里是绝迹的。也因于此,他把周氏兄弟以来的好的传统,延续了下来。
自从木心被介绍到大陆,读者与批评界的反应似乎是两个状态,前者热烈,后者平静。作品的被认可,在过去多是借助了文学之外的力量,或是现实的心理需求。有时乃文学上的复古,明清的所谓回到汉唐,80年代的回到"五四",都是。
木心绕过了这一切。既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主义的标榜,不拍学人的马屁,自然也不附和民众的口味。东西方的语汇在一个调色板里被一体化了。这是一个独异的人,一个走在天地之间的狂士。类似鲁迅当年所说的过客,只不过这个过客,要通达和乐观得多,且把那么多美丽的圣物呈现给世人。有多少人欣赏自己并不重要,拓展出别一类的世界才是创造者的使命。
文学本应有另外一个生态,木心告诉了我们这种可能。文学史家对他的缄默是一个错位,不在文学史里却续写着文学史,便是他的价值。看看网络的反应,足可证矣。
一些杰出的画家,如吴冠中、范曾、陈丹青,偶然的写作,打破了文坛的格局,使我们瞭望到新奇的存在。散文界的杰作常常出自于非文学界的人,科学家、社会学家和画家的介入,引入的是新的景观。杨振宁、李政道都写一手好的文章,奇异的思维改写了人的记忆。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汉语的可能,远未被调换出来呢。
我说过,当代文学史存在着两个传统,即鲁迅与周作人的传统。现在依然坚持这个看法。30年代,周作人认为文章存在着"载道"和"言志"两个流派。钱锺书曾对此表示异议,那是学术之争,难说谁对谁错。在我看来,"载道"与"言志"后来经由鲁迅兄弟的穿越,形成了现实性与书斋化两种审美路向。
至少在80年代,散文还在鲁迅、周作人的两个传统里盘旋,其他风格的作品还没有形成气候。鲁迅的峻急、冷酷及大爱,对许多作家影响巨大。优秀的作者几乎都受到过他的思想的辐射。
邵燕祥、何满子、朱正、钱理群、赵园、王得后、林贤治都有鲁迅的风骨。邵燕祥短文有犀利的力量,毫无温吞平和的虚伪,常常让人随之心动,正切合了"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传统。
何满子谈历史与现状,袒露着胸怀,何曾有伪态的东西?朱正严明、牧惠深切、赵园肃杀,是真的人的声音。对世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些作家的自我表达,多了批判的笔触,与其说是指向荒诞的存在,不如说也在无情地冷观自己。只是他们中的人对西学了解有限,没能出现大的格局和气象,这是与鲁迅有别的地方。
周作人的传统在历史上被诟病,可实际是存在这样的余脉的。沈从文当年就是受到周氏的影响,后来的俞平伯、江绍原走的也是这个路子。80年代后,周作人的作品重印,他的审美认同者们也被推出水面。舒芜、张中行、钟叔河、邓云乡都有学识的风采与笔致的神韵。
他们把金刚怒目的一面引到自然平静之中,明代文人的灵动与闲适杂于其间。个人主义在中国一直没有健康的空间,文人的表达也是隐曲与委婉的。以"说出"为目的,而非言"他人之志"为旨趣的表达,在更年轻的一代如止庵、刘绪源等人那里得到了响应。
鲁迅与周作人的传统并非对立的两翼,把两种风格融在一起的也成为了一种可能。一些人既喜欢鲁迅的严峻,也欣赏周作人的冲淡。唐弢的文字其实就介于明暗之间,黄裳在精神深处流动着激越与闲适的意象,孙犁的小品文在两种韵味里游动,虽然他不喜欢周氏,可是这两种笔意是难以摆脱掉的。
钱理群其实是赞成两个传统的互用的。他对周氏兄弟的研究无意中也影响了知识界对新文学传统的看法。刘恒、叶兆言都欣赏周氏兄弟的文采,在他们的随笔中,偶尔也有那些历史的余光的闪烁吧?
其实在周氏兄弟之外,散文的样式很多。像汪曾祺,就杂取种种,是自成一格的。汪氏举重若轻,洒脱中是清淡之风,颇有士大夫的意味。与他同样诱人的是端木蕻良、林斤澜等。端木晚年的散文炉火纯青,不被世人看重。可是我觉得其分量不在汪氏之下,至于林斤澜,其文恍兮惚兮,有神秘的流风,吹过精神的盲点,让我们阅之如舞之蹈之,很有醉意的。
他们都生在民国,受过旧式文人的训练,文字不时流出古雅的气息。"文革"的话语方式是在他们这些人那里开始真正地解体了。
在这个层面上,说新时期的文学是回到五四的一次穿行,也是对的。世人也由此理解了为什么是老人承担了这一重任。启功的幽默,聂绀弩的狂放,贾植芳的率真,柯灵的无畏,都衔接着一个失去的年代的激情。不同的是他们带着半个多世纪的烟雨,有了更为沉重的肩负。读这些人的作品,常能感到道德文章的魅力,身上还带着旧文人的抱负。与五四那代人比还显得有些拘谨,而心是相通的。
因为痛恨说教的文学,一些新面孔的书刊在三十年间纷纷问世,引来了散文的流变。这些刊物是从颠覆僵化的文体开始引人注意的。外国的随笔译介,西方世界的难题也进入了写作者的视界。许多青年正是在这些译文里得到了启发,7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者更多是吸取了洋人的笔意。
不过考察三十年间的作家,引人注意的作者大多是经历过磨难的人,高尔泰的酣畅淋漓,张承志的清洁之气,北岛的浑厚磊落,史铁生的寂寞幽远,周国平的绵远深切,在吸引着我们的读者。这一群人在心绪上都有独特的一面,中国的历史在他们内心的投影实在是太长久了。在挣脱了八股文化的束缚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一下子就把自由的心放逐到天地之间。
从80年代开始,散文的疏朗感日趋明显。从小说里走来,从哲学里走来,从诗歌里走来,各种视角下的文体都开始登场。张承志模糊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史铁生的独语从诗情进入到天人之际的哲学之境;余秋雨的苦旅,把学术随笔与游记结合起来,解放了小品文的套路;在高尔泰的心语里,画家与史学家、哲学家的色彩都能看到。
我在读徐晓回忆文字时,听到了她空旷的心灵里无边的大爱,那一刻在心里对其过往的苦难感到了震撼。同样的,林贤治的回肠荡气撕毁了世人的伪饰,他内心的刚烈在词语里形成了一个气场,把人引向遥远的高度。
从文化史的角度打量生命的秘密,在一个时期成为一部分人热衷的实践。余秋雨的出现使许多人随着登上一座座时间的峰峦。地域性的大随笔在层出不断,祝勇写湘西,王安忆谈上海,车前子的江南,马丽华的西藏,贾平凹的陕西,各臻其妙。
近三十年来民俗学与史学新理念的出现,诱发作家从理性的层面进入历史,以免使感性的直观被幻影所囿。贾平凹的文本就提供了社会学的图景,原始思维对乡民的暗示,常能在他的作品里找到。刘亮程的乡下笔记,是过去文人从未有过的摸索,文体上的拓新是爽目的。
有时,偶与这些美丽的文字相遇时,我就想,其实我们的作家沉浸在各自的世界的时候,都自觉向着感知的极限挺进。深浅不一,力有大小,而呼吸的空间似乎渐渐扩大。他们一面直面着,一面内敛着,将自己的心贴到时光的隧道里。那些文字就是这隧道里的火光,一点点燃烧着,释放着暖意的光泽。一道道认知的盲区,就这样被照亮了。
人们普遍认识文体还是在80年代。被世人喜欢的散文家多有特有的文体,鲁迅、周作人、张爱玲、张中行、汪曾祺、孙犁无不如此。当代有文体特征的作家不多,能在文字中给人思维的快乐的人,大多是懂得精神突围的思想者。李健吾、杨绛、唐弢、王蒙、谷林、赵园、李长声在写作里贡献给人的都是新意的存在。文学的变化,一定意义上是文体的演进,不能都说是进化之声,可是独特的独语是无疑的。
那些有过翻译经验的人,在写作上是有表达的自觉的。李健吾的作品不多,可是词语里是隽永的质感。法国文学的绵软多少感染了他。杨绛的随笔不动神色,西洋人的精致与东方人的顿悟在她那里形成奇俏的笔意。李长声的短文有着日本小品的寓意,在什么地方也承袭了周作人的调子,散淡闲情里跳出的是趣味。
至于周国平的深沉的歌咏,也可能是受到尼采的启发。他译介尼采时的激情,后来在自己的随笔中也有。他文字的流动感似乎也是受益于域外艺术的。
这使我们想起80年代人们对双语问题的讨论,在单一背景下,文字的表达是有限度的。人们对鲁迅的译介意识对其文本的辐射力的认识也是那时开始的。可是当时能在此领域给人惊喜的作家,还为数不多。
散文随笔、读书札记,是古已有之的文体。大凡有古典文学修养的作家,在文笔上自然有厚重的地方。文体家的妙处是常常能从旧的遗存里找到呼应语。赵园的文字就有五四气与明人小品味儿。她的清纯与悲悯交织着一个远远的苦梦,唱的是知识群落的夜曲。
金克木的读书札记,有印度古风与旧文人的厚实,在他的漫步里,伟岸的思想之风徐徐拂来,畅快而自由。舒芜的杂感有平仄的韵律,他知道白话文也脱不出古文的影子,所以在谈天说地时从来不忘与历史的对话。何满子、王春瑜、黄苗子、朱正也不乏明清狂士之风,常常也仗了古典文学修养的优势。
文体是精神的存在形式,不妨说也是一个人气质的外化。40年代后,新华体横扫一切,后来是毛泽东体、样板戏体等流行于世。这些语体都有点阳刚之气,带着排山倒海之势。可是这三十年发生了实质的转变,宏大叙事之外的细小的东西多了,不都是史诗的神往。当一个人开始用自己的生命感受切身地表达自身时,那文字也许是有奇力的。所以,我们的作家一点点从此摸索,回到自己的世界,尽收天下甘露,成一家之言,诚为幸事。
青年的面孔是这些年散文写作的庞大的队伍。90年代后期,一些更年轻的作家显示了他们的写作才华。各类青年文丛就推出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作者:余杰、王开岭、摩罗、李大卫等。另一些有特色的青年人也不断推出自己的著作,祝勇、周晓枫、安妮宝贝、于坚等都开始走进读者的视野。
这是无所顾忌的一代,他们许多在默默地写作,形成了青春的气韵,各自有不同的路向。给人最深的印象是没有散文腔,天马行空地游走着。自由地阅读与自由地书写,在这一代开始可能了。
思考的快乐也未尝没有给他们大的忧患。在回眸过去的一瞬,他们无法绕过历史的一页。所以那看人的目光就有了隔代的沉静,有时甚至无端地消解历史的黑影。不过他们的承担也照样有前人的大气,未被琐碎的羁绊所囿。有时未尝没有愤怒的激流,"愤青"的称谓其实是一种舆论的责怪和默许。如果没有他们的身影,我们的文坛将是何等的单调。
在各类风格的作品行世后,青年人已有了自己的生态网络。他们不再惊奇什么,也不必去为语境焦虑。于是回到内心,真实地坦露,有趣地往返,游戏的一面也出现了。有人惊奇于安妮宝贝的独异,在这位作者的文字前,旧有的理论解释似乎失效,那个合乎青年读者口味的著作,昭示了汉语的私人功能的各种潜能。
而这一切都是在网络上实现的。网络写作日趋活跃。各种博客的文体跳进文苑。它们表现了迅速性、个体性、无伪性等特点。许多媒体在其间发现了一些新人,连边远地区的青年也加入网络的大军了。
那些匿名的写手在网络上创造了许多阅读奇观。他们不在意自己的荣辱,可是文字轻风般吹来。大胆的猜测与无边的神往,使文字拥有了另一种味道。他们创造了新词语,有些表达式只有一些群落才能知晓其间的含义。也许那些文字还幼稚和简单,可是它们是从内心无伪地流出来的,新的语词已丰富了我们当下的语言,对自我经验的演绎,大胆的袒露己身,其实是新的价值理念的萌动。网络语体的层出不穷,能否影响未来也未可知。
网络语言在颠覆那些格式化与标准化的书写。文章越来越不像文章的时候,也许会出现真的文章。只是我们还需要时间等待。
散文的世界广矣深矣,岂可以一种语体概括?就我的经验来说,闲适的笔触不易为之,狂狷者的笔锋更难,因为可以刺痛我们的躯体,使人不陷在自欺的麻木里苟活。在这些年所阅读的作品中,有几个人令我久久难忘。这都是些思想者类型的作家,他们灼亮的思想曾被世俗的声音掩埋着,至今也未能朗照于一切。可是他们对知识阶层的影响力,是别一类人所不及的。
王小波以小说闻世,可他的随笔惊世骇俗,智慧与幽默表述得淋漓尽致。他的文字没有做作的痕迹,是心灵的自然喷吐。伪道学被颠覆了,帝国心态被撼动了,奴态的语言被洗刷了。王小波的语言常常是文不雅驯的,似乎是坏孩子的句式,可是在嬉笑怒骂里却有大的悲悯,那神来之笔让我们体味到非正宗语体的伟大。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清道夫之一,其锋芒起到了思想界许多人无法起到的作用。我阅读他的文章时,常常发笑。我知道那是在笑别人,其实也在笑我们自己。这是只有在读拉伯雷这类作家的作品时才有的情状。
李零是另一位值得反复阅读的人物。他的文字和王小波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在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他有许多创见,功底是深厚的。可是他没有学院派的呆板气与模式化,心性散淡,幽默滑稽,而思绪漫漫。比如他讲孔子与孙子,就有胡适与鲁迅那样的眼光。
文字也是清淡平和,而颇有力度。有时直逼核心,有六朝人的清脱。《花间一壶酒》、《放虎归山》等书,多是奇笔与妙笔。放浪形骸之外,有个体的无边的情怀。他是少有的得到五四真意的人。我在读他的文字时,就想起钱玄同的诙谐短章,真真是有狂人之风的。我们在读这样的人的作品时,才知道知识的力量。现在有此类风骨的人,几乎不多了。
比李零稍小一点的汪晖,早期的散文很幽玄、灵动。写人与写物,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他的思想和诗意的感受是连为一体的,整个文字有哲思的气象,情感像一道激流穿梭在夜的世界,很有质感和意味。后来因为专注于理论思维,这样的随笔写得不多了。
李敬泽也是个很有穿透力的思想者。他的文学批评爽朗大气,有很好的感受力,而散文也洋洋洒洒,往返于感性与理性之间,世间的冷热、人情的深浅都在缓缓流动,滋润着读者的心。与他相似的还有南帆、郜元宝、张新颖,在自己的世界里把学识与诗情笼为一身,绝没有平板的呆气。当情感渗着思考的时候,我们读出的不是简单的抒情,而是生命温润的状态。
我常常感动于这些思考者的文本。在普遍缺乏自省的时代,几个清醒的文人给世界留下的不仅仅是几段句式,而是睁了眼的梦想。有了这些文字,我们的生活便不再那么粗糙了吧?
如果上述的描述也算一种掠影的话,那么三十年间的散文给我们留下的至少是以下几点印象:
一、文学从没有离开对现实的关注,受到读者青睐的人,大多是远离"瞒"与"骗"的人,直面的文学还是最鲜活的文学。
二、个人主义的萌动,才从真正意义上撼动着伪道学的艺术。五四新文学的这个传统,虽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可是它对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三、智慧的召唤与趣味的滋养,是散文生长的土壤。我们现在的作家,能在此有独异贡献的还不多见。"载道"的传统大于"言志"的传统是我们的悲哀,未来的写作照例面临着这样的突围。
四、年轻的一代已浮出水面,新锐们已显示出比父辈更热情和自我的意识。"人的文学"在他们那里开始成为可能。而对历史的惰性的跨越,如果没有对前人智慧的借鉴,也许失之简单。丰富自己依然是一条苦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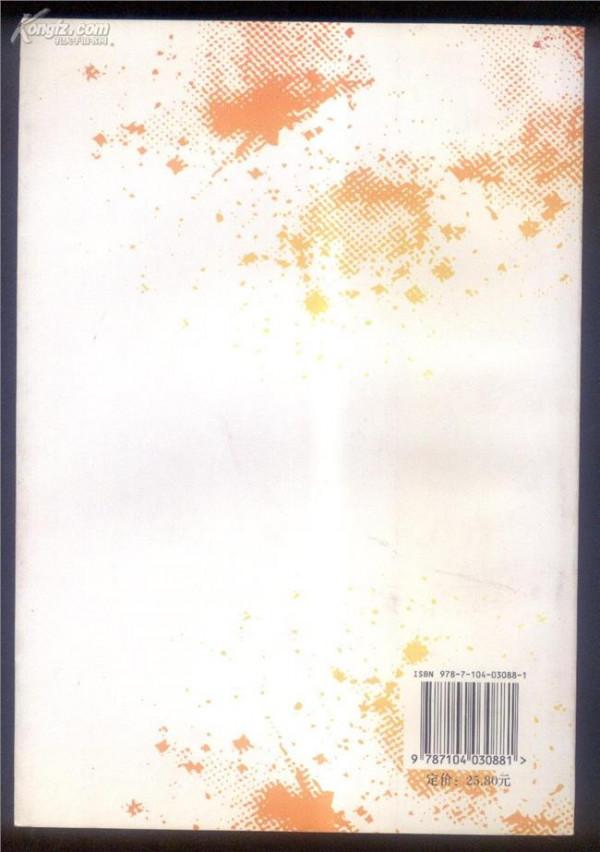











![李靖飞老婆 【陆树铭妻子】孙彦军陆树铭李靖飞]孙彦军妻子](https://pic.bilezu.com/upload/d/60/d60a0c85f1bdcb448a01949ef012431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