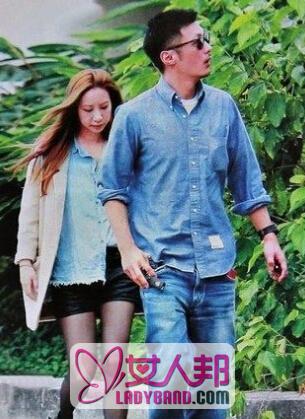中国好歌曲舒克淘汰 赵牧阳怎么被淘汰了|中国好歌曲
1994年春天,魔岩文化同步推出了三张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和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魔岩三杰”从此成为中国摇滚史的一个重要符号。2014年冬天,一个手握鼓棒的男人,戴着压得很低的鸭舌帽走上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的录制舞台。歌曲表演结束,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赵牧阳”时,节目导师刘欢和羽·泉陡然从座位上站起,海泉瞪大了双眼问他:“牧阳老师您怎么会来这儿了?”而刘欢甚至来不及跟他打招呼,就急急忙忙地请他“把帽子摘一摘,我们看一看”。
节目播出后,译者陈震发微博感叹:“如果《黑梦》《在别处》这两张专辑里的鼓不是赵牧阳打的,还会如此叩动人心么?我真的怀疑。”低苦艾乐队、痛仰乐队、周云蓬等正在活跃的独立音乐人纷纷转发这条微博,许多当年的摇滚乐迷也在微博下留言感慨。他们好奇,赵牧阳——这个曾先后加入过鲍家街43号、超载、苍狼、呼吸等摇滚乐队,并参与窦唯《黑梦》、许巍《在别处》及张楚《姐姐》等歌曲录制的“摇滚鼓王”——他消失的十几年,到底去了哪里。
录了百张专辑,没拿过一份版税
12月23日,“鼓三儿”张永光去世的消息让许多音乐人和乐迷震惊,事实上,就在两天前的21日,赵牧阳录制《中国好歌曲》节目时,刘欢还曾提到这位著名的摇滚鼓手:“我们中国有几个数得过来的摇滚乐队的优秀歌手,从当年的三儿到马禾,赵牧阳在里面算比较年轻的。”年轻时的赵牧阳,曾经向当时就已经颇有名声的前辈鼓三儿请教:“我刚到北京的时候经常去他那里看他打鼓、学习。”那时的赵牧阳,刚刚被常宽从西安带到北京,加入常宽的宝贝兄弟乐队做鼓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和现在不一样,三环都没有,只有二环,乐队也就数的过来的几个,宝贝兄弟是其中之一。刚到北京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赵牧阳住在常宽家里,吃常宽妈妈做的饭:“我还算走的比较顺利,不像其他乐手会没饭吃没地方住。
”至今回想起来,赵牧阳依然觉得那时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虽然不能挣到很多钱,但每天都活在音乐中,每天都在和乐队的伙伴做音乐。”他们常常去沙龙开party,乐队们轮流上台唱歌、玩音乐,卖票给观众,收入场地拿走三成,剩下的给乐队,乐队大家一起来分这些钱,“演出完可能一个乐手能分到几十块钱,分到30、50就算可以了。
”然而,这些薪酬并不能支撑赵牧阳在北京的生活。1989年,他被文化部特招进入东方歌舞团担任鼓手,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00,可在那儿呆了三年之后他还是决定离开:“歌舞团会去国外演出,或者就是一些外国使者到中国,我们去给他们演出他们国家的曲目,民间的音乐非常少,最后我不太喜欢,我就离开。
”东方歌舞团三年,赵牧阳唯一庆幸的事,就是每天都有足够的时间去练鼓。
当时摇滚圈很缺鼓手,有些乐队在找不到合适鼓手的情况下甚至只能用鼓机排练,在这样的环境中,拥有精湛鼓艺的赵牧阳被很多乐队请去担当鼓手或是参与专辑录制:“我可能进棚比较快,在录音棚里不耽误时间。”在北京的那些年,赵牧阳前前后后在100多张专辑里敲下了自己的鼓点,尽管如此,他的经济情况并没有好转:“每次都是一次性付给我费用,我也签过那种合约,说有回报那种,但我从来没拿到过钱。我可能录了有100多张专辑,但我没有拿到过一张专辑的钱。”
黄金时代的分崩离析:“因为人没办法左右金钱”
“以前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鼓手,参加过很多的乐队,录制过很多专辑。每一个乐队组成的时候,大家都奔着一生去的,要用一生去对待这个乐队、对待自己。但是一个一个地解散,2000年是最后一个乐队,鲍家街43号。”这段赵牧阳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说的话,道出了许多当年摇滚乐手的心声。
在那个疯狂燃烧又轰然倒塌的摇滚黄金年代结束后,从激情中回过神来的中国摇滚音乐人和歌迷蓦然发现,那么多留名中国摇滚史的乐队,几乎没有一个活到现在。“你没法改变的,乐队解散都是因为公司,它只签主唱,不签也不负担乐队,所以只要公司一介入,乐队就会解散,当时中国没有一个乐队长久,”赵牧阳回忆。
有一种说法是,在早期唐朝乐队和黑豹乐队时,唱片公司仍然和整个乐队签订合约,但在窦唯离开黑豹乐队之后,唱片公司损失惨重,为了减少风险,他们开始只签主唱不签乐手。
这种说法无从考证,但从窦唯离开黑豹后组建的乐队“做梦”开始,唱片公司就开始只与窦唯签订合约,不过仍然会向“做梦”其他乐手支付一定生活费。作为“做梦”乐队鼓手的赵牧阳也收到了这笔费用,不过在他曾加入过的所有乐队中,也只有“做梦”和之后腾格尔的苍狼乐队所签的唱片公司会定期给乐手一些钱来维持生计:“这都是海外的公司签的,当时好像是台湾的公司,他们会考虑乐队的基本生活费用。
”
不出专辑的时候,主唱和乐手们就窝在一起排练,许多乐队的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排练中一点点“磨”出来的:“很多时候主唱出一个小的动机,就是一个简单的旋律,甚至连歌词都没有。乐队就用这个简单的旋律去发展,最后慢慢完成一个作品。”放在现在来看,那时的乐手们其实替主唱完成了编曲、甚至一部分歌曲的创作工作,但在当时,很多乐手并没有这样的概念:“编曲有的时候写乐队编曲,有的会写(主唱)自己,都有,当时不知道有那么多细节,组乐队没人分得那么清,公司进入后才把细节清楚化。”
“我没路可走了”
虽然十年来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出现过,但赵牧阳其实一直没有离开音乐。在《中国好歌曲》亮相之前,赵牧阳最近一次的影像资料来自于三年前一个名为《走近独立音乐人:张力和他的朋友们》的迷你专题片。拍摄这个专题片时,赵牧阳正在上海朱家角短暂停留,于是我们在视频里看到,赵牧阳拿着他的三弦,戴着一顶草帽,在水乡古镇的街道上四处徜徉。画面外的记者问他:“你觉得自己会一直坚持下去吗?”他笑着回答:“我没路可走了。”
鲍家街43号解散之后,赵牧阳回到了老家。“人在最失落的时候,只能回到爸爸妈妈那里。”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这位曾经的“鼓王”留下了曾让他在京城扬名立万的架子鼓,背上一把三弦,开始了五湖四海的流浪生涯。在《张力和他的朋友们》中,独立音乐人张力曾评价赵牧阳“行走在整个中国,有点像苦行僧”,而三弦之于赵牧阳则“像长在他身上一样”。赵牧阳把他的三弦称为“我的爱人”。这把三弦原来的主人是赵牧阳的好友、因癌症去世的野孩子乐队吉他手小索,小索去世三年后,赵牧阳回到北京取走了这把失去主人的三弦:“打开的时候上面都有青苔了。我给他换了套新的弦,然后带着他。”
流浪歌唱的日子是孤寂的,和在北京组乐队的艰苦不同,赵牧阳形容这种状态下他“心里是空的”,“没着没落,很难过”。一次在重庆,辛辛苦苦卖唱三天,他却总共只收到了29元,多年来现实的沉重、经济的压力在那时积压在他的心口,他问自己:“我是不是要放弃,选择另一种生活。”心里闷得慌,他走出暂住的客栈出去闲逛,刚好遇到了另一个正在弹奏的街头艺人:“他一直在弹一个solo,可能弹了十几分钟,我一直等着看他怎么不张口唱。”失意落寞的赵牧阳刚要转身离开,街头艺人却恰好开口,“他张口唱,我的心就碎了,他唱的是我写的第一首歌叫《流浪》,我觉得是他提醒我不要忘记。有时候自己说不清楚,当你崩溃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外力让你坚持走下去。”后来他在黄河边写出了这首登上《中国好歌曲》舞台的《侠客行》,这首歌来自于他多年坎坷对生活的领悟:“不管生活各方面再艰苦,我应该像侠客一样。”
宁肯来打鼓也不愿意来参赛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赵牧阳没有稳定的住所和收入来源,他不愿意为了利益去做任何违背本心、违背他音乐理念的事。“也不是音乐不能维持稳定的生活,如果你安下心去做,衣食可能不会有忧愁,但很多音乐可能偏离了你的根本,它不是我喜欢做的,我就不愿意去进入,很多让我去做一些评委,选他们当地的音乐或是乐队,湖南、陕西都有,但跟我的音乐没有太多关系,我也不愿意去做,都会拒绝。”
其实,《中国好歌曲》也曾是他拒绝的对象。在做第一季节目时,导演组就曾联系过赵牧阳,但当时赵牧阳对《中国好歌曲》这样的电视节目并不了解:“当时选秀太多了,我觉得很多都是有内情的,提前安排好。”当时导演通过赵牧阳的一个朋友邀请赵牧阳参加节目,她至今还记得那个朋友告诉她的赵牧阳的回复:“他说他宁肯来我们这儿打鼓也不愿意来参赛,还说让我们别丢人现眼了。当时心里挺委屈的,但还是很敬佩他,因为他跟我们想的一样,是个有根骨的音乐人。”
第一季“好歌曲”播出后,看了节目的赵牧阳对《中国好歌曲》有所改观,加上他的朋友李夏、灰子都参加了节目,当第二季《中国好歌曲》导演组再来邀请他时,他欣然同意。录制时,这位“鼓王”在舞台上对节目导演表达了歉意:“我去年还把导演骂了一顿,我不知道去年谁跟我联系,我非常非常歉意,今天给你道歉。”
喜得麟儿,漂泊多年终能安身
2013年,赵牧阳为凤凰边城音乐节担任音乐总监,邀来了哥哥——著名音乐人赵已然、何勇、宝贝兄弟等老朋友来担任演出嘉宾。8月24日晚,边城凤凰暴雨如注,赵已然抱病演出,弟弟赵牧阳在背后为他撑着伞。台下的乐迷在雨中忘情呼喊两兄弟的名字,台上的赵老大拨动琴弦,唱着那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在缀着雨幕的夜色里,坚持唱完整首歌的赵已然抖心抖肺地咳嗽着,如今的他还在老家养病。很多人看完这个演出视频感动得流泪:“老早就听说老赵病了,不少民谣圈子的人都在帮忙救助。看完这个视频,感动的哭。我只想说,在他眼中,音乐已经高于一切。”
音乐节结束后,赵牧阳在凤凰停留了三个月。他每天在自己学生开的小客栈里吃饭,学生亲自给他烹饪饭菜,有一天,学生临时有事外出,正好客栈里有几个刚毕业、来凤凰游玩的女大学生在做义工,他便请她们为赵牧阳做顿饭。这几个女大学生中的一位,后来成了赵牧阳的妻子,再后来又为他生下了孩子。再如今,赵牧阳和学生一起在山东临沂开了一所音乐学校,教导一些年幼的小孩乐器和音乐,把沉迷于网络的90后、00后从虚拟世界拉出来,在音乐中成长。这位曾经漂泊不定的“鼓王”,终于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
谈起窦唯、李延亮当年这些音乐人和乐手如今从台前转型幕后,赵牧阳很能理解:“做乐队他们也没法生活,唱片业卖不到钱。”但赵牧阳同时很高兴这些过去的伙伴依然在做音乐这个行当:“他们做音乐的路没有停止,他们还是在做,摇滚它就是一个艺人的生活方式,在那一刻真实的唱给大家,那就是摇滚,没有定义。李延亮他们现在不做这个了,但他们只要坚持做音乐,那就是摇滚。”
成为人夫和人父,这位曾经桀骜的艺术家对于未来看得十分豁达:“资本对音乐的影响是没法改变的,你不能左右,只能放手。但不要放掉自己,坚持往下走,一切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