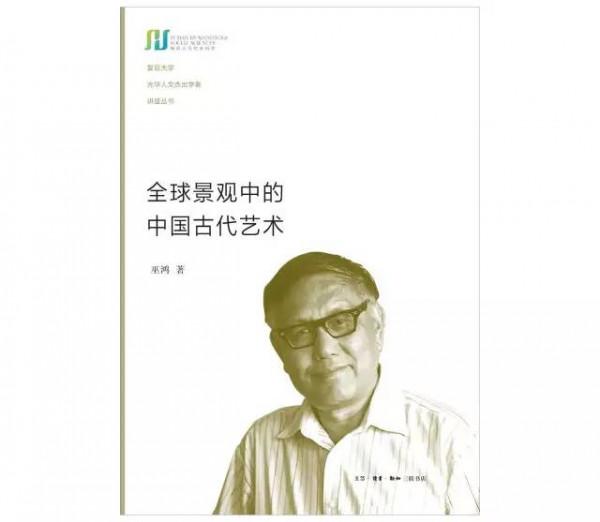巫鸿空间 空间的乌托邦——巫鸿的OCAT年度讲座与“关于展览的展览”
“空间的美术史”,是巫鸿为他今夏在北京OCAT研究中心的系列讲座拟定的标题,这个标题以提纲挈领的方式,对他多年来的中国美术史和当代艺术研究工作做出了精辟的总结。正如巫鸿在讲座开篇所说的那样,通过“空间”这个概念,他将自己历年的研究工作在方法论的高度上进行了整合。
对于巫鸿来说,处于方法论层面上的“空间”概念,就像一座桥梁,沟通了他的横跨中国美术史两端的研究工作,向人们清晰地展示出了他的古代美术史研究和当代艺术研究、展览策划工作之间的连贯性。此后,我们不再说巫鸿是一个研究跨度大、涉猎面广的学者,而应说巫鸿是一个有着特定的视角和兴趣,并将这种视角和兴趣沿用到极为多元的研究对象之中的学者。
同样,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了这个年度系列讲座和同期在OCAT举办、由巫鸿担任策展人的展览“关于展览的展览”之间的连贯性、乃至整体性。
那么,什么是巫鸿所说的“空间”?在尝试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时,巫鸿引用了海德格尔的看法,认为“空间”并非自在之物,而是由存在物互相关联所构成的一种关系,也可称之为“空间化”。比方说,对于古代器物的理解,应该考虑到器物实体与包裹着它的虚空之间的互动,以及器物在其历史语境中与其他物体、主体、文化情境之间的关系等。
这些关系即构成了空间,它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非但对象依存于它,它本身也是在与对象的互动中形成的。
很显然,被置于美术史方法论层面上的空间,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可以从对一个特定对象的具体分析,扩张到对各种语境、关系的研究。巫鸿历年的工作表明了这正是他努力的方向,在“空间”在这个框架中,他展开了对墓葬、卷轴、画屏、当代艺术等多种对象的多维度、多层次的理解,凭借深厚的美术史功底和过硬的哲学修养,将形式研究、图像阐释、符号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多种阐释方法收纳进来。
正如他在讲座中提出的:“空间”可以打破传统的类别、沟通作品与图像、将艺术的内在和外在属性综合起来,构成一片海纳百川的广阔天地。
但是,这个庞大的架构也内在地蕴含着一种风险:它具有极强的整体论倾向,很容易将研究对象预设为一个整体,再从这个倒转的视角出发,试图找出不同的“部分”之间有意义的关联,从而导致过度阐释。
正是这种潜在的风险,使得图像学研究常常受到质疑,而巫鸿的研究思路、尤其是他的古代美术史研究思路,本身就带有很明显的图像学痕迹。例如他在讲座中就古代美术研究提出的“总体空间”三段式,尽管并非图像学三段式的翻版,其思维方式却与图像学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
巫鸿本人是一位极为务实和谨慎的学者,在对“总体空间”进行描述时,他特意提出这种方法并不具有普适性,而是必须有一些先决条件。
但尽管如此,这个扩张性极强的“空间”概念还是引导他做出了一些推演:在他试图将“总体空间”的概念从一个特定的墓葬推演到墓葬与其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与存在于其周边的其他艺术品之间的关系,乃至与一个特定地域的所有艺术品、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时(例如他在讲座末尾提出了应该理解一种作为地域美术整体的“敦煌艺术”),过度阐释的潜在风险就显露出来。
Wu Hung 巫教授
Wu Hung 巫教授
如果说巫鸿的“空间”在属性上近于“关系”的话,它也并非等同于关系,二者之间有一个本质区别。空间是一种被结构起来的关系,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实体,或者说,它可以在实体的层面上落地。正因为如此,巫鸿对于画屏的研究,可以落实为艺术载体的物质性,而他对于当代艺术的考察,则可以落实于对展览空间的分析。
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巫鸿对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特殊兴趣。正如“关于展览的展览”这个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这个展览的关注对象并不是90年代当代艺术的整体,而是其中的一个特定问题,即“展览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就是对90年代的当代艺术与其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从一开始,巫鸿对当代艺术的讨论就经常围绕着展览来进行,他关注展览空间的选择,关注展呈方式与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也关注展览与观看主体之间的互动。
他始终认为,展览问题位于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这个论断包含着两个层面:其一是指90年代的当代艺术参与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为中国当代艺术寻求一种可被常态化的展览空间与机制;其二则是指90年代的当代艺术十分关注借助展览空间的选择和组织,来介入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关系变迁。他还指出,对于展览空间的这种关注,与90年代的当代艺术日益注重本土经验、出现了“国内转向”的趋势有关。
“关于展览的展览”似乎是对巫鸿的这一系列思考的实体化。它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开篇处展示了一些90年代举办的当代艺术展的历史文献,主要包括展览海报和邀请函等,随后,以1996年末到2000年之间举办的12个展览作为样本,展出了其原始手稿、影像资料、出版物等。
这12个展览基本涵盖了90年代曾使用过的各种展出空间,包括公共美术馆、私人博物馆、商业空间、内部交流空间、非空间等,凸显出了展览空间的多样性与实验性、其与社会语境之间的紧密互动、及其介入社会的迫切愿望。
第二部分是一个“展中展”,实际上是对巫鸿2000年在芝加哥大学斯马特美术馆策划的展览“取缔:展览中国实验艺术”的重现,而“取缔”本身则是对冷林1998年在北京太庙策划过的一个流产的展览“是我”的再现和研究。
巫鸿曾经发表过大量的文字,来阐述“取缔 ”和“是我”之间的关系,提出:该展在开展前被临时取缔这一事件,使得展览空间发生了转换,从一个室内的展览变成了一个室外的公众活动,而“取缔”通过对这两重空间的象征性呈现,探讨了展览、艺术家、策展人、公众、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互动。
因此,总体上来看,“关于展览的展览”似乎是以一种从全局到个案层层推进的方式,对90年代当代艺术的展览问题做了“空间”研究。
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层面。进一步的观察会发现,被巫鸿尽量以中性化的方式加以描述的展览空间,实际上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指向性,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12个展览的选择中。通观这12个展览,我们会发现,其中有6个都有过被勒令关闭的经验;而在未曾有过类似遭遇的另外6个展览中,则又有3个是面向极小范围的特定人群、在相对私密的空间中举办的交流展,1个是根本没有展览实体的 “非空间、非展示”;剩下的2个展览,都使用了商业空间,而且展出时间极短。
看得出来,在巫鸿对90年代当代艺术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的观察中,当代艺术与制度框架、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被当作了重点。
对于这种倾向,我们应做如何观?考虑到90年代当代艺术的复杂性,任何单向度的考虑都必定是过于简单化的。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一方面,当代艺术展览与制度、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是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尤其在90年代下半叶,展览多次被关闭的经验,使得寻求可以常态化的展出渠道成为当代艺术的工作重点。
而另一方面,对这类经历的反复陈述又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很容易在一种后殖民视角中被捕捉,尤其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成长是与国际策展人、赞助人的介入密切相关的,而这种介入又绝非中性的。
正如巫鸿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在90年代,国际艺术界的带有特定视角的强势介入已经引起了中国当代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的警惕。
他们注意到,这种介入往往将中国的当代艺术扁平化为一种政治和文化符号,非但遮蔽了其丰富性,也强行赋予了它一种意识形态性,使之简化为国际舞台上的“文化景观”,而90年代的“国内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自觉意识来推动的。
如何处理好这种紧张关系,是任何表述、呈现90年代当代艺术的努力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尤其是,不同的接受语境将导致不同的解读。比方说,2000年在斯马特美术馆举办“取缔”,和2016年在OCAT举办“取缔”,尽管展呈方式、空间研究方案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其接受语境却是不同的;又比方说,同样是2016年在OCAT举办“取缔”,设若它是单独呈现的,则又与它和12个以意识形态张力为重点的展览同时呈现,有着不同的意义。
至少就目前而言,从“取缔”两次被呈现的结果来看,我们只能说,尽管巫鸿有着极为细致和谨慎的学术态度,尽管他竭力将“取缔”描述成一种空间研究,他终究还是未能避免其中的意识形态指向性,也未能避免自己的工作被嵌入后殖民的框架中。
原因何在?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尽管巫鸿能够全面、细致、深入、具体地考察中国当代艺术,但他的工作首先是从一种预设的视角来进行的。也就是说,他已将国际当代艺术预设为一个中性的结构,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套与国际平行的结构。
尽管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需要迎合国际社会的期待和标准,但由于结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标准,因此,只要处身于这种结构之内,那些立足于本土、关注日常经验的作品和展览,依然会在一个特定的框架中被捕捉,只不过,这不再是以简单的文化符号为依托的框架,而是由特定的哲学视角和方法论所缔结的框架。
这让我们立刻想起了巫鸿的“总体空间”。这个概念套用自瓦格纳的“总体艺术”,但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绝不仅仅在于一种字面的借用,关键在于,两者同样有着整体论的基底,而这个基底终将导向一个理想世界,更恰当地说,它们的起点本身就是一个理想式的预设。又或者,我们再进一步:“预设”本身就标识着一个理想国的存在。
时隔十余载,反观90年代的当代艺术,我们看到,当初所追求的那些目标,譬如当代艺术展出渠道的常态化和多元化,大都已经实现,但其结果却是另一套体系制度,在这套新制度规范的引导之下,当代艺术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被另一种张力所代替,这就是当代艺术与商业、娱乐之间的张力,对此,我们至今仍未看到强有力的反思。
既然如此,举办于2016年的“关于展览的展览”究竟意义何在?作为一个精致的展览、作为对巫鸿十多年前的那场思考的具体呈现、作为对一个历史片段的特定再现、甚或作为对巫鸿的“空间”观念的视觉阐释,这个展览都无懈可击。然而,它未能够提供新的知识、新的观察、新的见解,当我们试图去寻找它与当下现实的相关性,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个落满尘埃的乌托邦。
“关于展览的展览:90年代的当代艺术展示”,展览现场“An Exhibition About Exhibitions:Displaying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1990s”, installation view
1999年1月,“后感性:异形与妄想”展上王卫的摄影装置《水下·三十分之一秒》(1999年)Wang Wei,“1/30th of a Second Underwater”, part of the exhibition “Post-Sense Sensibility: Alien Bodies and Delusion” in January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