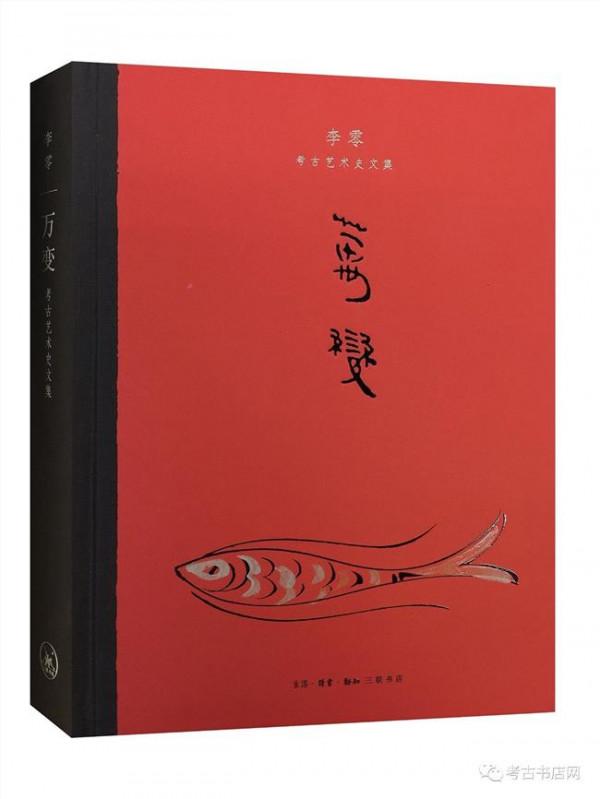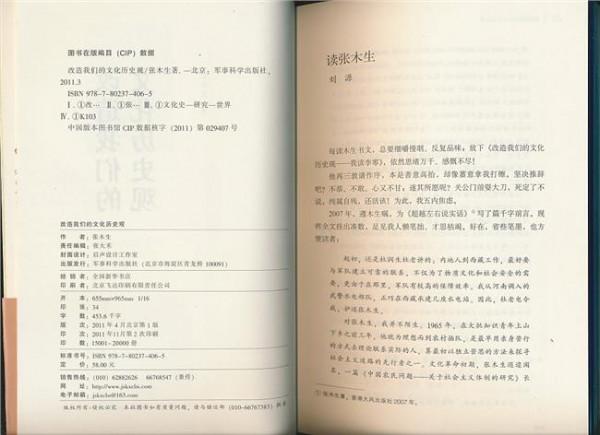巫鸿著作 李零:学术“科索沃”——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
在即将过去的1999年里,恐怕没有任何事件比科索沃战争更触目惊心,既体现世纪末的悲哀,又预示新世纪的不祥。我用“科索沃”这个大字眼为这篇文章题名,也许是过于夸张了。 但当我提笔写作这篇文章时,我却忍不住地要想,它和下面那场讨论怎么那么相像,特别是它在圈子里的理直气壮和圈子外的缺乏共识。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已是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再过两天,我们就要普天同庆这个本来属于西方文化的千禧之年。?
去年8月25日,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Burke Museum)看过一个展览。展览是讲环太平洋地区土著语言的消亡,叫“太平洋的声音”。当我驻足凝望那个名叫“西雅图”的当地土著首领的大幅照片时(他背后还是那座悬在云端的雪山,我从桥上经过每天都能看到的雪山),我何尝不能体会人类学家的叹惋和悲哀。
但是我也想过,假如这些环太平洋地区的千百种语言依然存在,人类从来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统一,我们仍然在为那个“巴比伦塔”的问题苦恼不已,那人类又将如何。
因为无可奈何,所以心平气和。我希望自己能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讲话。?
在研究中国一事上,我们对我们的海外同行(其实也包括我们自己)有很大误解,由来已久的误解。一方面,我们有很强的“诺贝尔情结”,急赤白脸想让人家引用和承认,以为只有得到他们的重视,才算为国家挣了脸,也比国内同行高了一大截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不起他们的研究,握手归握手,拥抱归拥抱,人一走,扭脸就说,“话都说不利索,字都认不全,做什么学问”。?
然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家,我是说很多汉学家,他们可根本就没把咱们当回事儿(包括咱们的看家本事和绝活),他们的学问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差(只要你不是拿中国的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我们要知道,第一,他们的学问是在我们之外,用另一种语言,另一套规范,从教学到研究都运转自如、自成系统的学问,并非离了我们就活不了;第二,他们人数虽少,却坐拥“国际学术”而自大;我们人数虽多,却只有地区的资格(东亚研究的一部分),“小”、“大”的关系是以“位势”而定(“外”总比“内”大);第三,他们对我们看重的是材料而不是研究(但即使是从材料的角度看问题,他们也常常觉得我们还不如日本,因为我们“只有零件没有组装”),我们认为的优势,异地而观之,也许反而是劣势所在。
比如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局者”(insiders)视角,叫他们一说,倒成了“偏见”的别名(“当局者迷”),反而不如他们这些“局外人”(outsiders)来得客观公正(“旁观者清”);我们自以为绝活的文献考据,在他们看来,也是“传统史学”的尾巴割不断,“迷信书本”的恶习改不了。
就连王静安先生提倡,我们谁都不敢怀疑的二重史证”,他们也不以为然,觉得削足适履(考古是“足”,文献是“履”),把好端端的考古材料全都糟蹋了。
在近代史学的开辟过程中,我们有过许多矛盾的选择,思想的源泉出自许多前辈,而并不只 是顾先生一家(今天也是如此),但在感情上,在心理上,我们的西方同行,他们却是一门心思,最能认同的就是顾颉刚先生。
西方学者对我们的批评很厉害。很多话在他们是“说者无心”(他们对自己的说法太自信,甚至一点都不跟我们“见外”——尽管我们把他们叫“老外”),到我们这儿就成了“听者有意”(我们太容易把他们当作“无知”,因而也太容易觉得他们“狂妄”,动不动就感情 受伤)。
比如我的朋友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他在几年前用英文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癖》。这篇文章的中文译文就使很多读者深受刺激(包括我自己)。虽然罗泰一再跟我解释说,他的讲话对象是西方学界而不是中国同行;他的目的是让西方学界了解中国考古,而不是故意为了伤害我们的感情。?
近年来,同欧美学者打交道,我经常可以听到类似的批评,非常尖锐的批评,这就是中国学术已经“疯”了,已经失去对文献的批评精神,已经倒退回“疑古时代”以前去了(刚刚从日本归来,在那里我也听到同样的声音);“倒退”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作怪,二是我们的民族感情作怪,三是我们孤陋寡闻,太不了解国际学术的“常识”或“规范”,有许多“失误”和“犯规”。
特别是我们这儿有个声势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一 个由中国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流学术队伍(包括中国最优秀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与断代有关的科技专家)率领大家“走出疑古时代”的运动,这对他们的想法似乎是有力证明。
他们认为,这是由官方出钱用于提升和拔高民族自豪感的政府行为(讲炎黄五千年文明,讲龙子龙孙大中华),中国学术的堕落已是明摆的事实。?
西方学者对我们的批评是不是一无是处?我看不是。但他们的理由是不是不容商量?那也未必。我的看法是,恢复自尊,必先放弃自大;没有交锋,也就没有交流。但遗憾的是,尽管中国学者和他们的西方同行在很多问题上看法大不一样(就像瘸子笑瞎子眼睛不灵,瞎子笑瘸子腿脚差劲,背地里的评价都很糟),说到关键之处,躲不过也绕不开,但双方却总也不肯把真实想法摆到桌面上来(聋子式的对话,《三岔口》式的对打)。
只是最近我们才有了一些机会,可以比较系统地领教西方学者的想法。
一是1996年以来围绕巫鸿先生的新作《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下简称《纪念性》),西方学者有一场大讨论(现在仍在继续);二是由鲁惟一(Michael Loewe)先生和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先生主编、十四位欧美学者(都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重镇)执笔的《剑桥中国上古史》终于在今 年出版,书中浓缩了近三十年来他们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系统思考。?
为了让读者对西方同行的想法有所了解,不但了解他们的批评本身,也包括他们的批评方式和学术规范,我们特意选择前者做翻译介绍。?
在正式讨论之前,我先介绍一下巫鸿先生。?
巫鸿是新一代的华裔美国学者,改革开放之后才到美国。在中国,他曾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原来就有研究中国美术和中国文物的背景。后来他远渡重洋,负笈哈佛大学,不但原来的背景没丢,又受到西方学术的训练,毕业后,留在哈佛大学执教,现在是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的教授。
巫鸿不但在中国留学生中很出色也很走运,在美国著名大学得到很高的位子,而且还入围美国学术界的主流,在艺术史界有很大影响。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武梁祠》在欧美曾深受好评。
但这位成功的学者,他既得益于自己的“双重背景”,也受这种背景牵累,正碰到一些前所未有的麻烦。比如他的新作《纪念性》,刚一出版就“走了麦城”,接二连三遭到同行的强烈批评。这就和他的“中国色彩太浓”和不够“国际”有关(虽然读过该书的我们北大考古系的学生说,他们的印象可正好相反)。?
关于《纪念性》的书评,就我所知,至少已有七篇。它们是:?
(1)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的书评,刊于《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21期(1996年),第183-199页。?
(2)美国俄勒冈大学拉齐曼(Charles Lachman)的书评,刊于《亚洲学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ties ),第56卷第1期(1997年2月),第194-196页。?
(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利斯(Robert E. Harrist, Jr.)的书评,刊于《东方艺术》(Oriental Art),第43卷第2期(1997年夏季),第62-63页。?
(4)美国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ur College)戴梅可(Michael Nylan)的书评,刊于《亚洲艺术》(Artbus Asiae),第17卷1/2(1997年),第157-166页。?
(5)捷克国立博物馆柯思纳(Ladislav Kesner)的书评,刊于《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第5卷第1期(1998年春季号),第35-51页。?
(6)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Robert Bagley)的书评,刊于《哈佛亚洲学报》(Harvar 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58卷第1期(1998年6月),第221-256页。?
(7)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杜德兰(Alain Thote)的书评,《亚洲艺术》(Arts Asiatiques),第53期(1998年),第129-131页。?
这七篇书评,除(2)、(3)是简短介绍,对巫鸿给予肯定,其他五篇,都有尖锐批评,甚至干脆就是体无完肤的批判。在上述书评的作者中,罗泰是第一人。他对《纪念性》的批评还比较含蓄,至少一开头先承认“它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第183页),最后结尾也说它“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劝大家不可不读(第199页)。
但他对巫鸿在技术细节和工作方法上的“小疵”,特别是其“中国式的毛病”却毫不客气,该点到的全都点到,可以说是首发其难。
贝格利先生的书评比较晚出。他和罗泰不同。他关注更多的不是巫鸿在细节上的失误,而是巫鸿至今没有改造好的“中国劣根性”,因而在所有批评者中态度最激烈。罗泰和贝格利,他们都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都是巫鸿在美国艺术史界的同行,并被公认是这一领域颇具实力的重要学者。
他们的批评当然很有份量。特别是后者,他的批评不仅更能表达西方学者的典型看法,而且还被认为是“毁灭性的批判”,态度之强烈和语气之挖苦,都可说明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所以在这七篇书评中,我们特意选择了贝格利的书评。其他各篇,因为篇幅有限,只好从略。并且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有关的评论,我们还在贝格利的书评之前加进了一篇秦岭先生撰写的《纪念性》一书的介绍。?
此外,除上述公开发表的文字,在私下议论里,我们也能听到不少类似的批评。只要是西方读者,他们多半都认为,巫鸿的新作确实很有问题。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贝格利的批评在语气上好像重了点,让人觉得过分,但真正的反批评,除去夏含夷力排众议的简短发言,到现在还一篇没有,这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巫鸿的书为什么会引起西方学界的普遍不满和贝格利的“狂轰滥炸”?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可以讨论的只能是学术原因。这里,撇开个人感情不谈(我和巫鸿、罗泰都是好朋友,对贝格利的学问也非常佩服),我想尽量从学术角度归纳我对上述批评的印象:
第一,《纪念性》和《武梁祠》不同,《武梁祠》的对象只是小时段内的单一艺术形式(汉代画像石),而《纪念性》的对象则是从新石器时代到六朝以前的整个艺术史,包括多种艺术形式。作者以“纪念性”为主线来概括这些艺术形式的发展,极易让人觉得费力不讨好。
批评者觉得巫鸿野心太大,成功太小,理论虚构胜于知识推进,反而不如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编写的《中国古代之谜》。8罗森的书只是一部展览图录,但它对艺术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很多最新发现,全都讲到了,干货很多,水分很少,大家可以从中学到真正的艺术史知识。?
第二,《纪念性》的写作手法是属于主题先行,这在追逐理论时髦的美国很普遍(和我们这里的新一代学者相似,巫鸿对各种后现代的理论也是情有独钟),它给人的感觉比较类似我们说的“以论代史”,令人觉得好像“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中国形容酒肉和尚的话):艺术形式的隐显切换非常随意,不变的只是穿行其中的“纪念性”而已。
批评者认为, 它所涉及的各种艺术形式(如陶器、玉器、铜器、石刻、建筑),本来都有较早的来源和较 长的延续,往往是呈并行发展,并无前后相继的关系,作者说什么时候什么艺术形式有“纪 念性”,很多都是任意安排,或者至少很勉强。?
第三,西方语言所说的“纪念物”(monument),通常是指在地面上巍然高耸、赫然可见,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神庙、方尖碑和凯旋门一类东西,即主要与建筑有关的艺术形式。但作者论“纪念性”(monumentality),却把“纪念物”的概念放大,也包括藏于隐秘之处的器物(甚至是很小的器物),他对各种艺术形式的讨论,早期(新石器时代到“三代”)偏 重器物(陶器、玉器和铜器,即书题所说“艺术”),晚期(“三代”到汉魏六朝)偏重建 筑(墓葬、宫室、陵墓、城市,即书题所说“建筑”)。
“器物”概念的加入,不仅让人觉 得对西方语言有“亵渎”之感,而且从技术角度讲,也有很多不便处理,牵强生硬的地方。 比如罗泰和贝格利(他们两位都是研究青铜器的专家)就都认为,巫鸿对中国青铜时代的描 写颇多误解。
第四,也许更重要的是,西方学者批评巫鸿的目标,更主要是集中在所谓“解构永恒中国”,即打破我们习惯上爱说的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他们认为,巫鸿的“纪念性”是为了突出“化外中国”的独特发展,和表现其自外于西方学界的沙文主义情愫。
时间上,巫鸿竟用晚期史料讲早期历史,不讲历史变化,这是犯规;空间上,巫鸿的“中国”太模糊,外部不讲“跨文化研究”(特别是跳出中国版图边界的研究),内部不讲“地区多元 性”,同样是犯规。
特别是对考古与文献的关系,巫鸿的理解就更成问题,他不但把考古的 “大脚”塞进文献的“小鞋”,而且还用文献曲解考古。比如他以晚周文献记载的“九鼎” 传说作早期(早到新石器时代)“纪念性”的象征,在西方人看来就是笑掉大牙的无知妄说 (如果他们能看到我们这里到处铸造的大鼎,他们的气还不定有多大)。
这四点批评,前三点可能有一定道理,但并未考虑作者的初衷,第四点也是一面之辞,未必可以“犯规”视之。我们从最后一点看,当不难发现,西方学者的批评并不仅仅是针对巫鸿,它也包括巫鸿曾经从中受到教育现在也还没有割断联系的学术背景和学术习惯,也包括他还时时引用的中国同行的研究。?
我看,这才是西方学者“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想法。?
对巫鸿的《纪念性》,我想参考上述批评讲一点我个人的理解,“抱了解之同情”的理解。
首先,我认为,在艺术史的研究上,“纪念物”和“纪念物”背后的“纪念性”是个值得探讨的好题目(有点像文献研究上的“经典化”)。巫鸿以“纪念性”作他考察中国古代艺术史的主要线索,从选题的角度讲,是无可非议的(十年前,我听巫鸿先生说他要写这个题目,就觉得很有意思)。
问题只是在于他的处理是否成功。学者认为巫鸿的“纪念物”是东拼西凑,“纪念性”是先入为主,这是阅读该书的人很容易得出的一种印象。但我理解,他之所以要修正“纪念物”的西方概念,并把“纪念性”当判定“纪念物”的标准,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建筑是以土木(而不是石材)为主,它们除宫室基址和城墙基址现在还有一点早期发现,唐以前的东西都已荡然无存,我们在地面上什么也看不见,根本找不到可与西方“纪念物”对等的东西。
10而如果我们以“器物”填充空白(巫鸿之所以用“九鼎”的传说作“纪念性”的象征,原因就在于,他把“器物”的概念引进了“纪念物”),势必会扩大“纪念物”和“纪念性”的范围,从而颠覆西方固有的阅读习惯。
不过,尽管对很多西方学者来说,巫鸿的“纪念物”和“纪念性”十分滑稽可笑,但柯斯纳已经指出,这样的概念并不是巫鸿发明,而是近年来在后现代艺术研究中已经被人接受的“新原则”(第37页),他把“纪念性”从规模大小和时间长短中解放出来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第47页)。?
其次,《纪念性》一书所选择的写作方式可能会予人以怪诞之感,就像很多带有后现代色彩的作品常常会给我们造成的印象一样。艺术史的写法和一般历史的写法一样,大体也分两种:一种是细节描述法,略如绘画中的工笔;一种是主题描述法,略如绘画中的写意。
它们各有千秋,也各有陷阱。此书的写法,作者说是以“纪念性”为“基本发展逻辑”的“个案研究”,前者是强调其一以贯之的主题,后者是表明它并非面面俱到,对各种艺术现象的描述都是有所选择。
特别是“纪念性”和“经典化”的概念相似,本身就包含了“选择”的概念在内。它对各种艺术形式只能挑着讲、跳着讲(像《儒林外史》那样讲),这是受到了主题的限定。巫鸿的书,两种写法都有,但主要倾向是主题描述法,即粗枝大叶的一种。
学者为了贬低巫鸿,每每喜欢拿罗森的《中国古代之谜》作为对比,说这样的书才叫“艺术史”, 而《纪念性》不配。我认为,罗森的书当然是很优秀的图录,但这种比较却不太恰当。因为 主题描述法比细节描述法难度更大,风险也更大,写不好就如同虚构;后者虽比前者容易上 手,也更容易站的住,但它一样有它的缺陷,一样不可能面面俱到,并不能取前者而代之。
我们不能因为对前者的失望,就认为后者才是艺术史的唯一写法(就像我们不能说“写意不成功,当改练工笔”)。?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中国的学术界诚然还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甚至让我感到痛心疾首的地方,但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批评也并非天经地义。第一,他们深恶痛绝的“意识形态”干扰、“民族情绪”作怪,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中国的传统学术,而是拜近代化(或现代化)之赐,受西方的刺激、鼓舞和启发才产生。
它们表面上是与西方学者的“普遍价值”和“国际主义情怀”作对,但实际上却是如影随形,互为表里,水涨船高,与之相伴始终的东西(这是个他们转身跺脚也挥之不去的幽灵,就像马克思称呼共产主义一样)。
第二,中国的学术虽不能免于“意识形态”和“民族情绪”的干扰(就像西方学术同样不能免于他们自以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上述东西的干扰一样),但却绝不应该执此一端,衡量一切。在这方面,他们的“政治挂帅”和我们的“政治挂帅”,同样非常落伍。
事实上,中国近年的学术反思,它的直接动因还是近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而不是对古史的迷信。虽然“走出疑古时代”是由李学勤先生倡言(注意:他并没有自称“信古派”,也没有提倡回到“信古时代”),但他的发言范围却主要是古文字和古文献,真正谈论五千或六千年的文明史,真正以考古发现印证古史传说,其实全是考古学家(从徐旭生到苏秉琦和苏秉琦的弟子),无论批评者还是赞同者,他们都并不是从文献出发(文献只是一种解释系统或参照 系统)。
第三,尽管西方学者说中国学术已经大大退步,但只要不带偏见,谁都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古书年代和体例的认识上,还是在考古文化整体面貌和细节联系的理解上,中国学术都比以前是进步了而不是退步了(相反,西方学者的想法,即使不算“过时”,至少也很“保守”,虽然他们的怀疑态度反而非常大胆)。
事实上,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的不满其实主 要不在史实的了解,而在范式的不同。他们讲的很多规矩,比如:(1)时间上要讲“同期 史料”(谈哪段历史用哪段史料,绝不能拿晚期的东西讲早期),一段是一段,免谈“连续 性”;(2)地理上要对“中国”的概念进行缩水,里面要“瓜剖豆分”(分出其他文化 ),外面要“蚕食鲸吞”(溶入其他文化),坚决反对“大一统”(特别是早期);(3 )认为中国的传说时代都是汉代伪造,“三代”也是后人虚构(夏不存在,商是小国,周也 没有多大);(4)中国的文献只有晚期有效性,早期是“考古学”的天下;(5)考古 不受文献约束,眼睛胜过书本(尤其流行于艺术史界)。
其实,这些“学术规则”都是大 可商榷的东西。?
将来有时间,我们很想和我们的西方同行做详细讨论,限于本文只是一篇介绍,这里不再多谈。
据说,在美国学术界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或习俗,就是作者对别人的批评最好不做辩解和回应(“写出的东西不再属于自己”),学术杂志也一般都不登反批评(和“来而不往非礼也”正好相反)。回答是缺乏风度也很丢脸的事情。但是对于贝格利的书评,巫鸿还是写了《答贝格利对我的〈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一书的评论》。?
记得1998年夏,我和巫鸿在芝加哥谈话,他还向我表示,他并不打算回答贝格利的批评(尽管有人说,“不回答就意味着灭亡”),就像他所“入”的哪个“乡”必须“随”的那个“俗”,君子风度是必要的。可是现在,为什么他又出来回答呢?我想是忍无可忍吧。?
在巫鸿的回应中,我们不难发现,他除去对自己的写作思路和内容表述做了五点辩白,用来批驳贝格利的“曲解”和“武断之论”,在更大的篇幅里,他想表明,他并不是自外于他已加入其中的西方学界,也不是与中国学者的偏见陋习沆瀣一气;相反,他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他的西方同行: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也不问他们是什么族裔(他对罗森和张光直都表达了敬意)。
他认为,贝格利以“当局者”和“局外人”来划分中外学者,以“传统史学”和“考古眼光”来划分中外学术,这都是非常荒唐的想法,充满偏见的想法。?
当巫鸿答应我把他的回应收入这组评论时,他曾向我解释,他的原稿是用英文写作,预想的读者也是英语世界。因为环境不同,读者不同,他在文章中特意有上述强调,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知道,在美国,族裔歧视、宗教歧视、性别歧视都是很大的禁忌。
他不太像我,说起话来,可以口无遮拦,公然置“国际规则”于不顾。不过,陋见以为,这些禁忌,它们对保护弱者固然是有效手段(既可作防范措施,也可作进攻武器),但对“事实上的不平等”却可能起掩盖作用。
因为大家对这类问题往往都是敬而生畏,避免接触,绕着走。比如我读过一本美国人讲脏话(以及种族、宗教方面的禁忌语)的书,叫《危险英语》(据作者说,她写这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说这些“危险英语”,而是让人小心这些“危险英语”) 。
书的作者要讲这类学问,不但一上来先得讲清自己的资格:她是从新泽西来的“慈 祥可爱的老奶奶”,受过什么教育得过什么奖——决不可能教人学坏,而且她还得对自己的每一句话小心留神。
比如什么人说脏话,她敢说男人说脏话(“Men of every social class fr om street cleaner to banker, even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use these words”,p.
5),水手、年轻人和情人说脏话,但不敢说女人或黑人说脏话。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想指出的是,尽管我们不应发泄偏见,侮辱对方,但也不应回避分歧,掩盖真相。
因为尽管中外学术,谁也不是铁板一块,但二者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同,这却是明摆着的事。否则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争论呢?记得北大百年校庆,我们学校在北京香山饭店举办过一个“汉学研究国际会议”(1998年5月5日-8日)。
会议开幕,袁行霈教授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把“文化馈赠”当作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很想和海外同行共享“中华文明的精粹”,其乐融融,有如一家。但我注意到,我们的海外同行,他们在发言中却毫不掩饰,他们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接受不同的教育(包括汉学和汉学以外的教育),因而在很多问题上和我们的看法很不一样。
在那次会议上,夏含夷先生送给我他用中文出版的《温故知新录》(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这本书的前言,一开头就讲了类似的话。我很欣赏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开诚布公。
在我们组织的这组文章中,我们还特意收入了夏含夷在今年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的一篇发言。这篇发言非常令我感动。因为他是地道的美国人,但对中国学术却有“好之”和“乐之”的心情,不像有些汉学家是以毫无感情为学术客观之前提,并以之作为拒绝与中国学术交流的借口。
过去大家常说,Ed是个脾气很大也很骄傲的人。但在当前这场最易感情用事的争论中,他竟虚心降气,首先检讨美国学界的偏见,主持学术上的公道,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另外,可以顺便提到的是,读者要想进一步了解夏含夷的上述立场,大家还可参看他与鲁惟一合写的《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导论。虽然在这篇短文中,我们还不能就该书的细节与西方同行进行讨论,但我们已经注意到,该书不仅和中国学者的想法有很大不同(如他们笔下的“中国文明史”,前后只有三千多年),而且写作队伍内部也同样存在不同想法,主编并没有强求一律。
比如此书的时间范围是从商到秦统一,全书是按“古文献/古文字”和“考古”两两相对的方式来写。
它的两个队伍之间和每个队伍内部都存在矛盾。像二里头文化,从体例上讲,是安排在讲文明背景即史前的第一章,因为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明”只有“三代”中的二代,即商和周,没有夏代。但在这一章里,张光直先生却取中国学者说,承认有夏代。
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先生的第四章是以“商:中国的第一个历史朝代” 为题,但贝格利讲商代考古的第三章却不承认商是统一王朝,宁愿相信它是当时小国林立中 的一个,或者不如说是“安阳文化”(早于殷墟和安阳以外皆非商)。
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巫 鸿、罗泰、贝格利,他们都是《剑桥中国上古史》的作者。他们都把自己不同的看法带到了 这本书中。我理解,两位主编要想协调各位作者的想法确非易事。作为主编,他们应该开诚 布公而又兼容并包。而他们做到了。?
在《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导言中,我们注意到,两位主编曾就中国学界的“疑古”、“信古”之争发表如下看法:考古发现对传世文献的这类证明导致了一种学术观点的产生,即肯定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方面有古老性,它特别流行于中国。
这种观点现在叫“信古派”,即有意同三十年代《古史辨》杂志有关的“疑古派”相区别的一派。从它的某些说法看,这种对古代的迷信无疑是说过了头。因为它们更多地是出自当代的文化沙文主义,而不是学术证据。但比起很多西方学者对这一观点的否定,此类看法的偏见也未必就更多。
尽管有诸如此类的保留,我们还是很难否认这个结论,即近三十年的考古发现,它们主要不是推翻而是肯定了中国古代传统文献记载的可靠性(第10页)。?
他们指出,我们有“偏见”,他们也有“偏见”,彼此的偏见不一样(相映成趣),谁的“偏见”也不一定比谁更多。我看,这才是比较客观的态度,也是比较开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