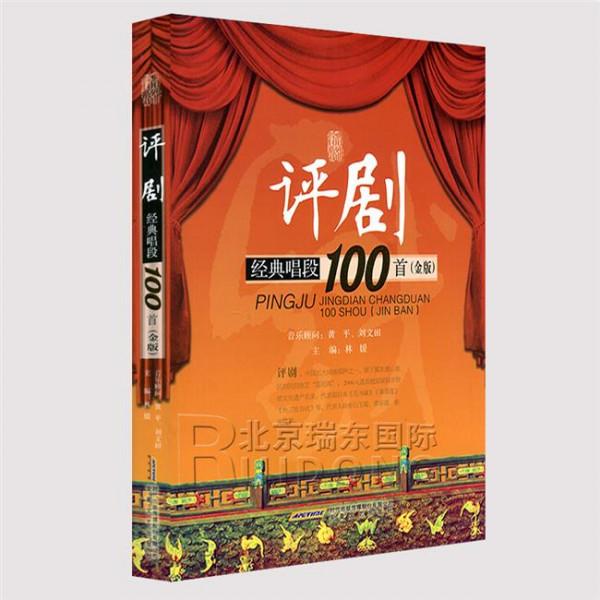冀中星孙志刚 孙旭阳:车上的陌生人——冀中星案采访记
孙旭阳:车上的陌生人——冀中星案采访记
摘要: 7月25日上午11时,一个来自山东菏泽的手机号码打来电话,接听后,对方是一个急促的女声,问我是不是京华时报的记者。我说不是。她追问,你不是京华时报的,可你肯定是记者吧。
孙旭阳
7月25日上午11时,一个来自山东菏泽的手机号码打来电话,接听后,对方是一个急促的女声,问我是不是京华时报的记者。我说不是。她追问,你不是京华时报的,可你肯定是记者吧。
我就报了单位和姓名,对方一听就很生气,说找的就是你,你为啥把我们的车牌号和郑阳的名字给登到报纸上,你不知道车站会报复我们吗?我们小百姓的,敢惹谁?你们报道完了都走了,我们咋活下去你们管不管?
这位女士所提到的车牌号,正属于7月20日从山东省鄄城县汽车站,送冀中星进京的那辆金旅牌大巴。这辆客车共有49个座位,票价140元,每早6点半从鄄城出发。7月20日,包括冀中星在内,它一共拉了47名乘客。
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鄄城两天了。当天,这辆大巴车在北京被丽泽桥汽车站扣下,理由是拉了几只活鸡。这位不知是郑阳家人还是同事的女子认为,以前拉多少活鸡车站都不管,现在却扣了车,明显是因为在冀中星案的报道中,媒体点了这辆车的车牌号,让其招致丽泽桥汽车站的报复。
这位女士要求我删除网上稿件中的车牌号,被我当即拒绝,这确实也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转而,她又要求我过问被扣车一事。对我来说,这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就答应帮她问一下。
没想到几分钟后,同样的号码又拨了过来,是大巴车乘务员郑阳,他纠正了上一位女士的说法,称没被扣车,现在还不知详情,要我先不要惊动丽泽桥车站,“得罪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说完后,他很客气地挂上了电话。
对郑阳,我得承认自己有几分愧疚。我第一次联系到他,是在7月21日下午。当时,我正在冀中星老家村子里转悠。在冀家小院外,远远地就可看到有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在蹲守,守什么,当然是守记者呗。冀中星的父亲,这时也已经被派出所接走,连续好几拨记者都没见到他。我转了几圈,就试着联系那辆进京大巴,看有什么料没有。拨号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冀中星进京过程的新闻价值之大。
我手头的三个号码,来自鄄城县汽车站门口的一家副食店女老板。在见到她之前,我问过汽车站方,问过20多名出租车司机和三轮车主,和其他好几家店主,都毫无结果。她一开始并不是太想帮我查,但我听她说有一个记录很多客车车主号码的笔记本,就买了一瓶冰红茶,站在她的店内,说我从外地过来一趟不容易,请她帮帮忙。
在接待了七八名顾客,卖出去十几瓶饮料之后,女老板看起来心情好了很多,她对我笑了笑,“小伙子,你给我引来不少生意呀。”说完,就从柜台下边扒出一个20年前装潢风格的本子来。
她有五六十岁,眼神不是太好,低着头,用手指捣着纸面,一行行地搜索,嘴里还在轻声念着。这时,我明白了她一开始为何会犹豫,这个足有四五十页的本子上,几乎记满了电话号码,大部分都没有记姓名,而代之以某个地名,显然都是跑客车的。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她一边说一边忙着找。终于,在大概二三十页的地方,她找到了第一个号码,“这个是跑北京的,就是不知道是哪一趟。”我忙用手机拍了下来,刚想转身走。她喊住了我,“别急,还有呢。”又翻了两页,她又找到了两个号码,“这个是另外一趟车的”。
至今,我都非常感激这个与我母亲同龄的女人。她给我的第一个北京大巴的号码,是8点半那趟车的车主,对方得知我是记者,第一句话就是“不关我的事儿,那个老先生上车找他儿,他儿是坐第一趟车走的。北京警察上午也给我电话,问了一两句就挂了”。这位老兄还给我详细讲了拉冀中星那趟车的牌子、颜色和座位数。最后,他又给我提供了该车的随车手机号。
于是,我就联系到了郑阳。他给我详细讲述了冀中星乘车的过程。作为一个乘务员,他尽力想为这个残疾乘客做好服务,他和司机把冀中星抬上车,安置在驾驶座后最宽敞的那个座位上;到了中途的深州服务区,他帮冀中星买了一份鸡块卤面;北京丽泽桥汽车站到站后,他帮冀中星接了小便后,再次抬他下车。
在通话结束前,他不假思索地告诉了我他的全名,“郑阳”。但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和所谋生的大巴的车牌号,将与“冀中星”三个字写入同一篇报道中,招致那么多的惶恐和不安。
有同行曾说过,采访需要仰仗“陌生人的仁慈”。可是,我们对陌生人是否足够仁慈?他们大多被迫卷入某起丑闻或悲剧中,暂时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我曾询问一个在汶川地震中失去父亲的少年,他与父亲最后一面的细节;我也曾守候在一个被前男友沿街散发裸照的女子的家门外,期望能遇到她说上几句;我还曾追问一个同时失去孙女和外孙女的老阿婆,两个孩子中毒倒地的具体时间……
7月21日晚,我完成了3000多字的《冀中星爆炸前12小时》。这篇写作尚显粗糙的报道因故未能全部见报,经官方微博传播后,解答了该案的不少疑点,击破了某些网民对该案超出科幻尺度的阴谋论想象。有同行称赞我的效率,我却清楚真正该被称赞的其实并不是我。
7月25日之后,郑阳和那位女士没有再给我来电话。我那句“有事儿随时找我”的承诺就更像一张空头支票。但愿他们的客车能很快被放行,没有被罚款,每天平平安安,永远满员。
提起客车,冀中星父亲冀太荣印象最深的可能有两辆:一辆是郑阳的那辆进京大巴,儿子冀中星坐着它进京,在首都机场炸烂了自己左手。
另一辆是东莞某个汽车站,北上山东的某辆大巴,在2005年7月14日,冀中星坐着它离开了打拼6年的南方,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这辆大巴,像一面刻满悲愤之词的纪念碑,深深扎根在冀太荣的记忆中。
当时,冀太荣大儿冀中吉和一个亲戚抬着冀中星去坐车,车主嫌一个残疾人太麻烦,好说歹说不让上车。不清楚最后冀中吉如何才求情成功,只是冀太荣提起这段场景,就老泪纵横,在记者面前嚎啕大哭。这辆大巴启程前,见证了冀家哀告的屈辱;到站后,抬下了一个冀家至今挣不脱的噩梦。
7月20日晚10时,我接到部门领导派活儿后,拨了十几遍冀中吉留在网上的号码,一直忙音。到最后,我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我是南方都市报记者,来自广东,现在广东省官方和民众对此案都非常关注,希望他给我回电话。
后来,冀中吉告诉我,那一夜,他接到的电话之多,让他直到天快亮时才有空闲看短信。7月21日早上5点多,他给我拨过来,我当时正在火车上趴在小桌上半睡半醒地煎熬,没有听到。一个小时后,K974次到站菏泽,在地下通道中,我拨通了冀中吉的电话。
一个问题把他几乎问哭,“你会到北京,或者回老家吗?”他稍顿了一下回答说,“不会。我一二十天前刚带着老婆孩子过来,还没挣到钱呢……”可能是出于对广东媒体的信任和期望,他特意告诉我在内蒙古当地办的一个手机号,说网上留的号码是菏泽的,马上就欠费停机了。后来,很多媒体同行都是通过我,才找到了他内蒙古的号码。
然而,与他的信任比,我又能帮到他什么呢?8年来,在散发着恶臭的住室内,前黑摩的拉客仔冀中星学会了上网,他用尚能活动的双手敲击键盘,把自己的遭遇不断往网上挂,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回应。媒体根本不会注意到他的帖子,他的遭遇太常见,没“新闻点”,他的苦难就只好继续陌生下去,孤悬公共话题之外。
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那一声巨响,硝烟尚未散去,舆论战场上已是硝烟弥漫。指责冀中星的人为数并不少,当我在采访间隙看到这些指责,就一直在思考:这些指责对冀中星意义何在?以他残疾的程度,不是他怕监狱,而是监狱怕他。
很多时候,尤其在中国,人们与其说是在争论一个人一件事的是非,还不如说是在表白自我所能接受或忍受的限度。冀中星与其说是做错了事,还不如说是他做的让很多人无法接受。至于他遭遇的能否让人接受,照例被归为另外一个问题。
7月21日上午8时左右,我在距离冀家百十米的地方,截住了从镇上回来的冀太荣。这是一次让不少同行羡慕的相遇。冀太荣刚刚被派出所喊到乡里以躲避媒体。在我们相遇时,派出所的人已上班,赶到他家,在房前屋后拉上了警戒线,等着冀太荣回家。
我先告诉他最新获知的消息,冀中星左手被炸烂,手腕以下被截肢。“截肢,那就截掉了?”他伸出左手打量比划着,咧嘴哭了起来,“你说他咋没炸住别人,把自己给炸了呢?”他哽哽咽咽,接着说,“手不残,他还能骑电三轮,生人看见他,都觉着跟正常人一样,现在一只手没了,可咋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