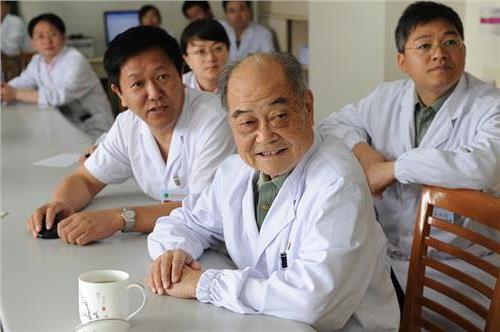潘向黎鸽子 夏天最后一朵白玫瑰——送李子云先生(潘向黎)
今天是李子云先生的七十九岁生日。今天,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这首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 李子云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而且是白玫瑰,美丽高贵,散发着洁净的芳香。她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身上兼具了“士”和“淑媛”的气质。在这种气质对照之下,现在的许多红人顿时会“小”下去或者显出骨子里的“俗”。
现在,世界红绿依旧,白玫瑰蓦然凋零。白玫瑰是不会像红山茶一样,开过了,还以一种锈一样的颜色挂在枝头。
这么快,这么干脆。这也是她的风格。刚才,一个同事来推荐我看一篇文章,我说:今天我不看什么文章,我要专心想念李老师。(我称呼她李老师,但是在我心里,她是应该被称作“先生”的那种女性。) 昨天下午,突然一条短信:李子云走了。
大惊!然后是茫然,梦里被冷水浇醒的那一种。 几个月前,我和南妮在瑞金宾馆的天鹅湖上的那家餐厅吃饭,看见她和一位女士一起进来。
她穿了雅致的外套,还是漂亮的发型,清澈的眼神,我们很高兴,但是没有凑成一桌——我们知道,这不是李老师的风格。
我们说下次要再请她吃饭,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去年,我请她吃饭,陈惠芬、南妮、王雪瑛来陪,那顿饭吃得很开心,李老师还夸我们漂亮。
其实最漂亮的是她自己,永远那么优雅出尘,那么气定神闲,有时充满机趣,有时还有点“童言无忌”。 论辈份,李老师当然是长辈。
但是,就像邵燕祥先生在他的作品研讨会上的开场白所要求的那样,我们从来没有把她当成一个需要保护、小心对待的老年人,我们都是把她当成完全平等、无话不说的朋友在交往。
我们对她,是欣赏,是喜欢,有钦佩,但没有“高山仰止”。 她重视仪表,所以每次和她见面,都要特别打扮一下,一见面我们就要互相夸奖一下——我们是真的想让她高兴,而她是真的能欣赏同性的女人。
我们在一起是没有规矩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家也有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她反应特别快,点评特别犀利,经常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然后她还忽闪着眼睛说:“唉呀,我这样说是不是不合适?” 我们会互相推荐新的作品,评点新出现的作家,观点偶尔不一致时就当面反驳她,她会说:“不会吧?那我要重新看看这本书!
”我还不依不饶:“你肯定是嫌人家长得难看!”她被说中“弱点”,大笑起来,笑完了说:“难看不要紧,他太邋遢!
”有一次出国回来,谈到出国感受,她最大的抱怨是针对同行的人:“这么好的宾馆,这些男人怎么就不肯每天洗头?油乎乎的,我看了就难受!”这种抱怨,非常有趣,非常李子云。 她爱热闹,非典期间,满城都是戴口罩的,她偏偏请我们几个吃饭,我们全都去了。
整个饭店,就我们一桌,她早早让服务员打开门窗通风,然后对着一桌佳肴长叹说:“再不出来吃吃喝喝,都要憋出病来了!
”我们都说:“能让我们冒死前来,只有你有这个魅力!”真的,很少见到像她这样,到七十多岁都那么有光彩有活力的女人。许多时候,她显得比我们还年轻,倒是我们被凡俗生涯磨得眼神苍老、反应迟钝、缺乏激情。
她对我是有恩的。几年前,她写了一篇关于我的小说的评论,节选发表在《新民晚报》,后来全文又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
我没有想过要请她写,不敢指望自己的作品能入她的法眼。她说不知道把握得准不准,我说:“只要你看了我的小说,说什么我都高兴,说什么都是抬举。”她笑了。那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许多人惊讶于她怎么对我这么好,后来她说了原委,是为我打抱不平的意思。后来她在许多场合不止一次地说:“国内年轻作家,我看到迟子建和潘向黎为止。”报纸采访,她也这样说。这当然更是抬举我。这样仗义,这样无私,这样不遗余力地提携一个晚辈写作者,是一位真正的评论家的风范。
最难忘的,是她私底下对我说的一句话:“你呀,生错了年代!”我觉得,这是很重的批评,也是很高的评价。 她的一生,充满了美感,也带着些许悲剧感。
我幻想过:等有机会,要问她一些关于她自己的秘密。但是好像始终没有机会。也许有些伤痛过往,本来就不该触摸。
手机响了,是“李子云治丧小组”发来的讣告。这么说,她是真的走了,我再也不能在此生的任何一张餐桌上见到她,再也不能让她清澈的眼神和灿烂的笑容照亮了。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白玫瑰。 那样一种清气和幽香!
尘埃和废气之中,令人永远怀想。 写于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