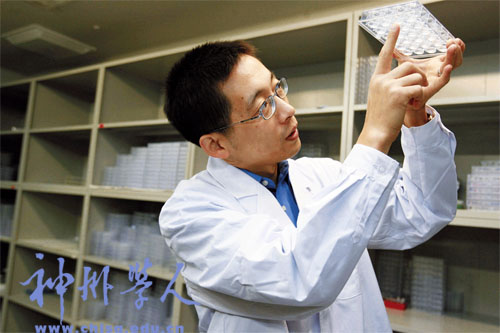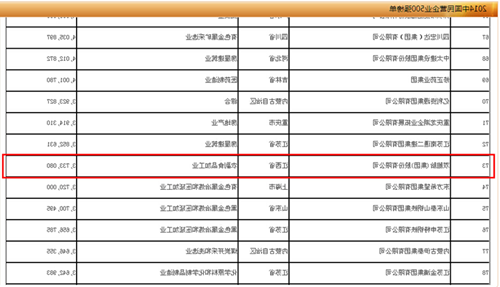颜宁施一公 施一公:回国是最好的选择
施一公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 摄影/高海涛
文/顾淑霞
2004年,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获得200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合作奖,他在答谢辞中说:“我确实为帮助中国数学发展付出了很大努力。另一方面,我很遗憾自己还没能回中国定居。无论我为中国数学作了多大的贡献,也无法与那些在中国土生土长,或是已经回国永久定居的人相比。”
施一公不想留给自己这样的遗憾。2008年2月,40岁的他全职回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他说:“从条件上讲,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的话,我确实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做科研。
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教育一批人。育人在育心,做科研是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
我想,如果引导正确的话,清华大学一定会有这样的一批学生,他们在为自己奋斗的同时,心里还装着一些自己之外的东西,以天下事为己任,驱使他们往前走,一定会有一批人这样做。如果这样,20或30年后,当我从清华退休时,我会很满意的。”
2006年5月,是施一公命运的拐点,这位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最年轻的正教授,毅然放弃在普林斯顿大学正值巅峰期蒸蒸日上的事业,决心回归母校清华,开始了回国的过渡期。
2007年3月,施一公在清华大学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开始了第一个实验。
2008年4月,施一公入选美国著名的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研究员,但为了全职在清华工作,他毅然辞去HHMI的聘任。
2008年底,施一公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的终身职位,他说:“在美国,我的学习、工作顺利,生活富足,但我内心始终缺少归属感和认同感。我接受和崇尚的是传统教育,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希望回到祖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为改善和改进国家的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做些努力,能培养一批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一些贡献。”
“最出色的学生”
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父母结婚后响应祖国号召,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我是在‘文革’时郑州开始武斗那天出生的,母亲生我时连医院都找不到,在惊恐中将我生下。父母想给我取一个有革命意义的名字,想来想去,就取了‘一心为公’的前后两个字。”
受家庭熏陶,从小聪颖过人的施一公对数学和物理具有浓厚兴趣。
1985年高中毕业时,学习成绩优异的施一公同时收到了清华、北大等几所重点大学的保送邀请。在那个年代,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生命科学是什么,施一公甚至一无所知。
“我也很想学物理,因为觉得学物理是最聪明的人的选择。”但在与北京大学签订了意向书后,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又找到他。“这位老师说生命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尽管当时我对生命科学一无所知,但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我都觉得到清华是最好的选择。”
1989年,施一公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同时以优异成绩修完了数学系双学士学位要求的所有课程。在教授们的记忆里,施一公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全面发展,是清华大学田径队的主力队员,曾经创造了学校万米竞走的纪录。
“1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都要打一次铃,提醒你必须要坚持。这不仅仅是一个体育项目,这是意志品质的锻炼,这种锻炼让我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都受益无穷。”施一公说。
施一公(左)主持由《科学》杂志主编(右)主讲的清华大学演讲会。摄影/郭海军
1990年,施一公赴美深造,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及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在国内一直保持“第一”的施一公,刚到美国后发现英语不行,于是给自己规定每天背25个新单词,很快过了语言关,他在学科上的能力也得以充分的展示。
有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为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没想到施一公却当场指出了导师在某个演算中的漏误。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毕业时,导师破例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竞相争夺的领军人物
1995年,施一公获博士学位,次年到纽约史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结构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1997年4月,他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
1998年2月,施一公正式就任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一进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就给他提供了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万美元的启动基金。在当时,这种待遇是很多人无法企及的。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机制为施一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
施一公选择癌症研究为主攻方向,他研究的课题是:细胞凋亡和癌症发生的分子机理,而细胞凋亡通路的破坏与癌变有密切关系。施一公说:“我们这个分子生物学系癌症结构生物学研究组,以研究细胞凋亡和癌症发生的分子机理为主攻方向。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根源上了解它们,提示其分子机制。而这正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我们以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为主要研究手段,获取关键蛋白质的原子水平的结构。我们看到癌症抑制因子和致癌因子的一些空间结构,看它们怎样相互作用,把‘不正常’变为‘正常’的工作手段,而这就是导致治疗和防治癌症发生的一个突破性的手段。”
致癌原因一直是全球科学家致力研究的目标之一,2003年7月,由于对解开这一人类生命科学之谜的突出贡献,施一公获得国际蛋白学会(The Protein Society)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研究家奖”(Irving Sigal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是这项奖项设立19年以来首位获奖的华裔生命科学研究学者。当时施一公刚刚36岁。很多曾获该奖项的人如今已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施一公卓越的学术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认可。2001年,仅用3年的时间,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而一般申请终身教职需要6年;2003年,他又被聘为正教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他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短短9年,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
年轻且学术造诣深厚的施一公,成为许多顶尖级大学争相竞聘的对象。2000年以来,哈佛、MIT、 约翰·霍普金斯、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国顶尖级大学都向施一公抛出了“橄榄枝”。随着他进入学术发展的上升期,普林斯顿给他提供了越来越优厚的条件:他的实验室面积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整整一层楼。
他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除学校给予他稳定的资金支持外,他申请了11次美国国家基金,10次中标;有一个基金会资助他的科研;他还和许多美国的大公司合作,支持他的科研;他回国前仅目前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5个独立的科研基金点就可以一直支持实验室到2012年;而且如果他愿意在普林斯顿大学哪怕保留半职,他就可以获得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5年共计1000万美元的经费支持……
事业的成功也伴随着他优越而幸福的家庭生活。在普林斯顿,学校资助他购买了500平米的独栋别墅、1英亩的花园。一对龙凤胎儿女享受着美国快乐的幼儿园教育……
施一公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指导学生。 摄影/高海涛
归国回校:“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4年一次的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期间,校领导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尤其是医学院和生物系,问他是否可以全职回清华工作。
当天晚上,施一公给妻子打电话,妻子说:“这个机会挺好的,你不是一直想回国吗?你应该好好把握。”他非常高兴:“没想到妻子会这么支持我。”
妻子支持他回国工作,但没想到他还要把家全部搬回去!当时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还有20名科研人员。2006年6月,施一公开始了回国的过渡期,他开始慢慢关掉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并着手在清华大学建立结构生物学中心。2007年3月,他在清华的实验室开始了第一个实验。一年后,他全职回到母校清华。
“对于我回国的决定,许多人困惑,但真正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决定。我的童年生长在河南中部农村,周围都是贫穷但朴实的农民,他们对‘文革’中下放的我们全家格外照顾;他们任劳任怨,辛勤劳动。我懂事以后就想回报这些父老乡亲。若要民富,则需国强。对他们最大的回报就是尽自己的力量使国家更加富强。”施一公说。
曾是施一公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和博士后、如今已是清华大学教授的颜宁清楚地记得,在普林斯顿第一次见到施一公时,施一公就对她说:“你出国之后就会更爱国。”在施一公看来,“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
率直、生性乐观的施一公坚定地面对着回国过渡的每一个困难。在2007年的过渡期,每次回国,他的咽炎至少要一个月左右才康复。在普林斯顿,他可以直接在普通实验台面上做实验,因为空气质量好,作实验时很少会出现被污染的情况。
而回到清华,他必须建立专门的细胞间。否则,培养的细菌经常被空气中的噬菌体杀死。因此,他们规定所有实验室的窗户必须关闭,无论天气多好都不能打开,否则做实验会污染。但这些毫不影响他回到祖国的兴奋与激情。
就像他每周都爬一次香山,每次都从北门最陡的地方爬上去。“第一次爬的时候花了近两个小时,累得不行。现在,直上直下2300多个台阶,半个小时就爬上去。有时累的时候就想,回国不一定有多累、多艰苦,这点累是一种享受。就像大学时练体育,我的意志很坚定,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他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些事情对我思想的影响太大了。你问我回清华最想做什么?我最想做的就是育人,科研只是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我甚至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和专业教育一样重要。
他相信,中国会有一批这样为理想奋斗的人。如今,41岁的施一公培养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已有许多成为知名的教授。
“再过二三十年后,当我在清华退休时,看到自己的那么多的学生成为理想远大、影响社会甚至影响世界的人,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施一公说。
在清华开始事业新征程
“在美国和中国做同样的事,在清华会开心得多。回到清华后,我每天早上都很激动,又是新的充实的一天,又可以做很多事情。当你很有理想、心情愉快的时候,觉得特别有劲。”施一公说。
每天早上不到8点,施一公就来到办公室,晚上12点以后离开,几乎每天工作都在16个小时以上。他的学生张旭说,只要施老师在办公室,大家可以随时进他的办公室。而只要他有空,也会随时来到实验室,指导学生实验,从国际前沿的课题思路,到实验如何设计,到一个溶剂的配制……
“虽然在清华开始实验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但课题的深度、广度、学生的思维训练已经相当不错,大家都干劲十足、热火朝天,现在实验室完全可以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鼎盛时期的实验室相媲美,这是我非常自豪的地方。”施一公说。
施一公的8名学生中,已有3名学生的课题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2008年12月14日,他的博士生张旭在读二年级时就已经有一篇成果在《自然》杂志的姊妹刊《自然结构与分子生物学》杂志刊出。
谈起导师施一公,张旭不住地感叹自己“幸运”。谈起自己的实验和文章,张旭说:“其实我自己一直不看好自己的实验,当施老师从他的角度阐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惊讶,没想到成果这么重要。我们发现的这个蛋白结构跟以前的任何一个蛋白结构都不一样,是一个很新的折叠方式,还推翻了以前一个著名实验的假设。”张旭说。“如果没有施老师,对我们初学者来说,不可能会得出这样重大的成果。”张旭说。
施一公对自己的学生也是称赞有加。“他们都很努力,每天夜里我12点离开时,还有许多同学在做实验,周末也经常不休息。”
张旭说:“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尤其是有一些成果出来后,大家比着向前做,要强劲都出来了。”
学术造诣高、率直、乐观、平易近人,像是老师,更像是朋友,这就是学生眼中的施一公。在学生眼里,施一公对学生“总是特别好”,他会随时来指导学生实验,有时组织学生去爬香山,每月和实验室同学至少聚一次餐,与学生讨论任何问题,关心学生要吃好穿暖……“与施老师谈话时,他总是给你希望,即便是他很苦恼时,也不会把这种情绪带给你,总是给你信心。”李晓淳说。
他还会给学生做各种讲座。一位大一学生听完他的讲座后激动地说:将来一定要成为像施一公教授这样胸怀祖国的科学家。一位大四学生在听完他的专业讲座后感慨地说:听了这堂课似乎把本科4年的生物学全部串下来了。施老师一针见血地把要领全部提出来,要点全部串下来,讲的是观念,而不是具体的知识,告诉你如何向前走。
施一公把实验室的目标索定在膜蛋白上,这不仅是国际结构生物学领域最前沿的课题,也是国内制药领域需要解决的重大创新。同时,施一公还担任了科技部重大专项的首席科学家。
他的事业在清华大学全方位地前进着。
施一公,1967年生于河南郑州。1985年,作为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和河南省赛区的第一名,被保送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1989年,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1990年赴美国留学。1995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物物理专业博士学位。
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2001年获该校终身教职,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3月,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
2008年4月,入选美国著名的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研究员(入选HHMI被认为是生命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为了全职在清华工作,他毅然辞去HHMI研究员的聘任。
研究方向主要运用结构生物学的手段研究癌症发生和细胞调亡的分子机制,迄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25篇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刊物《自然》,《科学》,和《细胞》。
在2003年获国际蛋白学会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为19年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2005~2008年,担任美国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