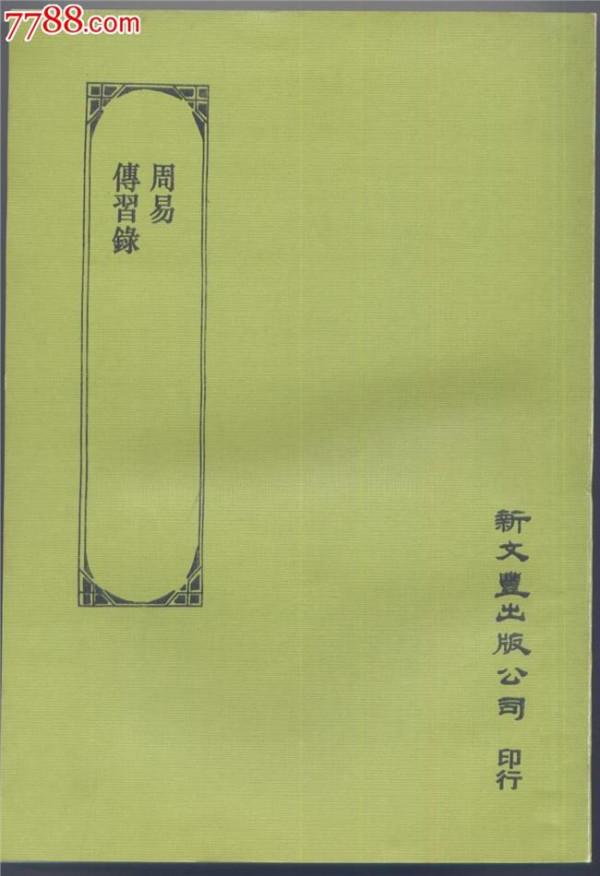贾平凹极花 贾平凹谈《极花》:像刀子一样刻在心里的故事
近日,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月14日,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召开。现场,贾平凹以一口浓重而韵味十足的“秦腔”与大家分享了创作这本书的初衷和过程。
创作是对现实的提问
从《秦腔》《带灯》《老生》,直至15万字的《极花》,从事文学写作40多年来,贾平凹在中短篇小说、散文、长篇小说等诸多方面都均有优秀作品面世,向世人展示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激情,被冠以劳模作家之称。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充斥着满满的乡土乡情。《极花》取材于一位老乡女儿的真实经历,以被拐卖女子胡蝶的口吻展开自述,着眼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以及城市不断壮大的同时,农村迅速凋敝,具有震撼人心的现实冲击力。
这个题材“雪藏”了整整十年,贾平凹从未跟人提及:“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了数百页的文字后却再也写不下去。直到前两年跑过农村的好多个地方,才获得了想要有的写作感觉。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
故事的女主人公胡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众多姑娘中的一个,不甘重复父辈生活,急于摆脱农村的一切,梦想着自己能摇身一变成为城里人。当胡蝶来到城市后,她喜欢上了扑面而来的城市气息,喜欢房东的大学生儿子。靠母亲捡垃圾维持生计,胡蝶自认为已经变成城市人,可是在她第一次主动出去找工作的时候,这个虚无缥缈的城市梦迅速破灭,她被稀里糊涂地拐卖到一个西北小山村。
当她被解救送至父母身边时,却深陷舆论压力。最终,她出乎意料地选择了逃离,重新“逃”回到了被拐卖的村庄。
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极花》是具有现实提问能力的小说,作家将贫瘠之地写出了人性丰饶和世事纷繁,既有对人的体恤、对乡村的探察,也有风俗志式的地方知识谱系的精妙书写。”贾平凹坦言,写《极花》时,他尝试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精神动向:“我不能漠然于现实,不能躲开它。
那块地方究竟坍塌流失了什么?村庄是常年驻雪的冰山还是一座活火山?以个体经历为线索,我着力探求群体性人格。”《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认为,每当贾平凹搜寻到一个令他激愤的点时,他就会进行深挖,让容易被漠视的乡村重回大众视野,这也体现了小说向现实提问的能力与担当。
文学的痛感来自土地
以社会新闻为创作契机构思小说,在贾平凹以往的写作中并不少见。小说《高兴》是对民工千里背尸返乡的故事演绎,《带灯》则网罗了灾害瞒报等社会新闻景观。《极花》的写作动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土地的痛感和对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新闻事件的震惊。
贾平凹认为,光写新闻本身,显然是不够的,文学可以从生活撕开的小口子里继续深究,呈现出小说艺术的高明与丰富。“《极花》虽然写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却并不是一个拐卖故事,它继续的仍是我多年来对于乡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
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它们正在消失。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
我曾经取笑说,农村人死了,烧那么多纸钱,城市人死了,尸体立即送去了火葬场。那么在另一个世界或有托生的话,那城市人是最穷的。在我的作品中,感情是复杂又微妙的。我不知怎么才能表达清,我企图用各种办法去表达,但许多事常常是能意会而说不出,说出又都不对了。”
如何从纷繁离奇的社会新闻中,剥离刺激、离奇的元素,蒸馏提炼出小说语言的厚实与灵动,是贾平凹一直在思考的。他说“我的文学观念很多是美术上过来的,可以从中西方美术史方面吸收借鉴”。贾平凹在创作《极花》时,尝试使用中国传统绘画的方式,借鉴了水墨画的手法,以达到中国传统美学物我合一的境界。
后记中,贾平凹告诉读者:“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时兴一种用笔很狠、很极端的叙述。这可能更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是不行。
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水墨画的本质是写意,通过艺术的笔触,展现作者长期的艺术训练和自我修养凝结而成的个人才气,从而克服将现成‘社会新闻’简单移植进艺术世界的急切和粗糙,注重接地气、引活水,深度夯入生活的地层,刻画生活湍流里普通人的浮沉。”
有评论认为,《极花》源于作家对现实的热望,源于精神在场,因为精神在场,故事和想象的世界便扎根于生活之中,而不是局外幻境。小说的结尾,被拐卖的女孩最终选择回到乡村。为何要安排这样的结局,贾平凹说:“我把胡蝶又写回乡村,实际上这是一个轮回,第二次再回去的时候,她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的未来怎么发展?谁也不知道。这是把结尾基本是当开头来写,这个故事写完了,下一个故事又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