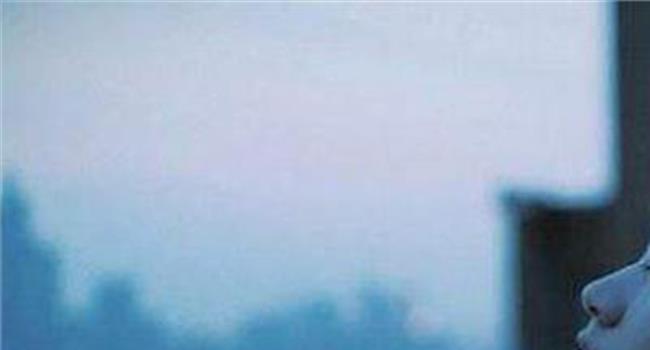萧功秦知乎 萧功秦:知识分子应回归“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
[摘要]人们相信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比一般人能讲出道理来,知识分子也很自信,因为他们觉得读了书就有知识,对自己往往有很高的估计。
作者: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知识分子常常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来进行思考与思想创造,而人的理性本身却有着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它有一种逻辑上“自圆其说”的能力,它会编织出一种观念的罗网,让人脱离现实,变成作茧自缚的“观念人”。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对集体经验的否定,使之不能承担起过滤外来经验与信条的功能,从而进一步导致各种超越本土经验的舶来的主义在中国长驱直入。
人们是经由主义而行动,并改变着周围的世界的。正因为如此,对21世纪知识分子来说,要避免成为“观念人”,最重要的就是回归经验主义。
油画《蔡元培与光复会》(作者:章仁缘、尹骅、童雁汝南、李根)
一、知识分子与观念的陷阱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与传统时代相比,20世纪的人们是以主义来行动的,20世纪是思想主义盛行的世纪,是由知识分子创造的各种主义支配人们的历史行动的世纪。知识分子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通过自己的思想,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话语的力量,正是这种舆论场上的话语力量,会进一步形成群体性的思潮与主义,认同这种思潮的人们,就会结合起来进行集体行动,并经由行动而形成人类生活中的历史选择。
正因为如此,20世纪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他们的话语、思想而影响、改变甚至改造了世界。
人们相信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比一般人能讲出道理来,知识分子也很自信,因为他们觉得读了书就有知识,对自己往往有很高的估计。然而,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期望不能太高,事实上,正如历史上所表明的,知识分子也会造成时代的灾难,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来进行思考与思想创造的,而人的理性本身却有着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它有一种逻辑上“自圆其说”的能力,它会编织出一种观念的罗网,让人脱离现实,变成作茧自缚的“观念人”。
一般说来,理性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人的理性是通过抽象思维,把复杂事物予以简化。抽象与简化对于概括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简化的结果往往忽略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多元性、多面性以及多义性。运用简化的理性思维来作出判断与历史选择,其结果往往是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例如,观念型知识分子对西式民主具有的普世性的认识,造成民国初年的“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的社会失范状态,建构理性简单地把西方历史上演变过来的体制搬用到落后的第三世界中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旧的传统体制被打破了,而新的西化的体制却由于缺乏西方社会的各种条件,而无法有效运行,这种脱序,会形成全面的整合危机。
辛亥革命后的议会失败固然有多种原因,但这种体制缺乏本土资源的支持而造成的弱政府化、党争、军阀混战与国家碎片化,也是中国20世纪灾难的起源。
国画《武昌起义》(作者:冯远、杜滋龄、房俊焘、鲍凤林)
又例如,中国“穷过渡”的平均主义,当人们要用全面的计划经济这个“完美”的制度,来取代历史上形成的有缺陷的市场经济时,往往只想到这种由理性建构的“计划”的好处,却忽视了它的另一面,它同样也可能产生计划体制下的官僚主义化,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以及“大跃进”这样的由计划制定者造成的人为的灾难。
最为典型的是,波尔布特以废除城市、货币、市场,以及大清洗的方式来制造“新人”的“红色高棉革命”,这些都是左的建构理性的产物。
其次,个人理性的缺陷还表现在,一个社会主体所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全面的,当人们根据这种片面的信息来决定历史性的行动选择时,就会导致历史选择与判断的失误。
再次,主体自身的信仰、激情、人性中的幽暗的心理,以及浪漫心态,这些情感性的非理性因素,如同海面下面的冰山,会不自觉地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支配着显露在海面上面的理性,主体的理性受感情与其他非理性因素的支配,也就会发生判断的扭曲与错误。
油画《开创共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作者:杨松林)
更具体地说,人们总是以为自己是根据理性原则来进行判断与推理的,但支配人的理性的,往往是混杂着潜意识中的非理性的东西。人们总是把自己内心所希望的东西视为当然的、可以实现的东西,然后用“理性”的、逻辑的语言,把内心浪漫主义的意愿,论证为“社会规律”或“普世性”的第一原理,论证为“客观”的实在法则。
这些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的东西,经过华丽的理性外壳的包装,被误认为是真理。换言之,建构理性有许多“程序漏洞”,容易被浪漫主义乘虚而入,人的建构理性可能被人的信仰、感情、浪漫心态这些非理性因素无形中支配,建构理性很容易变成浪漫主义情怀的俘虏。
脱离人类集体经验的建构理性,往往最容易与人心中的浪漫主义结缘,将浪漫主义者追求的美,视为客观实在的真。于是,浪漫主义就披上“理性”冠冕堂皇的外衣,登堂入室,大行其道。
当主体把浪漫主义的东西论证为真理来追求,把浪漫主义付诸社会实践,就会造成乌托邦的灾难。这种把浪漫主义的心灵投影,自圆其说地论证为“科学”,是建构理性陷阱,这种“建构理性”是被浪漫主义包装起来的“类理性”,它与自然科学的理性并不是一回事,它只是看上去仿佛与科学理性是一样的,但它其实是浪漫主义的衍生物。
用一套看起来符合逻辑的语言,把自己心目中的实际上是乌托邦的东西,当作行动的目标来追求。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无论左的还是右的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都是左右乌托邦主义的实践者。
社会上的左与右的激进主义者,他们所推崇的愿景,无论是“穷过渡”的“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乌托邦世界,还是在落后专制基础上直接建构起来的符合西式普世价值的民主,实际上,都是在浪漫的“类理性”基础上形成的观念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