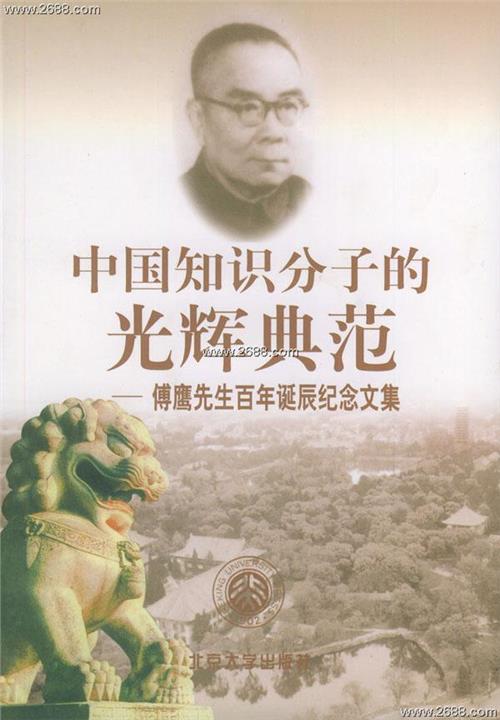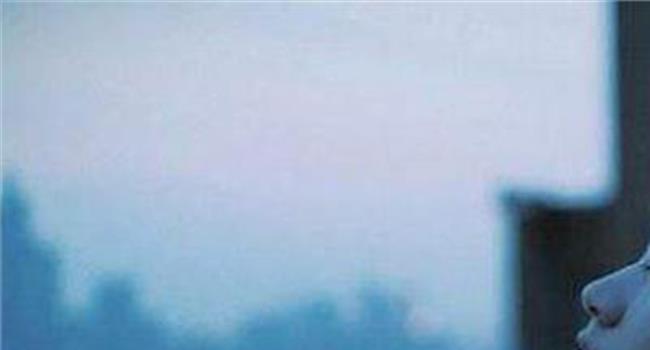萧功秦谈抗日 萧功秦谈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天涯网友:有人寄希望于出现苏联、东欧那样的情况,你希望哪种?或者有自己的思路吗?
萧功秦:我们可以把苏东模式称之为政治休克疗法,即激进派政治家通过一种民粹主义的广场效应,通过满足平民的抽象的民主诉求,通过取得多数选票而取得民意支持与权力。在这种民主化模式里,经济与社会发展可能完全不成熟,民主化却单兵深入。
这种模式最容易产生政治危机与连锁反应。在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在长期封闭专权的社会,民粹主义特别容易发酵。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从来没有参政机会的民众,又有那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与长期被压抑的未遂愿望,这些愿望一旦被改革唤醒,而一般人们总是会急切地期望立即实现它们。
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许诺快速满足这些愿望,谁的口号最简单,最煽情,谁就能稳操民众一人一票的政治资源。甚至可以达到垄断这种资源的地步。
俄国的"叶利钦现象"就这样产生,而那些现实主义的,务实的政治家却可能被指责为保守派而被边缘化。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叶利钦辞职时,对全国人民的忏悔,他说过,在多少个无眠的夜晚,他怀着摧心的忧虑,对过去的选择进行反省。
他说他曾经相信,俄国人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结果发现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我要求人们原谅我。再也没有比什么比叶利钦的自白更能说明问题的了。
多年以前,我就把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改革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他们把西方民主制度视为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制度,就像一件好的雨衣一样,穿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在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俄国学者米格拉尼扬写的《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
天涯网友:想听萧功秦先生对何新的评价。
萧功秦: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前期,我与何新在批判激进自由主义方面有一些共识,那时国内外舆论界往往把我与何新并为一谈,统称之为新保守主义。但我与何新有许多区别,我认为何新的"新国家主义"与我的新权威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新国家主义"缺乏民主导向,何新对民间社会,市民社会,独立人格对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似乎并没有予以重视。
何新思想中也缺乏对传统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批评态度,而且这种倾向似乎越来越重,他对计划经济体制往往予以不切实际的美化,似乎又回到政治浪漫主义上去了。
与"新国家主义"肯定计划体制与民主导向相反,新权威主义则主张在尊重现行政治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稳定,走向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可以说,新权威主义阶段,是从传统全能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的过渡阶段,这种导向性与"新国家主义"不同。
不管怎么,知识分子中不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还是对思想发展有益的,也是社会的进步所需要的。历史会在各种思潮与主义的碰撞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另外,我也不同意以何新为代表的那种民族主义,我对当下激进的民族主义抱有相当强烈的质疑态度,我认为它极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改革开放。
有人把我说成是左派谱系的学者,这可是极大的误解,从价值取向上看,何新可是左派,我则不是。我是最激烈批判新左派的人之一,作为文革时代灾难全过程的历史见证人,我对一切左的面目出现的东西,有一种人生经验给予我的免疫力,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与拒斥。
一个没有经历过极左时代的人,喊几句左的口号,喊出要回到毛时代去,正如我刚才在征求问题的网贴上读到的那篇讴歌毛时代的文章的作者那样,可能是天真,可能是对市场经济的弊端产生反感而激发的文化浪漫主义,犯这种错误是青年人的"特权",这些都可以谅解。
而一个经历过左祸苦难的中年以上的人这样做,只能被认为是投机。当然,我这里并不是指哪一个特定的人,而是指那些年纪不轻的"新左派"。
天涯网友:想知道这几年来萧老师对新权威主义的发展和扬弃。
萧功秦:近年来,我对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有过许多新的思考,这里不可能全面介绍自己的心得,我只说一点。那就是,新权威主义的生命力与存活力,取决于制度创新的能力。其实,新权威主义在防止腐败方面,也有其特殊的优势,世界上防腐败最有效的国家是新加坡,但它恰恰是权威主义的,我在那里待了五个月,写了一篇"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可供参考。
香港1975年前是世界是最腐败的地区之一,新总督来了后,向新加坡求教,并以总督的权威建立了仿效新加坡的廉政公署。
香港至今也不是民主政体,但它的廉政程度举世闻名。大家都以为,代议民主是防止腐败的最好办法,这可能是一个错觉,台湾现在是民主化了,但其腐败却远远过于民主化以前。去年在台湾花莲见到一位退出民进党的台湾朋友,他对我说,他亲见见证了一些两年前还向他借几千元新台币的钱的民进党穷政客,竟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突然暴富,买起了高级轿车与别墅,这使他十分伤心。
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民进党煽动族群意识,打民粹牌,反而使监督失效。
这些情况说明,反腐败的关键是形成有效监督与治理,使官员腐败的风险成本大于收益。理性的个人就会自觉地遵守规则。竞争性民主是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好制度,但它需要许多条件的配合,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同样会出现严重的腐败,例如民国初年的议员腐败,决不少于甚至高于专制清王朝。
从这一点而言,历史可以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就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而言,一个后发展国家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完成向新型现代化权威政治的转型。第二阶段,是完成新权威主义化以后的政体,如何避免进入退化了的权威政治。这就需要寻找防止苏丹化的机制。第三阶段,是向民主政治转型。所谓的政治发展,就是指后发展国家的三阶段的发展。这些问题都是我十分感兴趣的。希望今后有机会与各位交流。
天涯网友:"我个人认为,中国自邓小平改革以来建立起来的体制,尤其是九十年代南方讲话以后的政治体制,可以称为后全能型的技术专家治国的新权威政治。"不同意萧先生的这种看法。邓自己承认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邓以及当时的执政群体对将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没有长远的规划。
萧功秦:而我说的是对这个体制的政治结构的定位,你说的是邓小平模式的历史演变方式,我也认为,邓小平模式是一种经验试错的结果。另外,走小步的试错未必一定要有长远计划。先确定一个长远计划,未必就能有利于达到目标,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简单几句话讲清楚,以后有机会再进一步谈。
天涯网友:有个网友昨天问我,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请问萧先生:西方社会在"现代化初期"是从建立"军长型权威政治体制"开始的吗?若不是,为什么中国却要如此呢?是因为中国的超稳定的封建社会传统因素吗?
萧功秦:从历史上看,一些原发型现代化国家,如英国,现代化因素是在数百年的漫长时间里,在传统社会内部逐渐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并逐渐整合为一个整体,最终通过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建立起多元民主体制,这种原生型的西方现代化国家,它们确实不需要"军长型的权威政治体制",然而,相当一些比较后进的欧洲大陆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也需要一种类似于"军长型的权威政治",例如德国的威廉二世与俾斯曼。
以及其他欧洲大陆的开明专制主义国家。
至于后发展民族,在现代化初期阶段,确实更需要一个新权威主义发展阶段,这是因为,在非西方的传统社会内部,缺乏自主性的市民社会,缺乏中产阶级成熟力量、缺乏市场经济的力量,以及各种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推动力量,因而无法通过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整合,来形成新的现代化秩序,因此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新权威主义这支"看得见的手",充当整合枢纽。
所有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凡是没有通过新权威主义而直接建立西方多元民主体制的,除了印度(印度是英国多年的殖民地),几乎都无不失败,并让位于军事强人型的权威主义政权,如韩国就是例子。其原因可以从政治学上做出解释。
天涯网友:我认为你忽视了国家规模对防止腐败方面巨大影响的问题。我认为是:小国有杰出领导的话,容易防止腐败。大国制度更重要。
萧功秦:你的话有道理。超大型的国家规模始终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关键问题。对于中国的这一国情,应该是我们考虑中国问题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