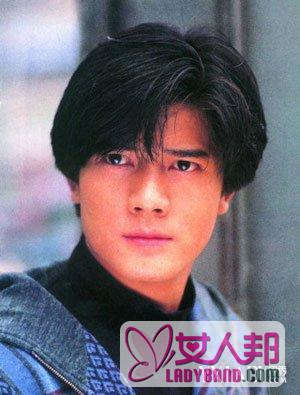萧功秦和秦晖 林治波:扒扒萧功秦对日的认识和立场问题
最近看到了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的高论:日本不存在军国主义,日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为了证明日本现实不存在、将来也不可能复活军国主义,萧功秦把所有能想到、能找到的所谓论据都搜罗出来了,比如全球化、老龄化、高科技、中产阶级,还有青年男女的尽情享受等等。
他说在国际学术界,军国主义有其严格定义。军国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体制:它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方面制度均从属于军事核心组织,从而满足扩军备战及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
如果按这样的标准来看,现在的日本并不是军国主义国家。这里萧教授先设置一个定义,声称这是国际学术界的严格定义,请问这是哪个国际学术界定义的?若照此定义来衡量,即便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的日本也不是军国主义国家,因为那时的日本政府也是多党制文官政府,并非什么都处于军事控制之下。
需要说明的是,当今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新趋势,并不意味着日本会完全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军国主义模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回到过去,因此其复活军国主义的趋势必定带有新的时代特征。
萧功秦设定一个先验的、绝对的、抽象的标准,以此衡量现实的日本,然后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日本不存在这种军国主义。这种似乎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其实是偷换概念,带有很大的迷惑性。
萧功秦的另一个论据是军国主义在日本的社会基础已瓦解。理由是:军部这个军国主义的毒瘤被彻底清除了;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橄榄型社会中的主体,全球化与高科技也使日本不需要像在二次大战以前那样把向外扩张领土作为目标;日本是个高度法治化社会,和平宪法的基础牢固。
这几条理由,均似是而非。随着日本战败,其军部确实土崩瓦解了,但比军部更重要的天皇制却被保留下来,比军部更悠久的武士道也被延续下来。
战后日本固然兴起了和平主义思潮,但军国主义余毒同样严重存在。由于天皇在日本的特殊地位和日本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天皇制的保留对于在日本彻底追查战争责任、反省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随着冷战的逐步升级,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完全改变了一度推行的非军事化及民主化改革、防止军国主义势力东山再起的方针,转而把日本作为反共的"防波堤"和"远东的兵工厂"来经营。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的1950年,日本吉田内阁就要求各教育机关在开学、毕业等仪式时必须扬日之丸国旗、合唱君之代国歌,并指令恢复战争时期的修身课。对战争的清算停止了,被侵略国家的对日索赔因为美国的阻挠而大打折扣或不了了之,对战犯的惩处工作也被搁置起来。
到1951年底,在整肃的21万人当中,居然有20万人被解除整肃,实际遭到惩处的人廖廖无几。很多战犯甚至被重新启用,其中吉田茂、岸信介还当了首相,岸信介就是安倍的外公。
这批人与战后的新右翼势力合流,形成了否认侵略历史、包藏军国主义余毒的恶势力。暗中大量贮存核材料并秘密研究核武器的工作,在日本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至于中产阶级和高科技的出现,就一定会使日本变成和平国家吗?事实上,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德日意法西斯,均存在着中产阶级和比较发达的科技,这不但没有影响他们发动侵略,反而成了助长其侵略野心的因素。法治化也并非和平的保障,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日益加速的军备扩张,不就是在这种所谓的法治化的背景下畅行无阻的吗?萧教授强调日本不需要像在二次大战以前那样把向外扩张领土作为目标,这实际上是非不愿而不能,日本已没有侵占中国领土的实力,但其他形式的侵略和破坏同样需要中国高度警惕。
萧功秦断言日本和平宪法的基础牢靠,几乎是罔顾事实。新安保法案的强行通过,已使得和平宪法名存实亡,日本已在事实上挣脱了和平宪法的束缚。请问萧教授,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宪法的牢固基础从何而来?
萧功秦说,其实日本极右翼早已经在日本政治中被边缘化……但2012年,民族主义行动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出现,有人甚至提出"宁愿日本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
2014年日本东京都选举,极右翼猛增到60万票,远超选前预计的30万票。……日本右翼借此挟持民意,促使多年无法通过的"集体自卫权法案"被顺利通过。
日本广大民众是爱好和平的,但日本极少数的右翼激进派居然能如此撬动中日关系,真可谓"蝴蝶效应"。萧教授的这些说法,均与事实不符。安倍作为极右翼政客两次当选首相且获连任,边缘化从何谈起?如果安倍这种人还算不上极右翼,那么日本的极右翼势力不是更极端、更令人恐怖了吗?整个右翼势力不是更庞大、更广泛了吗?萧功秦把新安保法案的通过和日本右翼势力的扩大,归咎于中日恶性互动,声称中日恶性互动反使日本右翼渔利,这是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貌似客观地各打五十大板,这不但是倒果为因,也抹煞了基本的是非界限。
难道说,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军备扩张,没有其内因,而仅仅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行动"?我们的民族主义行动有那么大威力吗?按照萧功秦的逻辑,面对日本政客否定历史的言行、霸占中国钓鱼岛、挑衅性的反华政策,以及军备扩张的危险趋势,中国人民不能抗议,抗议了就动辄得咎,就属于恶性互动,就会让日本产生蝴蝶效应,这不是血口喷人吗?
萧功秦强调,日本人是世界上对战争痛苦体验最为强烈的民族之一。根据近年来盖洛普对各国民众参战意愿的民意调查,当今只有11%的日本人表示在国家受到威胁时愿意上前线打仗。
连日本人都自我解嘲说,日本已经患上"和平痴呆症"了。萧教授此言差矣。日本是一个好战嗜杀、刀尖舔血的国家,姑不论古代日本对中国的不断骚扰,仅以1874年到1945年的70年而论,日本每隔三、五年就发动一场大规模对外战争,至于规模小一些的侵略扩张行动则几乎从未停歇。
井上清在《日本近代史》里说:"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
"可以这样讲,无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还是在现实的世界各国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凶恶残暴且持续不断地侵略践踏另一个国家,宽厚善良的中国不幸挨上了这么一个邻国。如果有哪个国家对战争的痛苦体验最深,那毫无疑问是作为被侵略国家的中国,而不是侵略他国、制造血腥战争灾难的日本。萧教授太体谅日本,反而抹杀了中国作为受害者的最基本的事实。
客观地说,这种凶恶残暴的侵略战争不是几个日本军阀单干的,而是日本民众在日本军阀的指挥下同心合力进行的。把日本民众与日本军阀分开是出于中国人的善良愿望,却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日本的统治者是从日本民众中产生的,他们是日本民众的代表。哪个国家都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日本也不例外;但在战时,日本的男女老少大都在不同程度地为侵略战争出力,这是事实。
战后一度兴起的和平主义思潮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重大变化,也是事实。日本《读卖新闻》2006年曾经进行过民意调查,当时80%的日本人反对发展核武器。不过就在2015年5月,同样的民意调查显示,已经有90%的日本人支持政府发展核武器。
安倍的新安保法案虽然遭遇了部分民众的反对,但还是被通过了,这说明:一方面日本虽号称民主国家,而日本统治集团并不尊重民意;另一方面,日本新安保法案之所以能够通过,是因为日本统治集团内部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而这种共识的背后也具有雄厚的民意基础,甚至可以这样讲,新安保法案代表了日本的主流民意,即使在街头游行的民众,所反对的未必是新安保法本身。
因为,反对新安保法,与反对通过新安保法、反对本会期通过新安保法,以及因新安保法讨论不够充分而反对,并不是一回事。
所谓"和平痴呆症"的说法,根本不能反映日本民意的主流,而只是反映了一些放弃了和平主义的人对仍然残存的和平主义的不满而已。
笔者注意到,萧功秦文中还有"野田内阁为了避免刺激中国而将钓鱼岛"国有化"的说法,这个说法已经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
我们当然不能说现在的日本就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但二十多年来,日本一直在右倾化和军备扩张的道路上暴走,一直处于逐渐复活军国主义的趋势中。
他们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现在敢讲了,比如拥有核武器;过去连讲都不敢讲的,现在都做了,比如废除限制武器出口的三原则、挣脱和平宪法的束缚和一再增加军费预算。酒醉后的安倍更是流露出惊人秘密:正在谋划对华战争计划,"要行使集体自卫权并和美军一道,敲打在南海上的中国",并扬言新安保法案冲着南海上的中国的。
就在本文收笔之际,又传来了路透社的最新消息:日本正致力于在东海200多个岛屿上部署反舰和防空导弹设施,连成一条长达1400公里的"战线",以对抗中国在西太平洋不断上升的地位。请问,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会这样吗?
封建的天皇制,浓厚的武士道与军国主义传统,漫长而血腥的侵略前科,对侵略战争的拒不反省,钓鱼岛争端,对中国崛起的强烈危机感和羡慕嫉妒恨,以及由此导致的反华政策的加剧和美日勾结的加紧,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日本日益严重和不断加速的右倾化,以及与之形影相随的军事化趋势。
这种趋势取决于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图与政策,而不取决于日本的青年男女是否"人山人海地在阳光下尽情享受着集市乐趣"。
不看清这一点,不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趋势,中国还会吃大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具有侵略前科而又拒不反省侵略战争,且暴走于军备扩张道路上的国家,犹如一条本性难移的毒蛇。
在农夫与蛇之间,我们不要再做迂腐的农夫,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不要再重复农夫与蛇的悲剧。我们以善良宽厚之心面对日本,已经吃尽了苦头,现在千万不要在磨刀霍霍的日本面前再患上"和平痴呆症"。
(作者是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兼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