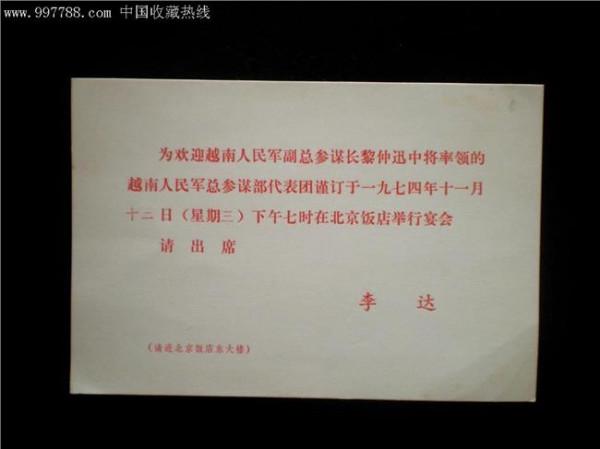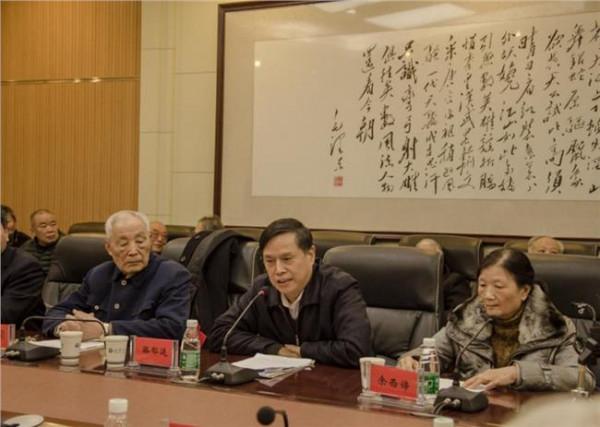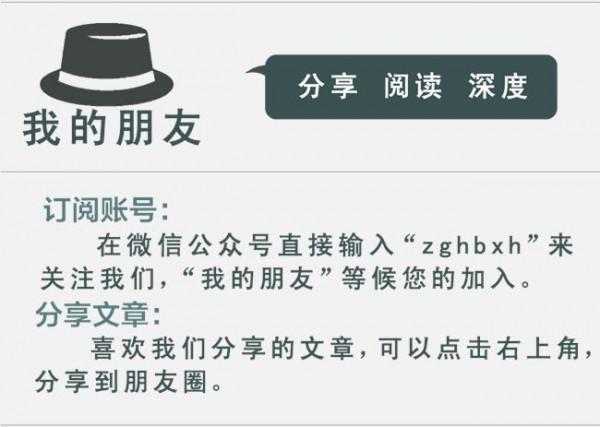王任重李达 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
王任重与李达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是1953年2月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因为新中国的高等学校是接受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所以尽管武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李达是国务院任命的部管高级干部,但却同时接受高等教育部和湖北省领导。
同时,李达也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由于这种双重关系,李达与王任重也有交往。再加上毛泽东来汉总要见见他,王任重作为东道主,虽然不是每一次都在场,但自然非常清楚李达与毛泽东的关系。
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王任重撰写《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派人将稿子送李达征求意见。李达读后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嘛!
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应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
王任重接受李达的意见,发表其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却认为李达的意见是思想不够解放,仍然使用着不同时空、不同意义的“超”。他说:“我开始考虑这篇文章的时候,本来想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样的题目,因为有几位同志不同意所以放弃了这个题目。
如果说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但是如果说要超过马克思,那么有人认为这似乎太狂妄了。
我想,如果不准说超过马克思,那么能不能说马克思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的一位神仙呢?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了真理的顶点,已经结束了真理呢?我看这样的说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
那么超过马克思的提法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呢?难道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超过产生马克思主义的19世纪吗?难道马克思不希望后来的人超过他吗?”
思想和事业自然是发展的,不同时空的人也可以延续和发展同一种思想和事业,但却不是同一时空人的“赶”和“超”。李达不同意或反对王任重的“超马克思”,当然不是指思想和事业的延续和发展,而是既强调时空的界线,又注重实际的意义。
1960年,当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他惨淡经营的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刊物《理论战线》不得不奉命停刊时,他终于道出了他当年反对王任重“超马克思”的实际意义:“超过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超……超……超得好!我们这个刊物还是小事,饭也没有吃的了!”
1958年,武汉大学同全国其它高等院校一样,进入了所谓教育革命时期。虽然在“教育革命”高潮中,毛泽东于9月12日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成绩,而李达却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对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然反对。
李达对于“教育革命”的这个态度,不能不令中共湖北省委派往担任中共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的刘仰峤和书记刘真甚至中共湖北省委不快。因此,即使在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眼里,李达也不免同二刘等人一样有“碍手碍脚”之嫌。
但是,李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行政级别定的很高,又与毛泽东具有很深的历史关系并与毛泽东保持不错的私交,因此无论在武大还是在湖北省委,都被视为“通天人物”,他们对李达除了敬而远之,似乎也没有其它的办法。
为贯彻“高教六十条”,1961年武大党委开展了整风,省委派宣传部副部长朱劭天来领导。经过非常激烈的整风斗争,继刘仰峤之后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的刘真被调回湖北省委,校党委两位副书记侯福珍、罗鸿运也被同时调离武大去郑州担任河南省国防工办副主任,改由朱劭天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
但是,李达因为反对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左”的倾向,在1961年整风中又发表了后来被指称为对1958年“教育革命”“反攻倒算”的激烈讲话,因而便得罪了刘真等许多“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即后来他们自诩的“左派”,埋下了以后“文革”置他于死地的祸根。
朱劭天是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后来去延安,曾任陈云的秘书。南下后留在湖北工作,来武大前为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本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朱劭天,熟悉教育工作,具有甚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开会讲话也十分中听。他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后,李达与他配合默契,工作显然顺手起来。
不意到了1963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的刘仰峤拟把在1961年整风调离武大的侯福珍、罗鸿运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
但李达认为他们不懂教,不宜回武大工作。刘仰峤很不高兴,便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意思是省委听你的,还是你李达听省委的?李达本来对刘仰峤1958年在武大领导“教育革命”就有看法,侯、罗二人那时分别担任物理系和化学系党总支书记,正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绩”而被他刘仰峤双双提拔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现在又要把他们调回复职,李达自然顶牛。
他毫不退让地说:“那好,他们回来,我就不做校长;要我做校长,他们就不能回来!”说完竟扬长而去!
刘仰峤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李达果真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有人劝他,他说:“生姜愈老愈辣,犯错误就犯错误,为了这件事,总开除不了我的党籍!
”杨秀峰是资深的共产党人,第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30年代,与李达同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他接到李达的辞职电报,十分惊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事,何况还是发生在他这位大名鼎鼎的老朋友身上!他马上把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叫来,将李达的辞职电报交给他说:“你赶快去一趟武汉大学,看李老遇到什么坎坎过不去。你只了解情况,回来报告。你在那里不要表态。”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来汉后,立即造访李府,转达杨部长的问候。他说:“杨部长让我来问您老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坎,以至于要辞职。”李达见杨部长接到他的电报就派专员前来关心,心情很激动。他在如实介绍了他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这场人事纠纷后说:“是省委刘仰峤同志跟我过不去。”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回京向杨部长汇报后,杨部长对着话机向王任重通报情况后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于是,王任重不能不过问了,两位副书记的调任只好收回成命。
翌年春节,王任重陪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还就此事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李达感动地说:“我对省委也不够尊重,也请您和省委原谅。”李达此事在当年那个时候不无唐突;但后来“文革”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却显然不实。
王任重此次去看李达,知道李达身体和心境都有问题,他也急了。他当即把常务副校长何定华找去谈话:“李老夏天去青岛,冬天去(广东)从化,你们要关心。没有钱,找省委,具体事你们办。”
但是,王任重却对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漏子”有意见。后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对朱劭天说:“任重同志对你有意见。”意思是难道省委、特别是王任重还不能做好李达的工作,能让他打电报向高教部辞职?其实,这也是冤枉了朱劭天。
因为李达给杨秀峰部长打辞职电报那天,朱劭天正巧感冒发烧未上班,完全不知道李达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事。1964年,朱劭天终于被调出武大,去广州任中南局科委副主任,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央组织部已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他本人也于10月14日给武大党委写信说明原委,并要其家属将书籍、衣物搬去北京。
但到12月中旬,中组部又派员向他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全国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他因急于向其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
可是,李达哪里想到,一场置他于死地的奇灾大祸就要降临到他头上了。他的赶回武大也就成了他“自投罗网”而抱恨终天之行。7个月后,8月24日,他就被迫害致死!
4月10日,广州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他点了李达的名,同时也点了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的名,并与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
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王任重派车把武大哲学系助教陆某接到其百花村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指示她将她当面汇报的材料再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
陆某原在政治系工作,1964年政治系撤销后才来哲学系。应当说,她并不怎么了解李达。但是,她居然搜集到了李达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材料!
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依据陆某提供的材料点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名。他还说:“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
28日,武大党委书记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王任重的报告,并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许道琦和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根据这个指示,对他们所确定的“知情人”,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日夜追逼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要求他们“拿出定性的东西来”,“一句话也要”。
在那种“知情不报就是对组织不忠,对毛主席不忠”的时代氛围下,一些人出于对组织的忠诚,或出于自我保护,都不得不揭发交待。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夹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李达在历史上脱党但始终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在那“怀疑一切”的时代氛围下,人们亦怀疑李达也一定有“大问题”。王任重在《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加按:“李达同志的历史可不光荣啊!一九四九年以前你在哪里?”在决定打倒李达的中南局会议上,庄果也预言:“按一般情况,李达一定是在大革命时叛党的。”
6月30日,李达被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当日《湖北日报》头版下半版,在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之下,发表“编者按”说:“今天本报发表两个材料,一个是《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一个是《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这两个材料,进一步揭露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黑帮的反动面目,这样,就便于同志们了解他们的反动言行,看透他们的反动本质,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们斗倒斗臭。”
李达向毛泽东求援
1965年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顿时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小孩知道了这一消息,不由产生了一线希望。17日,他试探地问刘某:“听小孩讲,毛主席来武汉了。”刘某因未得工作队指示,不便回答,只是冷冷地答说“不知道”。他迅即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耽心的正是怕李达去见毛泽东,便反过来让刘某去试探李达是不是有想见毛泽东的念头。
李达经受18日那天他家乡湖南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面斗后,心里愈加愤怒。他甚至气愤地说:“我是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他也更加痛苦,到19日很少说话。
得到了工作队指示的刘某这时以关心的口气反过来问李达:“毛主席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主席?”而李达却反而冷静了,他说:“毛主席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刘某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也就放心了。
但到这天下午,李达的血压已升到了236/114,尿糖仍是4 。在饭厅床上量血压时,刘某劝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他“顽固猖狂”地讲:“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
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压,他背着石曼华叫刘某入内,“怒气冲冲”地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他对刘某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
”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
随即,李达用毛笔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
李达这封信虽说是请毛泽东“救”他一命,但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的“将军”:“我写有坦白书,请你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
对于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李达要刘某马上送到。但是刘某因为还没有与工作队联系,不便答应,便推说:“今天已下午5点多了,明天一早送去。”
李达不依说:“今天就送去,你送去,要不找祝福庆、刘敬一(按:均为李达警卫,运动中已被调开)送去。”他还特别交代:“你帮个忙,送这封信到毛主席那里,你不要与工作队他们商量。
与他们一商量,信就送不到毛主席手里了,他们会留下。”他似乎在提醒刘某:“这还是一场宗派斗争,刘真、侯福珍回来领导运动,他们来整我们几个人,非要把我们整死才甘心。”刘某顶他说:“省委不早作结论,武大没宗派问题。”他仍然说:“是宗派斗争,整我们几个人……”
5点半,刘某即到招待所向工作队庄果等三人汇报李达写信情况,交了信。庄果接后即行拆阅,在取信纸时还说:“呵,这是给主席的信啦,没有看见,糟糕!我犯了个错误。”因为其时已有作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反党集团成员的杨尚昆所谓私拆和扣押毛泽东信件的“罪行”问题。
他们商量后,决定把信留下。庄果又告诉刘某如何向李达交代。他说:“你先到外面去玩玩,过一两个钟头再回去,对李达就说信已经送到毛主席那里了。”遵照庄果的指示,刘某晚上七点半回去见李达,讲信已经送到的情况。
李达问送信的经过,还讲主席是住在什么地方。但他又怀疑地问:“信是否真送到了?”刘某说:“怎么没送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还有绿色篱笆呢。”李达似乎还不放心地问:“有收条吗?”刘某未想到此着,愣了一下,便支吾说:“信交给了警卫,他说给主席的信是不给收条的,他保证送到就是了。”李达由衷而充满期待地说:“辛苦你了,交给警卫,信毛主席一定能见到。”
直到7月29日,工作队陆某才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陆某此举同样是出于所谓杨尚昆“私拆”和“扣押”毛泽东信件的“罪行”问题。
6月30日报纸、电台点名批判李达,翌日,7月1日,王任重就拟向已来汉的毛泽东呈报《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并写下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个地主分子,又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即清洗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可否?请批示。”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把写好了的这段“请批示”用红铅笔划去了。此后尽管他每天都能见毛泽东,却并没有向毛泽东呈报请示。毛泽东决定7月18日晨离汉回京。17日晚上,他在东湖召开省委常委会,一举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这个《决定》没有经过任何一级基层党组织的讨论,也不听李达本人的申辩,属于运动中的“热处理”,而不是通常运动后期的“落实处理”;并且属于“文化大革命”的罕例。
这个《决定》也开列了一些强加给李达的“三反”言行,明文肯定了李达“是个老叛徒”,但却既不给李达戴“三反分子”帽子,也不以“叛徒”罪名清洗出党,却只戴“地主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并“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管制劳动改造”。
这个《决定》连同《关于开除李达党籍的请示报告》上报中组部,由该部八处于7月27日呈送已调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批阅。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的8月1日批复:“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但是,李达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了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写这张条子的人当然就是收到武大所寄李达给毛泽东救命信的人,他注明“武汉大学”,是因为他知道除了“文”李达,还有“武”李达,即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达上将。
毛泽东看到的只是这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自然不知李达的其它话语。但对于李达的求救,他岂有不允之理,当即便用他那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
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但是,无论是毛泽东对李达“救命”信的批示和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以及王任重向毛泽东的保证,都没有传达,武大的师生也无从知道。但到8月中旬,省长张体学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却对武大校文革传达了毛泽东对李达问题的这样两点指示:毛主席说李达是没有什么用了,我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
8月16日,张体学一行来武大,临时召开师生员工3万人大会(包括附近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等院校)。性情豪放、快人快语的张省长对李达问题又讲了一番能烘托当时“革命”气氛的话:“李达,过去我们叫他李老,现在我们叫他老不死。他现在已经搞臭了,你们再用不着斗他了。你们一定要相信省委,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让他进博物馆,吃饭、睡觉、拉巴巴!你们也可以回家看妈妈。”
李达之死
自1965年7月中旬进入批斗高潮以来,李达胃溃疡复发,糖尿4 ,血压已升到236/114,常感“头顶发麻”,心力已感衰竭。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实况广播。
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也停止了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到8月上旬,他已感到极度虚弱。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
据当时武大卫生科医生说,李达虽年老多病,但按他的体质和病情,如果保持正常条件,稍加医疗照顾,三五年内是不容易死去的。但此时已既无正常条件,更无照顾医疗了!李达因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行政6级,在正常条件下,他不仅享受特殊医疗待遇,而且有防痨专家、武汉医学院李晖教授的亲自诊治,他的治疗和保健当然不成问题。
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极不正常的条件,他也就是脱毛凤凰不如鸡了,连自费治疗的请求也得不到准许,哪里还谈得上医疗照顾呢?
8月13日黎明,李达在卧室突然摔倒,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连血都喷到了墙上。监视人员不仅不去请医生,反而斥责李达夫妇在耍花招。当日上午9点左右,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也陡降为90/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
刘某去工作队请示,医生也去向工作队说明诊断情况,但却被一句“研究一下”的话推搪了。上午11点才由护士来打针止血,却并未给药。
19日晨,李达高烧39·4℃,又从床上摔下,监视人员仍漠然置之。到20日才来一位护士打针。她发现李达小便带血,大小便都拉在床上。她要去向医生反映情况,也被制止。
李达自知年事已高,现在又病处垂危,但他仍在顽强地坚持生存,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尤其寄希望于和他有几十年友谊的毛泽东!他对夫人说:“等病好了,我们就离开武汉大学,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告状!
”于是,他最后再一次向庄果请求允许送他去医院。他悲愤地说:“印度战俘有病,我们也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吧,你们也应当让我治病呀。”然而,他的请求仍未被准许。
自8月13日胃出血倒床后,心力衰竭,李达很少说话。他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17日,他终于嘱咐妻子:“我如死去,请转告托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一直到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某等2人将他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准夫人石曼华去护送和护理。李达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对夫人说:“他们不让你今天去,你好好带嫒嫒,明天来看我。
”于是,李达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意)住进普通病房(按行政级别,李达是当时整个武汉地区两位6级干部之一,当住高干病房)。第二天,秘书刘某来找石曼华,说他马上去医院,要她买些鸡蛋糕交他带去。
石曼华要求一起去,仍然遭到拒绝。她请求带一点牛奶去:“他是靠牛奶吊命的。”但刘某还是不愿意。结果,石曼华只好买了四块鸡蛋糕和四个梨子给他带去。医院每天早餐是稀饭馒头,中、晚餐则是干米饭,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刘某带去的鸡蛋糕和梨子,也原样未动。只三天,8月24日,李达便撒手人间,含冤死去。
李达死后,25日,遗体即被火化。当天晚上,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李达已死,宣读中央陶铸批复的那份《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1967年春,武汉大学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年夏,王任重也受到了部分群众组织的严重冲击,并从此身系冤狱近8年。
王任重在接受武大为李达翻案的群众组织盘问时说,对于打倒李达,他先后三次直接请示过毛泽东。第一次,杭州会议期间,他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不表态;第二次上海会议问,毛泽东仍不表态;第三次问,毛泽东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
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直到1966年6月30日李达才被“报纸、电台点名批判”,而此前一直被报纸、电台冠以“某资产阶级‘权威’”的原因。
1985年,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在武汉大学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的会上披露了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当面论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举座皆惊!人们也更加由衷地敬佩李达的睿智和胆识。
但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却于1989年3月撰文《满篇谎言》,认为梅白所披露的这场论争“全是一片谎言”。他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没有提倡过,湖北省委也没有提倡过。”但是,所幸梅白并不是孤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之22节也述说了这场颇有兴味的哲学论争。
然而,正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终于说到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一个是李达,一个是张体学。他所说的对不住李达的地方,不用再说了;而他所说对不住张体学的地方,大概是指1959年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批张体学的“右倾”吧。
张体学同样是革命家,王任重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他担任第二书记兼湖北省省长。他虽然文化和理论水平不很高,但却是一位性情豪爽、快人快语、体察民情、关心民瘼的好省长。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