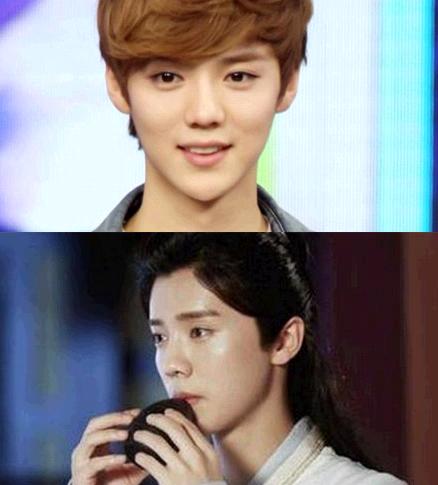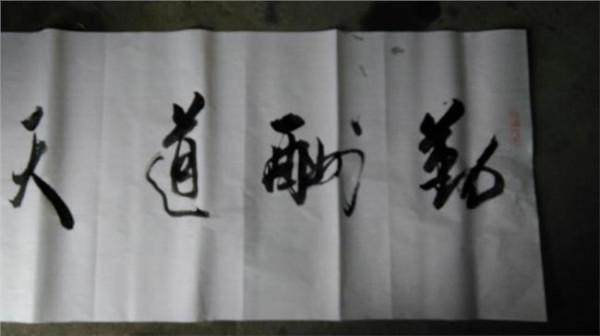瓜州李昌 李昌钰:我一辈子都在做傻瓜
“今天这个屋子里连我 8个人,我能用 20分钟大致了解你们7个人的情况。”这位 75岁的老人端坐在沙发上缓缓地说着。当然,这并不是他最厉害的本事,他可以凭着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让罪犯无所遁形”——他就是当今全球最著名的“科学神探”李昌钰博士。
近日,记者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见到李昌钰博士时,他刚从美国飞抵北京。想到他舟车劳顿,记者不忍心这么早就开始采访,李昌钰却很坚持:“早点开始,我们聊的时间可以长一些。”
近些年,在参与多起重大案件的侦破之余,李昌钰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世界各地授课、演讲,和媒体及公众交流,“每年都要跑 20多个国家”。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并不仅仅是司法界人士——理解并重视“让证据说话,不预设立场”的办案原则。正是这一原则,为他赢得了“当代福尔摩斯”的称号。我们的谈话,也从这里开始。
警察要有察言观色的能力
记者:您曾说:作为一名办案人员,要“保持全然客观,观察事物的原貌,顺其自然”。可做到“全然客观”很不容易,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李昌钰:我把自己看成一名科学家,科学家就是要保持客观立场,试验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掺杂人为修改。有些证据很明显,黑的或白的,但大部分是灰的。假如检验物证的人受到环境或他人的影响,就会把灰的说成白的或黑的,那就是不公正的。
但客观真的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当所有证人都指认同一个人时。所以,我们首先要训练自己,忘记自我。经常有警察给我送案卷时说:“李博士,就是这个人,证人都看到了。”我说:“你不要讲,我要看物证,等我看完再讨论。”
记者:警察和科学家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但在您身上结合到一起了,您自己怎么看这两个身份?
李昌钰:这是个很好、很有趣的问题。警察要有察言观色的能力。不仅看人,也要看现场,比如桌子上有几个杯子,几个用过,杯子上有没有口红……这里面有很复杂的人性的内容。而做科学家,就要完全客观,不能推测。
记者:最近国内有一些错案被公之于众,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错案与重口供、轻物证的观念有关。作为一名鉴识专家,您认为,重物证能减少错案的发生吗?
李昌钰:再有经验的警察,也会有主观性,但物证会比较可靠、客观,所以一定要让物证讲话。
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案子——“苏建和案”,这个案子对台湾司法界影响非常大。 19年前,一对夫妇死在家中,被刺了几十刀,非常残忍。警察被要求限期破案,压力很大。他们发现3个半夜打台球的16岁年轻人很可疑,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后来,这3个人遭到刑讯,实在没办法了,就承认是他们干的。没想到,另一批刑警也抓到一个人,叫王效先。他承认那对夫妻是他杀的,他还抢了4000元钱。面对这种情况,警察为保住脸面,就想了个办法,说这3个年轻人是王效先的同党。
后来,4个人都被判了死刑。王效先被枪毙前留下遗言,说是他一个人干的,但这段自白一直没公布。这个案子前后经历了很多次审判,所幸四任“司法部长”都没有签那3个人的死刑复核。
有一次我到台湾讲学,律师把案卷拿给我看,我发现了很多疑点,比如凶器、血迹。最后我们做了一个现场重建,认为是一个人做的。去年,台湾“最高法院”终审,将那3个人无罪释放。美国也有很多冤案,尤其是在使用DNA技术之前。最近 270多人翻案,就是DNA发现了新的证据;还有指纹鉴定,通过这个,又有一些案子翻案。
记者:所以说,鉴识科学与司法公正有必然联系?
李昌钰:司法怎么公正、怎么让人信任,其中当然有一部分人为因素,法官、检察官的操守,这个我们没办法谈,那是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但是物证,我们要保持绝对公正,物证的保存、鉴识、提取都要明朗化、公正化。中国的新刑事诉讼法公布以后,对警察的侦查程序、法律要求提高了,这是个进步。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互联网的影响无处不在。国内时常发生这种情况,案子还没判,就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这会影响到判案的公正性吗?
李昌钰:在美国,这个情况更严重,影响判案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是陪审团制,理论上,被选作陪审员的人,不能看新闻,不能和别人讨论案情。但现在有了网络,他回到家上网、发邮件,你怎么控制?再就是法官,因为怕在网络上被群起而攻之,会有顾虑,影响判案。这里面要考虑一个问题:那些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到底是真正的网民,还是被雇佣的“打手”。网络上的意见,是民意还是被制造出来的,很难讲。
记者:您怎么看待悬案?您参与侦破的案件,也有悬而未决的。
李昌钰:有人说我有案必破,没有这回事。美国的破案率也不是很高,有30%以上的凶杀案没破,50%的性犯罪案没破,大约 60%的财产犯罪案没破。
一辈子都在做傻瓜
尽管见惯各种血腥的谋杀现场,深悉人性中阴暗凶残的一面,熟知司法体系内的种种不公,但这位“科学神探”一直保持着幽默、谦和的人生态度。他开玩笑说:“我很会和人打交道的,当警察的时候,连犯人都喜欢我。”
李昌钰1938年出生于江苏如皋,他七八岁的时候,全家由上海迁居台湾。上世纪40年代末,父亲李浩民不幸在海上遇难,家境逐渐败落。“事实上,我不是一开始就想当警察。是因为家里穷,上警官学校可以免费。”1960年,李昌钰在台北警察局当了一名巡警。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李昌钰对鉴识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破案全靠刑讯。看到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我想,为什么不能用科学证据来破案呢?”
1964年,李昌钰到美国学习。“当时,没有鉴识科学这个专业,后来我索性在纽约大学学分子化学。”他用两年半时间修完了4年的大学课程:法律、刑事、生物化学。随后,又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半工半读10年间,李昌钰做过餐馆侍者、证券行小职员,教过中国功夫,也当过化验室技术员。
1974年博士毕业后,李昌钰决定去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这所学校正要建立鉴识科学中心,需要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来主持工作。“我的导师是一名得了诺贝尔奖的生物化学家,他希望我留在生物化学领域,可我要去做鉴识科学,他气得差点不和我讲话。”
那时,美国警界是白人的天下,他们都看不起这个中国人。“最先和我联络的是律师,我帮他们打赢不少官司后,州检察官专门召集警方开会,说以后所有案子都要找‘那个中国人’看一看。”
后来,李昌钰应州长之邀,担任警局刑事鉴识实验室主任。回到家,他告诉太太:“好消息,从明天起,你可以叫我主任了。”太太问:“年薪多少啊?”“1.9万块。”太太听了,开玩笑说:“人家的薪水都是越拿越多,你怎么越拿越少?”原来,当时李昌钰在纽黑文大学做教授,年薪已是4.
3万美元。“我一辈子都在做傻瓜。”李昌钰笑着说,“在台湾做警察,前途很好,却辞职到了美国;跟了得诺奖的生物化学家,却去做鉴识科学;教授做得好好的,却去拿不到原来一半的工资……当然,现在很多人又说我是最聪明的。”
作为最早利用 DNA技术破案的鉴识科学家之一,李昌钰利用证据鉴识屡破奇案。其中,震惊全美的“碎木机谋杀案”非常具有代表性。1986年,泛美航空的空姐海伦失踪了,只在卧室卫生间留下血迹。海伦的丈夫理查德是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 3次通过了测谎仪检验。
随后,有人提供线索,在海伦失踪那晚看见有人在他家附近拖着一台碎木机赶路,那人正是理查德。李昌钰把调查的重心转移到理查德可能停放碎木机的地方,展开地毯式的搜寻。结果,他们找到56片人骨, 2660根头发,85克肉块, 1颗牙齿。最终,经过李昌钰和同事们所做的5000多项检验后证实:这些人体残骸都属于海伦。检察官认为证据充足,逮捕了理查德。
从棒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到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性关系的 DNA鉴定,乃至“9·11”遇难者 DNA识别,李昌钰参与调查了8000多起案件。在美国,曾有警察问他:“这么多案子,您是怎么找到证据的?”他回答:“我归纳了7种简单方法——站着看、弯腰看、腰弯深一点看、蹲着看、跪着看、坐着看、各种方法综合起来看。”而他没有说的是,他坚持每天工作 16个小时。他家的十几个书房,每一个都是某一类卷宗的资料库……
妻子曾是他的“犯人”
李昌钰家是个大家庭,他在13个孩子中排行第十一。父亲去世后,母亲王岸佛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把子女全部培养成博士,这位了不起的母亲于2004年去世,享年106岁。母亲对李昌钰要求很严,他小时候不努力学习,就会被罚跪。长大后在美国工作,李昌钰通常7点到达办公室,一直工作到下午三四点。其间,他一般不接电话,哪怕是美国国会的电话,但母亲的例外。
太太宋妙娟也是他坚实的后盾。李昌钰在台湾当警官时,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姑娘宋妙娟正在台湾留学,因为签证过期而被带到警局,她可能要被罚款,还要拘留。李昌钰于心不忍,便出面处理此事。当宋妙娟走进李昌钰的办公室时,李昌钰对她一见钟情。为了能和宋妙娟保持联系,他告诉宋妙娟今天不处理,请她明天再来警局。就这样,两人的感情渐渐升温,最终走到了一起。
他们有一双儿女。李昌钰本希望能有一个孩子继承他的事业,但现在,女儿做了银行家,儿子做了牙医。他们告诉李昌钰:“爸爸,世界上有谋生更容易的职业,你这个职业太难了。”
李昌钰的做人准则正如他家中挂着的条幅——“至诚信义”。采访中,记者问他:“查案时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李昌钰坦言,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被害人的家属。李昌钰知道,找他的人都抱了很高的期望,这是对他的信任;而对待这种性命相托的信任,他唯有“至诚信义”——做事要言而有信,对人要以诚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