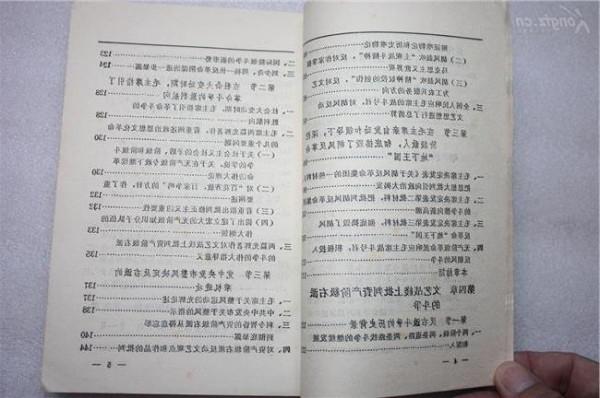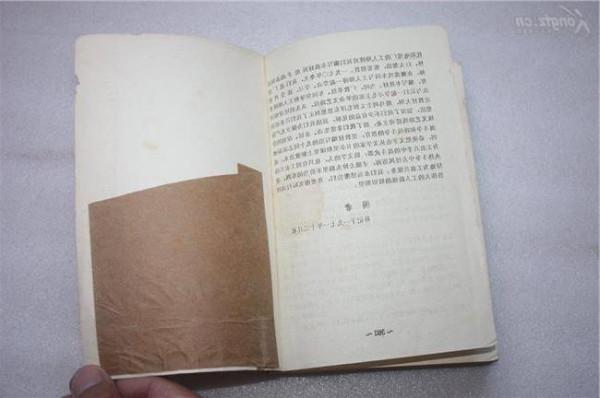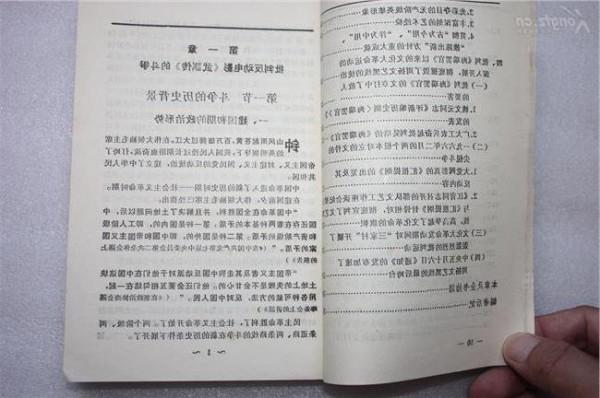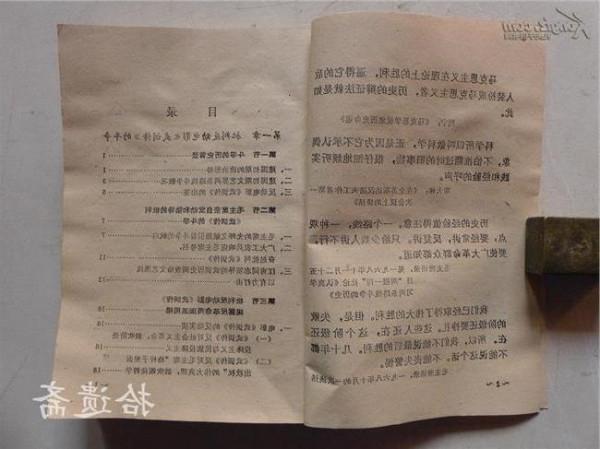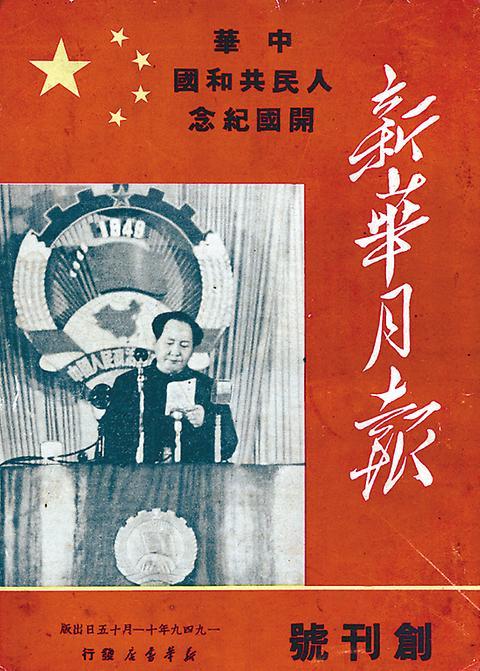胡风周扬 姜弘:胡风与周扬——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在纪念胡风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不由得想到了周扬,想到了胡风与周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复杂关系。
胡风与周扬都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骨干,分别代表着左翼文坛的不同倾向和派别。他们的思想和作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紧密相关。1949年以前,在文艺论战中,他们先是战友,接着就成了论敌。
1949年以后,文艺论战变成了大批判,周扬一直代表着政治权威和主流意识,领导着大批判;胡风则一直处于被批判地位,代表着当时和以后文艺上和思想上几乎所有的“异端”。他们都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继承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拥护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而互指对方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现实主义、反毛泽东文艺方向。
不幸他们后来又都以反马、反鲁、反毛的罪名而锒铛入狱。胡风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二十四年,周扬也受了九年的牢狱之苦。
七十年代末,他们劫后重逢,互致问候,虽不再争论,却也并未拥抱唏嘘,如传媒所渲染。胡风在继续他的思考和追问,周扬也开始了反思。在那几年里,他们都曾经激动、振奋、希望,然而最终又都不能不在惶惑、苦闷、忧虑中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
把胡风和周扬当作镜子,可以照见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照见知识分子的不同精神面貌。
先从七十年代末说起。
历史好像真的在兜圈子,“四人帮”倒台了,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十七年”,周扬复出了,“文艺黑线”也由黑变红了。于是,一些人故伎重演,再次落井下石,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再次重复当年诬陷胡风的那些虚假证词,为周扬的一贯正确作证。像茅盾、欧阳山、任白戈这些并非不了解真相的三十年代老人,大概是以为胡风已死,可以信口雌黄了。就在这同时,更多的三十年代文坛老人则刚好相反,他们在寻找、呼唤他们的老战友胡风。
1979年十月,在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上,周扬曾当众检讨,向以往被他整过的人陪礼道歉。他的这一举动,赢得会内会外一片赞扬声,人们以为周扬觉醒了,认错了。可是,一些对他深有了解的老人如李何林、楼适夷、吴奚如、聂绀弩、蒋锡金、丁玲等却将信将疑,持保留态度。
他们认为,周扬的检讨过于笼统,至于道歉,他所面对的首先应该是胡风,胡风已经获得自由却并未被邀请参加大会。于是,吴奚如出面向大会提出:请胡风出席会议,他自己就胡风问题作大会发言。
当时吴奚如把这个意见一直捅到了胡耀邦那里,弄得一些人手足无措。周扬连忙去向胡耀邦汇报解释,回来后找吴奚如谈话,传达胡耀邦的指示:“我和耀邦同志讲了,你那个关于胡风问题的发言就不要讲了,你一讲,别的同志像夏衍也要讲,本来是以团结为原则的大会就变成辩论会了。
其他人不了解当年的复杂历史情况,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大会就开不成了。胡风的问题,我保证向中央反映,促请中央尽早研究,然后我们找一些三十年代的老同志开个小会,争取半年内把问题解决。”
就在这个时候,他谈到了他和胡风的关系以及彼此的异同和短长,说:“我承认过去有宗派主义,不过胡风也有。胡风对文艺的理解很深刻,理论上自成体系,在今天的中国文艺界还没有谁能比的上,这方面他确实比我强。不过,我有一点比他强,我是一直紧跟党走的,而他却一直没有处理好和党的关系。
”当时,吴奚如还称赞了周扬,说他是政治家,紧跟历届中央;有能力,能领导资望比他高的田汉、夏衍;有魄力,敢于和鲁迅先生分庭抗礼。这话当然另有所指:说他不分是非,唯上命是从;有手腕,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正是在这些地方,胡风大为欠缺,而且个性强,认死理,坚持己见,竟敢发表与毛泽东的《讲话》不一致的意见,以致闯下了大祸(注)。
对此,胡风的看法和态度也很明确,说他和周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思想理论上的原则分歧,不应该纠缠在私人纠纷、个人恩怨上,也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的水平和性格问题。他认为:应该弄清楚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真相和思想理论是非。
在周扬说那番话的一年多以前,胡风在监狱里所写的检查交代材料里就已经对此提出了他的看法;第二年,1979年七月,在写给老友熊子民、吴奚如的信里,他说得更明白:为了避免“文革”式的灾难重演,必须找出“四人帮”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他认为“起源是在党内,在文艺上,就是五四以来的鲁迅方向与反鲁迅方向的斗争。
”三十年代的反鲁迅活动,延安的抢救运动、十七年的反胡风、反右派等等,是同一思想路线指导下产生的;周扬等人不是反革命,与“四人帮”不同,但在思想上理论上他们却是一脉相承的。
在拨乱反正的时候,周扬和胡风都已年过古稀,都曾经在监牢中面壁思过,又都是因文艺问题而获罪的,按理说,他们的思路和想法应该能趋于一致,殊途同归。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他们并没有走到一起。胡风的情况有些特殊,在他出狱前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在反思历史,他没有感到从“十七年”到“文革”的巨大落差,反而从历史的镜子里看出了“文革”的影子,发现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思想渊源。
周扬则不同,他从高位跌落到深渊,感到的是历史的颠倒。
在他的心目中,拨乱反正,就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三十年代也好,十七年也好,重要的是“文艺路线”的“红”与“黑”。他谈历史,不是“正本清源”,作纵向的历史考察,而是横向的类比,主要是检查自己在整人上的过失,也就是胡风所说的个人之间的恩怨。
正因为这样,1978年他接受香港记者采访,“笑谈历史功过”,面对近半个世纪血迹斑斑的苦难历史,竟然那样轻松愉快,毫无愧疚之意。谈到五十年代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反胡风、反右派等等,竟然用“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一语带过,好像与己无关,足见他对这一切并没有新的认识。
他对胡风的看法也没有改变。把他和吴奚如的这次谈话与1952年他对胡风的申斥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二十七年前,也就是1952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那个小型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在责令胡风检讨的时候,周扬严厉地警告说:“你说的话九十九句都对了,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全部推翻,全都错了!
”说得如此严重,如此确定,那一句话究竟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胡风也不知道,因为那是虚指。重要的是那个“致命的地方”,这个禁区是实有的,这就是政治,也就是党,党的领导。
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这个具体语境中,指的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方针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果你不是百分之百地拥护它,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那么,你对文艺的理解再深刻,再成体系,也全都没有用,全都要推翻,全都错了!
——99:1的奥秘就在这里。所以,1979年周扬在去探视胡风的时候曾不无感慨地对梅志说“他(指胡风)不懂政治!
”——这话里面不光有他的自信,也流露出他对胡风的怜悯。然而,一向以懂政治自许自恃的周扬,最后却栽在了比他更懂政治的胡乔木手下,其原因大概是他犯了和胡风同样的错误:在只能讲政治的“致命的地方”却大谈学术。
复出后的周扬不断发表讲话,在这些讲话里他一再承认自己在三十年代和“十七年”所犯的错误,还提到对鲁迅的态度和“国防文学”口号的问题,提到后来整人的过失,并且具体提到邵荃林、秦兆阳、王蒙、刘宾雁等等。应该承认,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并不是在讲假话敷衍。
比之于那些“决不忏悔”的人,他的这种态度应该得到肯定。但是,在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原则问题上,在另一些人身上,比如王实味、丁玲、冯雪峰、胡风这些人的问题上,他的态度就显得暧昧而僵硬。为什么会这样?只怕不单单是个人恩怨、宗派情绪,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理论原则和这些人的问题,全都和毛泽东有关,是毛泽东直接干预决定的。
他承认“实践是捡验真理的标准”,也反对“两个凡是”,但是有一点很突出,那就是他还有另一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讲话》里提出的原则和方针,都不能动,都必须坚持。他非常明确地坚持两条:一是从属于政治,二是思想改造。
他多次强调:“文艺还是从属于政治”,“不从属于政治不可能”。后来上面决定不再提这个口号了,于是他又“紧跟”,也不再提了,却说文艺应该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服务,因为“文艺是服务行业”。且不说艺术和科学原本就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行业”,单就这句话本身来看也并无新义,无非是转了一个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是当前的中心,也就是“最大的政治”,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服务,不就是为政治服务吗?可见,他并没有跳出老教条框框,文艺依然只是从属性的工具。
关于“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即“思想改造”的问题,他一再回顾历史,重述毛泽东的教导,说1942年有这个问题,1949年有这个问题,进入新时期依然有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看来他还没有悟出,这种否定五四传统,贬抑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反智谬说,正是造成历史曲折和民族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俱在,他还在念这本经,足见他还没有真正清醒。
有了这两个坚持,他那个“三次思想解放”论的提出也就不足为怪了。事情是明摆着的,当年延安整风所要求和达到的,是思想统一而不是思想解放。真正的思想解放,必须是思想上有选择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否则,只有单一导向的思想运动而没有批评论辩的自由,那只能是思想统一、思想统制。
当时是处在战争状态,所以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怎么能把这种非常时期的思想统制与正常情况下的思想解放混为一谈呢?更重要的是,军事政治与思想文化本属不同领域,性质和规律都不相同,前者要求统一政令,统一行动,后者要求自由思想、自由创造。
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靠“大一统”和“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繁荣思想文化的。上面提到的那两论:从属政治与思想改造,正是从军事政治的角度提出的特殊要求——战时的延安需要文艺充当宣传工具,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自由和自我。
相反,没有知识分子的个人自由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会有新文学、新文艺。这是两种不同的传统:以个性自由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以集中统一为原则的延安政治斗争传统。
周扬所代表的是延安传统,终其一生都在思想文化领域领导政治斗争,贯彻以服务政治和改造知识分子为理论支柱的《讲话》精神。到了晚年,他那两篇大文章,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纪念“五四”六十周年的报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基本上都是老调重弹,没有离开历次文代会报告的基调,没有触动那里面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绳索。
后来,他开始从理论上进行反思,却被胡乔木一棍子打懵了,从此一病不起,实在可悲。
胡风则刚好和周扬相反,他一直不接受上述理论和方针,他当年的获罪,主要就是为此。他认为这是文艺理论问题,可以讨论,可以有不同意见,他不知道这正是“致命的地方”,像误入白虎节堂一样,闯入了理论禁区,惹下了大祸。复出以后,他不但仍然坚持原耒的思想观点,而且由此出发,进而正本清源,明确指出:“文革”并不是灾难之源,而是以往的历史所造成的恶果,所以必须进一步找出造成灾难的真正原因。
近四万字的《〈胡风评论集〉后记》,是这位批评家复出后公开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在这篇长文里,他扼要地记述说明了他的九本评论集的写作和出版情况,并且谈到了与之相关的文艺运动和文艺理论问题。这中间,他特别强调鲁迅的作用和地位,充分肯定鲁迅的启蒙、立人的思想立场,认为鲁迅的道路就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道路。
他谈到了他直接参与的几次文艺论争,简单介绍了论争的起因和基本分歧,他把这些论争看成是继承五四传统和鲁迅方向与背离这一传统和方向的斗争。这中间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正就是上面所说的周扬所坚持的那两个问题,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不过他的看法和态度刚好和周扬相反。
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三个重要的概念:“形象思维”、“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在中国,胡风是最早引进和使用“形象思维”这一概念的,从开始从事文艺批评起,他就很重视文学的艺术本质和艺术特征,强调“追求人生”和“形象思维”。
谈到现实主义的时候,既称为“方法”、“道路”,又称为“态度”、“精神”。这说明他十分重视作家的思想立场、感情态度、意志人格等等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主观精神”、“主观战斗精神”就是从这儿来的。
鲁迅所说的“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不就是指创作主体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吗?——“形象思维”和“主观战斗精神”成为受批判的主要靶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