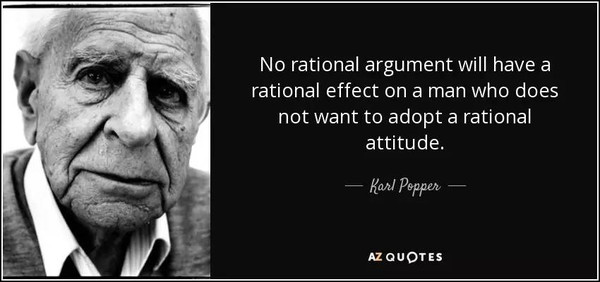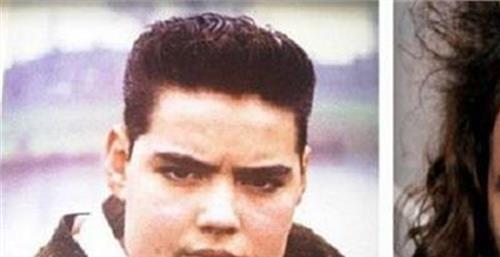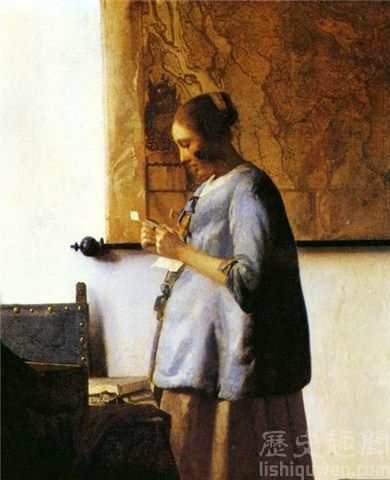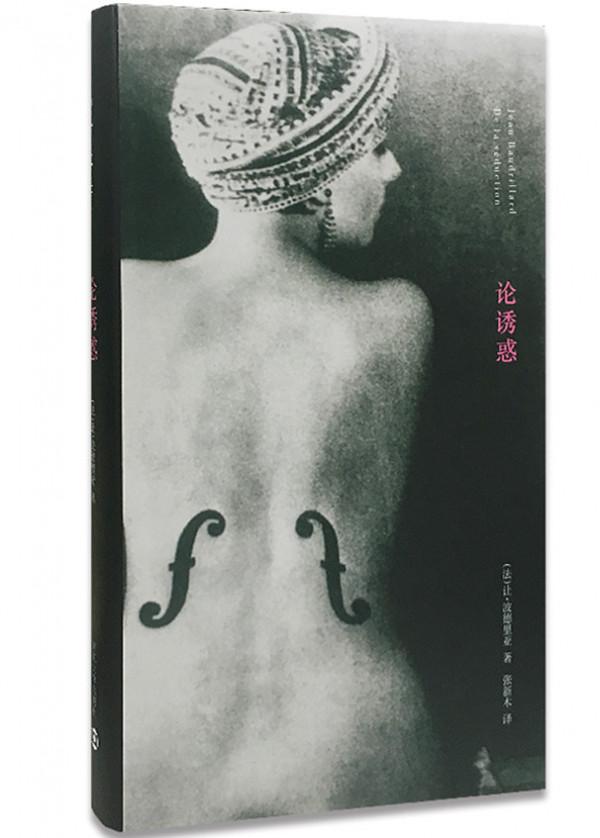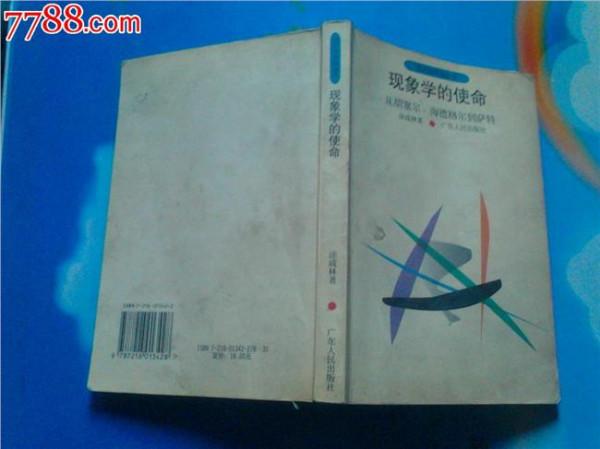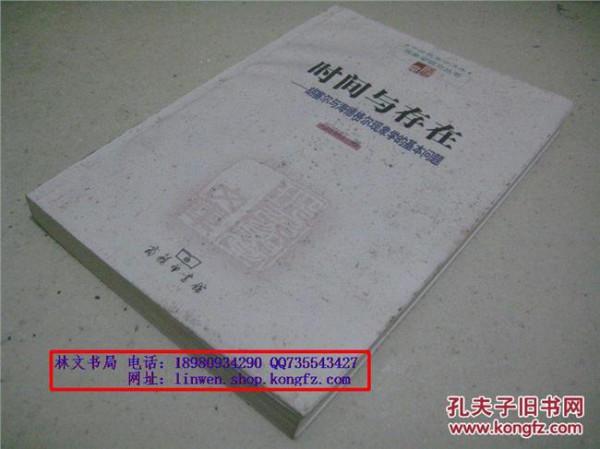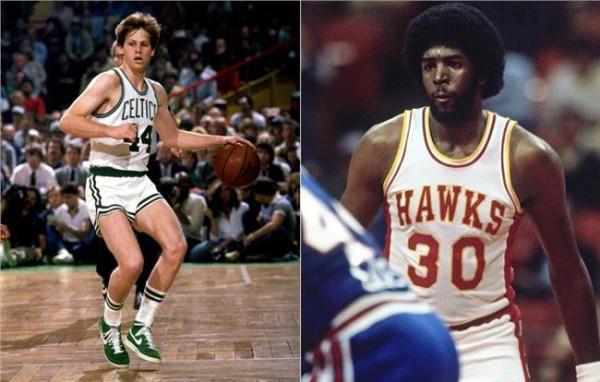胡塞尔的老师 皈依纳粹的海德格尔与犹太老师胡塞尔
1914年夏天,胡塞尔是哥廷根大学德高望重的哲学教授,而海德格尔刚刚在弗莱堡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他们对政治都不感兴趣,唯一重要的事情是思考。战争中,海德格尔两次被招进部队,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大学里竞争教席。战争中,胡塞尔的一个儿子战死,一个重伤,他的学术阵地也从哥廷根搬到了弗莱堡。
胡塞尔是一个爱国者,1914年“一战”爆发后,他的两个儿子都参军到西线作战,大儿子在前线战死,小儿子头部中弹躺在野战医院,得意门生赫莱斯也战死。胡塞尔为此感到自豪,在《逻辑研究》第二版前言最后写道:“我极有前途的学生赫莱斯已为国捐躯。”在 1917 年关于费希特的演讲中,他高度评价了费希特的爱国主义思想。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在1914年曾经写道:一场“地震”撼动了他。这次思想地震指的不是一次大战的爆发,而是他在阅读中第一次遭遇到了当时正被时代重新发现的百年前的诗人荷尔德林。自此,荷尔德林成为海德格尔毕生最钟爱的诗人。
弗莱堡大学的基督教哲学教席一直空着,海德格尔是有力竞争者,只要他能再发篇论文,就有机会获得。但这时战争爆发了,战争初始阶段的狂热情绪也烧到了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也得履行义务,幸运的是,他在军训期间就得了心脏病,这使得他重新回到书桌前。
海德格尔对自己未能直接征战沙场并不遗憾,他很清楚,自己的未来在讲台上而不是壕沟里,他要为论文为教席而奋斗,而不是做无谓的冲锋。当他的同事在为战争狂热或抨击这种狂热的时候,海德格尔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他的哲学狂怒并没有宣泄在政治上。
他是如此努力、专注和经营,但他在弗莱堡大学还是被打压了,有人认为,海德格尔的同龄人都在洒热血,他却在后方平步青云,这不公平。这一等是7年,这才拿到教席。但战争也不全是坏事,与教席擦肩而过的1916年夏,海德格尔认识了弗莱堡大学的女学生埃尔福丽德,后来的海德格尔夫人。
战争结束前,海德格尔又被召回到部队,他的工作是到前线气象站执勤——20年后,二战初期也有一个气象观察员,叫萨特。海德格尔目睹了德国的败退和战争带来的文明衰退,但他也认为,这也是失败带来的大清洗,新的精神将会诞生。
1916年,胡塞尔从居住了15年的哥廷根搬到了弗莱堡大学,他接替 H.李凯尔特在弗莱堡大学的教授职位——李凯尔特是海德格尔的导师。在那里他有了新的追随者。哥廷根时代的那些学生,大部分都去前线了,而且多数已经阵亡。也是在这个时候,海德格尔出场了。
海德格尔(右)与胡塞尔的学术分歧日益严重
海德格尔从1911年开始迷上胡塞尔的现象学,现在他是胡塞尔的学术助手,但海德格尔的魅力很快就超过了胡塞尔,而且两人的学术分歧日益严重。马堡大学希望聘任海德格尔为哲学系副教授,来咨询胡塞尔时,胡塞尔没有进行推荐,虽然他没对海德格尔作负面评价,但这对海德格尔的学术生涯还是造成了不良影响。
胡塞尔说他这位得力助手和继承人太年轻,太不成熟,而且是个天主教徒,马堡大学是所新教徒学校。事实上,胡塞尔是犹太人,而且是个新教徒。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真正的友谊要从战后才开始,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宣布脱离天主教会之后。但他们终归是两路人,尤其是海德格尔皈依纳粹之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惨烈最后改变了胡塞尔的态度和伦理思想,战争的后果和随后纳粹的兴起令他看到了欧洲文明的根本缺陷,看到了隐藏在这些恐怖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和病症,在他看来,战争在战争结束后依然继续着。他说对了。
胡塞尔还指出,这一时代的悲剧充分表明,欧洲已经失去其追求“理性目的”的伟大抱负,文化意义上的“欧洲”曾经相信充分的理性存在,相信人类所具有的正确判断事物的理性能力和对自身行动的洞察力,而现在这一切在欧洲都似乎荡然无存。
而在海德格尔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无意义的自我毁灭,原因是欧洲各民族国家不能创造性地解决它们的问题,而是投入到外在的统治世界的斗争中去。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在精神上为虚无主义所支配,而在政治上则陷入不断的军事冲突。
战争结束,海德格尔的哲学王国开始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