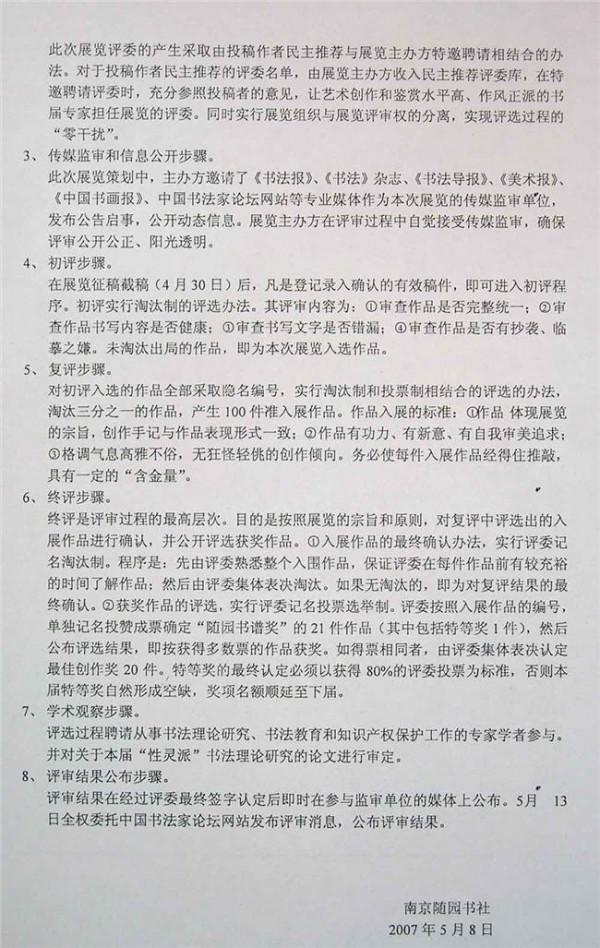社会学田耕 【“大学堂”讲学计划】著名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鲁赫特来北大讲学
【“大学堂”讲学计划】著名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鲁赫特来北大讲学
新闻纵横
新闻纵横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著名社会学家、海德堡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于2017年4月访问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发表系列演讲,并主持读书会。
施鲁赫特教授堪称在世最重要的韦伯研究者,是韦伯全集(Gesamtausgabe)的主编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涵盖社会学理论、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施鲁赫特教授关于韦伯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为其他研究者设定了很高的标杆,其中两部已有中译:《现代理性主义的兴起:韦伯西方发展史之分析》及《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
讲学活动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国际合作部共同主办,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4月10日晚,施鲁赫特教授的首场演讲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举行,演讲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主持。本场讲座题为“《以学术为业》发表100周年”。1917年11月9日,韦伯在慕尼黑大学发表了这次著名的演说,1919年3月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高潮,胜负尚未明了。当时亲历这场战争的学生希望邀请一些知名学者来回应他们的困惑,这便是“以脑力劳动为业”系列演讲的缘由,首篇就是韦伯的“以学术为业”。
当时的德国教育体系也处在转型时期,一是韦伯所谓的“美国化”或官僚化;二是“专业化”兴起;最后是学术的“经济化”,学术机构愈益成为等级化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而青年学者处于“近乎无产阶级的生活状态”。
施鲁赫特教授在演讲中
热情地献身学术意味着什么?施鲁赫特教授引用韦伯的话说:“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科学无法直接告诉我们应如何生活。现代科学只是一个价值领域,它与其它价值领域永不止息地斗争,不可调和,但它并不是最高的。
不同于政治家,科学家应当克制自己,避免价值判断。真正的科学家甚至请求被人超越,希望相形见绌。现代科学要求自明性以及责任感,才不会越过科学的限度,将科学变为意识形态或者世界观。最后,施鲁赫特教授总结道:“不论小科学大科学,我们应当以伟大的科学为业。”这是每一位以学术为业的人都应努力实现的目标,正如韦伯的思想直至百年后仍然鲜活。
施鲁赫特教授与李猛教授进行对话
4月17日晚,施鲁赫特教授发表了第二次演讲,题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过去与当下”,从理论视角而非历史视角来切入资本主义的问题。本次演讲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主持。施鲁赫特教授选择了马克思(19世纪中期)、韦伯(19至20世纪)与波坦斯基/夏佩罗(20世纪末)这三种理论立场。
马克思的框架是我们熟悉的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韦伯批判了马克思的框架,构造形式与精神之间的选择性亲和,而没有采用因果决定的关系。波坦斯基与夏佩罗在形式与精神之外新增一个要素,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三要素的相互关系为基本框架。所谓批判是出于对不公的义愤,包括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动力。
在韦伯看来,精神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结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自有其历史,正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推展的那样,经济上的行动者可能倾向于采取特定的生活方式:对营利欲(Erwerbstrieb)加以理性的调节。
营利欲是人的自然倾向,资本积累本身无法为资本主义赋予正当性,它必须有文化的维度,才能具有结构。针对韦伯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僵化的问题,波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广泛关联的世界有可能滋养出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其核心为独立、创造力、原创性、团结等等。
4月20日晚,施鲁赫特教授发表了题为“祛魅的辩证法:世俗时代的宗教”的第三次演讲。本次演讲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主持。“祛魅”是韦伯最著名的概念之一,流传甚广却难免被误用,施鲁赫特教授力图通过这次演讲澄清韦伯“祛魅”的语境和意涵,尤其是它与所谓世俗化命题(secularization)之间的关系。
他以泰勒的名著《世俗时代》开启演讲,在泰勒看来,祛魅等同于世俗化,始于1500年前后。韦伯却并未将祛魅等同于世俗化,对韦伯而言,祛魅早在古犹太教就开始了,至禁欲新教达到顶峰。
按照宗教史上的一般趋势,此世与彼岸的裂隙逐渐加深,双重世界变为二元世界(dualistic world),救赎宗教顺势而生。
宗教的祛魅是指救赎手段的去巫术化,它是宗教理性化的一部分。“要判断一个宗教所代表的理性化水平,我们可以运用两个在很多方面都相关的判断标准。其一是这个宗教对巫术之斥逐的程度;其二则是它将上帝与此世系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与世界建立起一种伦理关系。”祛魅发生在宗教内部,它主要贬抑了神圣与信徒之间所有媒介的价值,而不意味着世俗化。
17世纪以降,宗教祛魅由新兴的科学祛魅所继承。对现代人而言,科学意味着一种新的多神论,它必须自我限定,“主宰这些神祇及其斗争的,自然不是‘学问’,而是命运” 。祛魅意味着不可调和的诸神之争。从韦伯的角度来看,宗教决不会被世俗化消解,它回应着人最根本的需要,只不过宗教逐渐成为一种个人选择。宗教成为选择,意味着你必须具有宗教上的反思性。宗教的确不会消亡,但宗教的内部结构要发生改变。
4月24日晚,施鲁赫特教授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题为“法律社会学:涂尔干与韦伯之比较”,并与著名涂尔干研究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对谈。涂尔干的社会学即“民情与权利的科学”。他指出,随着社会分工推进,压制性法逐渐被恢复性法所取代,机械团结逐渐为有机团结取代,原先崇拜群体转为崇拜个体,前现代社会的宗教世界观转为现代社会的世俗世界观。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有别于凡俗化(profanization),它并非宗教截然的对立面,任何社会意识之内都蕴有圣俗之分的结构。
只不过宗教不能一成不变,现代社会整合需要一种新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公民宗教的概念源自卢梭,经涂尔干发扬后又被罗伯特·贝拉所继承。它围绕着抽象的个人,以理想的“人格”(personne humaine)为核心,并且受到压制性法的保护。
正如他的一贯作风,韦伯对法律首要的兴趣是要理解西方的独特性。他先划分形式——实质,又区分了理性——非理性,构建了四种理想类型:“形式的非理性”是卡理斯玛禀赋者受到启示才触及的神法;“形式理性的”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学家所制定的实在法;“实质理性的”是哲学家理解或思考得出的自然法;“实质的非理性”是继承而来的传统法。
韦伯所理解的法律演进是法律形式理性化的过程,然而它自然会促生对法律实质理性化的诉求,人们总是期待着法律能实现“正义”,尽管现实中人们更清晰地感到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的冲突。
对涂尔干而言,世俗化同时也是世俗法律要素的“神圣化”。韦伯将社会学严格限定在经验效力的分析上,神圣性的问题被归为价值判断,已然超出经验科学的限度。所以,施鲁赫特教授称涂尔干为“社会学的康德主义”(Sociological Kantianism),是“社会学版本的康德”;韦伯则固守经验科学与哲学的界限,顶多是涉及康德哲学的社会学(Kantian Sociology)。
除上述系列演讲外,施鲁赫特教授还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发起和组织的“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经典文献读书会,并担任领读人。4月9日至22日,施鲁赫特教授应邀主持三场读书会,带领相关学者与研究生,围绕“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社会科学中‘价值自由’的意义”“以政治为业”等韦伯代表性的文本进行讲解和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孙飞宇、田耕以及近20名同学参加了读书会。
施鲁赫特教授主持韦伯经典文献读书会










![费孝通名言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https://pic.bilezu.com/upload/3/ec/3ec522368476e234c3ea3796c797095c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