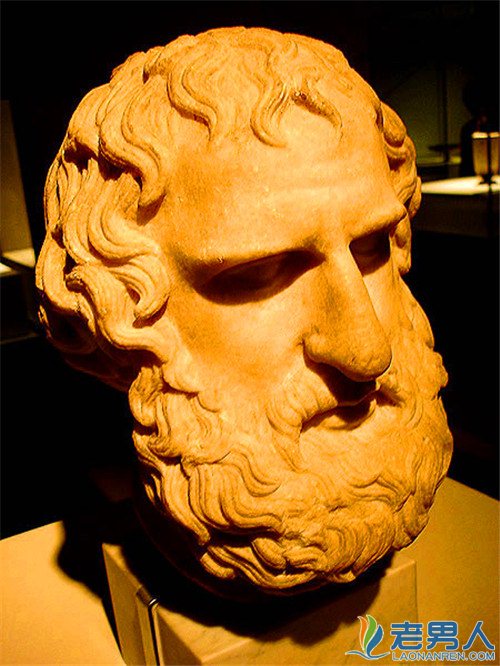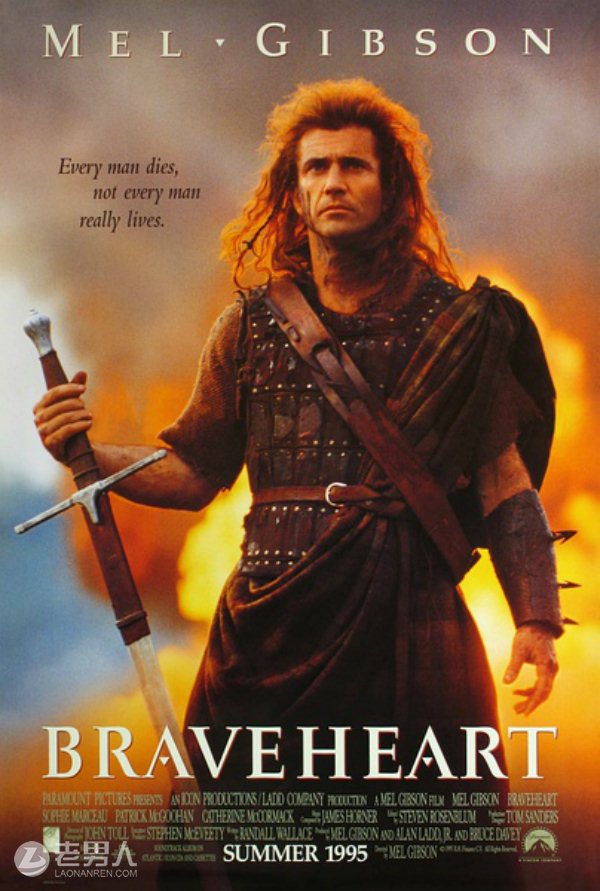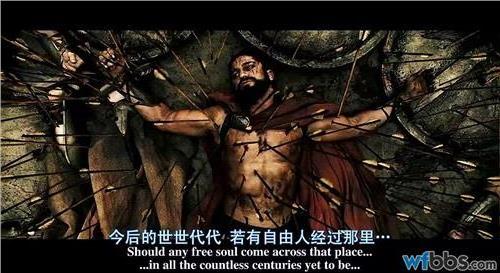罗昌平打铁记六:开门查水表
离开办公室,我给《财经》兼《LENS》杂志的掌门人法满打了一个电话,表达了歉意,因为这么大的动作事先没跟他通气。手机信号极不稳定,来回两次才听清电话那头的声音:“弟,你干嘛要举报我不关心,你有没有事先通气我不关心,其他的我都不关心,我现在唯一关心的是你的安全。对方说报案报警了,你要做准备,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联系。”
我鼻子一酸,坐在嘈杂的街边,平静这半天来的杌陧悬旌。
《财经》行政总监颜晓群也打来关切电话,他与法满是参与《财经》创刊的元老。按照内部流程,编辑部的善后事宜设有防火墙,即一旦有事,先不将记者编辑推向前台,由行政系统应付两轮,万不得已再适时介入。这位大管家替我挨过的骂,担过的责,数见不鲜。
行政通知,当晚是《财经》年会的庆功宴,高管必须参加。一年一度的《财经》年会每临岁末举行,可谓民间政经论坛中规格最高的,迄今为止,已有吴敬琏、江平等学界泰斗及不少于十名诺贝尔获奖者,美国前总统卡特、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王岐山及“一行三会”掌舵者悉数到会。它不仅每年收获上千万赞助费,还是这本杂志的人脉广场和政商平台。
但我回绝了这场庆功宴,一来在此关键时刻不能沾酒,二来尚无准备面对那么多同事。实际上,我和刘铁男成了当晚挂在大家嘴边的一对热词。
这时大约16点,我赶往长安街上的北京国际饭店。陈晓舒短信说,她要见谢晓东——两人曾是我不同时期的前同事,谢晓东是我在《新京报》带的实习生,现任匡时拍卖副总经理;陈晓舒曾是《财经》唯一的“法治宝贝”——我来牵线搭桥,让他们成为新同事。传媒这个行业的悲凉之处在于,即使为时不长的十年新闻苦旅,已经迎来数拨应届生,并又目送数轮改行者,自己不经意间成了“前辈”。
对于我当天的状态,两人给出了并不一致的印象。谢晓冬的说法是:“发生这么大事,你还悠哉悠哉的,有空帮人介绍工作!”陈晓舒事后回忆:“他说来就来了,到了之后就心不在焉起来,好像听不到我们说话,心里有事的样子。”这位被宠坏的“法治宝贝”习惯于主角优势,显然并未细心到发觉微博举报这档事儿。
彼时的“心不在焉”,源于应接不暇的电话短信。那些纷至沓来的问候读来温暖。老领导杨斌微信短信并举:“看到你的微博举报了,注意安全。最安全的做法之一,是将所有的威胁公之于众。”他与程益中曾是相继被免的《新京报》两任总编辑。
香港友人梁海明的短信更为直白:“虽预料你电话会被监控,但还是要发短信鼓励和支持。加油,保重!”
邓飞在来电中说:“这把玩得真大,刘铁男肯定完了,但这些省部级高官会抱团防备我们,你想他们有多震惊。”在调查记者这个群体里,湖南人以“霸得蛮,耐得烦,了得难”的独特风格保持着最高比例,并组成不太稳定的职业共同体。
年龄相仿的邓飞、欧阳洪亮、龙志与我被合称为“湖南四害”,一度成为新闻湘军的主力。但现在,年长的邓飞从良做起公益,他更乐意以“湖南四虎”外称;最小的龙志进了网易,探索新媒体路径;欧阳洪亮与我同事,他在重灾区与温柔乡之间消磨着战斗力。
这真是令人伤感的时代与行业,“80后”居然开始怀旧了。
好在新生力量已经迅速成长,比如当时准备出差的张鹭,闻讯跑了过来。他与陈晓舒的同事关系由《中国新闻周刊》平移到《财经》,和我一样是浓缩的小矮个,爱吃辣椒的湖南人。除了采访突破略显乏力,良好的理论底子、缜密的逻辑推理与老练细腻的文本,是他在同行中脱颖而出的资本。
在刘铁男这件事情中,张鹭本来是当事人,他既是《中国式收购》与《倪日涛沉浮》的第一作者,也是中央纪委早前问讯的对象之一。在由主角切换成为配角的过程中,我欠他一个解释。
我们闲谈也就半小时,“夜店皇后”晓舒还要赶她的饭局,小鹭也着急于他预订的航班。看着展览中忙碌的晓冬,尴尬地发现自己是多余的,于是转身告辞。
在抵家之前,有一个半小时的地铁行程,我不停地刷微博、玩游戏,直到耗尽这台手机的最后一点电池。
回家,通过安全方式向分别供职于纪委、国安、军方的三方密友发出要约信息,请求他们帮忙收集一切官方动态。然后,煮饭、洗菜、备料……等着夫人回来。她在午后得知举报的第一反应是:“胖子,你又调皮了。”
从刘氏团队答复《新京报》的短讯来看,他们当天会采取四项“明面上的”行动:一是联系网络管理部门报案,二是联系公安部门报警,三是采取法律手段,四是刊发正式的新闻稿。能想到的“暗地里的”举措,包括组织内部的游说与维稳机器的调用。
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反击策略。就“明四点”而论,我最希望看到的是第三条,“采取法律手段”,哪怕自己被诉诽谤,毕竟在法治轨道之上。
刑法第246条规定,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此罪侵犯的客体与侮辱罪相同,是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名誉权。侮辱、诽谤属于自诉案件,应当由自然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但立法者为当权者开了一道模糊的“口子”——当侮辱、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可以启动公诉程序。
什么是社会秩序?什么是国家利益?解释权当然归立法者和当权者。
本朝因言获罪的法律设置,从治安法对散布谣言的行政处罚,到自诉诽谤罪、公诉诽谤罪,再到诬告陷害罪,是一个阶梯式的惩罚机制,广泛适用于官对民。然而,每个阶梯并无明确的界限,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法律问题的政治化,更进一步导致边界模糊,苏联的红色段子可以形象诠释“从个体人格到国家利益”的跨度:一个人因为对着领袖像大骂白痴,被判刑10年,其中9年是辱骂领导人,1年为泄露国家机密。
吼吼,不妨划一个等式:国家利益=国家机密≈领导智商≈贪腐证据……
理论上讲,只要法律中有侮辱罪和诽谤罪条款,因言获罪的阴影就不会散去。正因如此,在保护人权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国际上出现了诽谤去罪化的大趋势。当然,本案的焦点并不止于言论自由,还涉及到举报人保护制度,此为后话。
但恰恰相悖,你最希望出现的方式是刘铁男最不想采取的方式,他习惯于密室作业。在刘氏反击策略中,其他三条都涉及强势部门,且精准针对新闻人,如第一条与第二条交叉部分是警察,有强制力;第一条与第四条涉及文宣系统,正是新闻人最无奈的宿敌。细加综合,亲友关心的安全问题详列如下:
——文宣系统可以影响职业,最糟糕的是永久性除名,不至于有人身威胁;
——警察系统对人身自由和心理负荷构成影响,不会丢命,除非发生意外;
——刘铁男方面综合发力,多重打击,轻则威胁恐吓,重则暴力相向;
——倪日涛马仔的报复,类似上一条,手法偏重,比如闷棍、交通事故;
——他因。如纯粹的意外事故,或企图嫁祸刘倪的特殊预谋(电影看多了)。
就时间而论,文宣系统当晚反应的可能很大,但仅限于对微博及账号的封杀,职务撤免需要很长时间;警察上门与党羽黑手的机率最大,不排除用力过猛导致意外,应该重点防备。我能采取的方式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不自驾车,无固定的饮食习惯与出行路线。切断自己的通讯工具,尤其隔离微博微信这类社交媒体,以及居住在一个不在自己名下的房子里,这算是临时性避险策略。
当然,组织真要找你,无处可逃,插翅难飞。
我把同事法满、丁补之的手机号写给了夫人,提示如果当晚确有警察上门,记下警号,第一时间通知这两个人,并视情况发微博呼救。
只要三条举报微博没有被删除,就意味着那道安全阀还没有完全脱落。它是悬于我内心的一根防线,或者说是最后那根稻草,也是权力系统是否深度介入的风向标。
“开门,查水表!”
“水表在外面!”
“开门,邻居借醋!”
“我家没有醋!”
“开门!消防队!”
“我家没着火!”
“查水表”,一个琐碎工种发展成为一句流行语,先有借此入室抢劫的歹徒,进而托谎敲门办案的警察,警匪一线之隔被引申为因言获罪的网络调侃。
当晚,确实有人找上门来了,只是他们一开始找错了地方,去了二环内的一套小公寓。这套公寓挂在我的名下,房客证实当晚确实有人前往探访,后来我也收到了物业公司“是否在家,要抄表”的问询短信。至于对方是警察的公务行为,还是受人之托的私人之举,抑或是不明身份的其他人士?不得而知。
在职业生涯中,我曾跟北京警察有过两次交锋。
一次是2009年6月3日深夜,公寓的门口、电梯、楼道布控了不止十名警察,我被带到最近的派出所。先前一个小时的盘问,不明就里。后来才知道,当天接收的一封来自四川的电子邮件,发信者是被重点监控的敏感人物。结束两个小时的问讯,他们一无所获,把我送回家。彼时妻子已经熟睡,我问她不担心吗?她回答:“天天跟你一起过日子,还不清楚你?又没犯法,担心什么?”
另一次是臭名昭著的安元鼎事件。2010年9月20日傍晚,4名警察气势汹汹闯入泛利大厦19层——也就是《财经》编辑部,要求带走《安元鼎保安公司专职截访》一文的记者。这是第一篇披露地方政府委托保安公司拘禁并遣返访民的新闻报道,作者是谭翊飞,主管编辑为我的搭档丁补之,但警察造访之时,他们分别在印度游历和日本探亲。行政系统经过多轮处理仍然无法支走对方,我作为这组报道的审核编发者,算是当时在京的唯一知情人。
那天晚上动静不小,法满、颜晓群一直在沟通,后来叫上两名法律顾问浦志强、王建勋,最后是老板亲自坐阵,他将四人警号录入短信发给委座的近侍,后者反馈给市局,得知报道获得顶层批示,警察前来确为履行公务。因此特殊人脉,对方派出另一批警员,态度大为好转,但仍然必须见到我,由我详细介绍报道产生的来龙去脉,并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愿意配合调查。直到次日零时11分,我应约赶到编辑部,当众完成笔录。
这一风波的发生,为数天后龙志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两万余字的安元鼎调查,起到了风险摊销的先兆作用。
面对警察这样的强势部门,《财经》有两条恪守多年的善后信条:一是不能让记者编辑进去;二是万一进去了,不能在里头过夜。或许受此潜移默化,我在经历12月6日的回黄转绿之后,选择了躲避,尽量不将自己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发生正面冲突,因为再大的民意声援也无法改变维稳系统的惯性。
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对暴力的垄断,军队与警察是重中之重。和平年代,作为与军队有着最大亲缘性的警察队伍,涵括了人从摇篮到坟墓、从自由到生命的最宽泛交叉,但至今尚未摆脱战争动员体制的路径依赖。
此时的刘铁男显然愿意不惜成本启动立体公关,他当天决定秘书王勇飞回北京,专职善后。不过,作为“条条”上的行业首长,他可以在能源审批领域无法无天,但调动警察这类拥有强制权的力量,还不如“块块”上的县委书记,除非双方有可以对换的条件,或者更高层级的干预。这是区别于权钱交易与权色交易的权权交易,在文宣系统运用较为普遍。
据纪委、国安与军队三条渠道事后的反馈,当天晚上及至接下来几天,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并非按兵不动,而是动而未彰,我的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甚至一辆无牌监视警车,就在我居住的小区内守到天亮,只不过命令一直没有下达。
西方有所谓基于良心的不服从权,尽管中国的公务员法也有类似表述,但孤悬的法条因缺乏系统的制度支撑而弱不禁风。纵然他们没有响应刘氏意志,或许仅是对乱局难辨,未必出于良心坚守。
一直漂泊在体制的围城之外,我对于城内的权贵自有良言相劝,以步步行善对应前文的阶梯惩罚:不作恶,即是善→先依法,再依良心,最不济依人性→迫不得已作恶,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换用《庄子》的古典表达:“与其残民以逞,不如曳尾于泥涂。”
那一夜,直到获知国家能源局网站撤下刘王的俄罗斯合影,我才如释重负。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次日凌晨,在距离举报微博20小时之后,我打开手机,拍下天空,发微博报平安:“晨跑途中大美!过渡时期多有层次感,阳光一出,乌云必散。套用高尔泰那两行歪字:闲却经纶手,高楼绘竹枝。先生画外意,难话亦难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