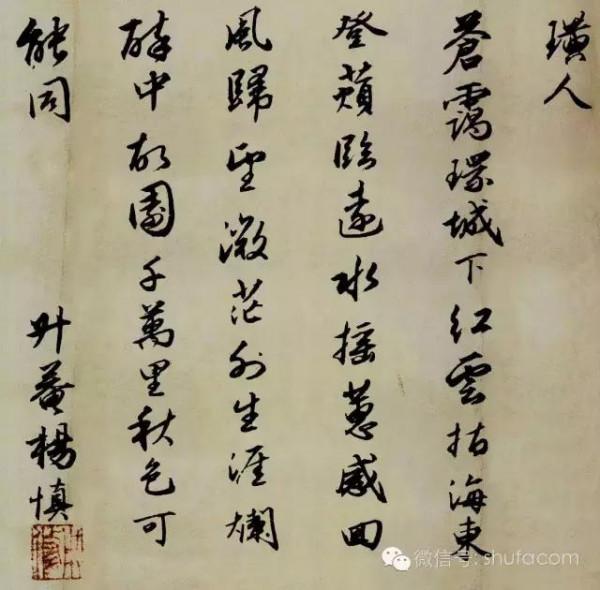童庆炳严羽 童庆炳:严羽诗论诸说
宋随唐后,宋代诗人所面对的情况是严峻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幸”的。因为唐代数百年间,中国诗歌已发展到鼎盛时期、颠峰状态。近体诗的形式完全成熟,古体诗更被人所自由运用,唐代诗人如群星灿烂,佳作秀句似百花争艳。
在后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感情都被抒发尽了,一切境界都被写得淋漓尽致了,一切艺术手段都被用得炉火纯青了。对于诗歌似乎唐人已无所不包,它不给后人留下一点空间。宋代诗人王安石惊呼:“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
”[1]在这种似乎一切都已被唐人“道尽”的情况下,宋代的诗人无不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宋代诗人和诗学家一直在寻求宋诗的新的出路。综观整个宋代诗学,宋代的诗学家给当时的诗人指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诗学路线,一条是以苏轼为代表的所谓“天成”、“自得”、“超然”的路线,它的实质是强调诗歌的创作要表现自己内心的所得,摒除功利得失,以审美的精神,达到自然平淡的境界(苏轼的诗学思想很复杂,这里就主要倾向而言);一条是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强调学习唐代诗歌遗产的路线,黄庭坚认为唐代最成功的诗人是杜甫,而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因此主张作诗要有“夺胎换骨”的功夫,它的实质是强调诗歌创作要充分吸收前代诗歌艺术遗产。
由于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指出了一条“可操作”的学诗、作诗的路线,所以从北宋到南宋的长达200年间,许多诗人都受其影响,“加入”江西诗派的“行列”,甚至像优秀诗人陆游、杨万里的早期,也受“江西诗派”的“浸润”。
应该看到,“江西诗派”中的确产生了像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等优秀诗人,对宋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对整个“江西诗派”的评价我们必须十分公允、慎重。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对“江西诗派”的理论和实践,一直是有争议的。
在南宋、金、元朝时期,倾向于苏轼的诗学路线,强调“自得”、“天成”等创作思想,并批评“江西诗派”的理论和作法的,有好几家,如南宋姜夔主张“独造”,金朝的王若虚主张“自得”,金、元间的元好问主张“以诚为本”,他们都指出“江西诗派”的理论和作法不足取。
但真正发挥了苏轼的创作思想,同时又别开生面,从禅家学理上进行有力论争,并在其后引起广泛争议的是严羽。他的批判之所以有力,是由于他针对江西诗派末流的流弊,提出了几种影响较大的诗歌学说。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所以他的诗论在身后反对他的人有之,赞赏他的人也有之,影响十分巨大。
严羽,字丹丘,一字仪卿,福建绍武人,自号沧浪逋客。生卒年不甚详。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约生于绍熙三年(1192)左右,卒于理宗淳祐年间(约1246)前后。[2]这是南宋为北方的强敌和内部的纷争所困扰的时期,社会黑暗,人民遭受苦难的时期。
严羽的主要著作是《沧浪诗话》,这是宋代一百多部诗话中系统最为严密、理论最为深入、影响也最为巨大的一本诗话。全书分六部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最后还有附录:《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最有理论价值的是“诗辨”这一部分。
《沧浪诗话》的最大特色是“以禅喻诗”。当然,“以禅喻诗”不是从严羽的《沧浪诗话》开始的。以禅境比喻诗境,从唐代就开始了。如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
神鬼闻如泣,鱼龙听似禅。
另外唐代诗僧皎然《答俞校书冬夜》:
月彩散瑶碧,示君禅中境。
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
皎然的《诗式》已开始用一些佛学的概念来解释诗的创作和欣赏。北宋开始流行学诗似参禅的说法。如苏轼《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
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这明显地把在欣赏诗的过程中的诗境与禅境作比较。后来吴可就把“参禅”与“学诗”的相似之处更明确的指出来,他的《藏海诗话》有三首《学诗诗》: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
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
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
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
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传至今。
此外作为江西诗派代表的黄庭坚的著作中也有“悟入”、“神会”等说法,也是与禅有关系的。他的学生范温所作的《潜溪诗眼》中也常谈到“悟入”,如说:“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
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盖古人之学,各有所得,如禅宗之悟入也,山谷之悟入在韵,故开辟此妙,成一家之学,宜乎取捷径而迳造也。……”应该说,上面这些所谓的“参禅”、“悟入”等,都只是认为学诗和参禅都需要领悟,诗与禅之间在方法上有相似之处,并没有把参禅与学诗认真地联系起来谈。
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与上面这些说法的不同之处在于,严羽不仅仅是把诗境与禅境相似之处作一些比较,也不仅是一般的将学诗与参禅从方法上作一些比较,他的目的是想通过诗与禅的类比,暗示诗的本质与禅的本质的相通,诗的创作与参禅过程的相通。特别是他的以禅喻诗有明确的针对性。并提出了“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和“妙悟”说,揭示宋诗的流弊,同时推进诗学的发展。
一、作为题材论的“别材”说
如前所述,宋代的诗人不管自觉不自觉都面临一个如何学习和超越唐诗的问题。当然宋诗从北宋到南宋的确也形成了一些特色,其中最主要的是以才学、议论入诗,这应该说是宋诗的一个发展,有人对此加以肯定,但严羽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沧浪诗话》中说: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为一厄也。
在这里,严羽用“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三句话作了比较准确的概括,然后指出这种诗歌即使是“工”的,也缺乏“一唱三叹之音”,缺乏“兴致”,或一味“使事”,或“叫噪怒张”,失去了诗歌的审美的品格。
当然,严羽也肯定宋代诗人向唐代诗人学到了一些东西,而且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但这句话是肯定苏、黄,还是贬抑苏、黄,就值得讨论了。实际上,严羽对宋代的以黄庭坚为代表的主流诗派,多采取否定态度。
严羽与黄庭坚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对诗为何物,即诗的本质特征是什么问题上的分歧。严羽的思想超越了“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他显然认为在“志”和“情”这两个字上找不到诗与非诗的区别,找不到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
在严羽看来,在“言志”、“缘情”上面很难找到诗之为诗的标志。而宋诗的发展则又进一步把“言志”、“缘情”泛化,“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尤其是“江西诗派”的末流,更只在前人的书本中乞讨,就完全失去诗的本旨,也就更进一步模糊了诗与非诗的界线。严羽针对这个情况,在《沧浪诗话》中提出了“别材”说和“别趣”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严羽在这一段话中,首先提出了“诗有别材”的论点。关于“别材”说,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把“别材”的“材”理解为“才”。按这种理解,“别材”的意思是诗人是有特殊才能的人。诗人与学者是有根本区别的。诗歌吟咏情性,情性中有诗情画意者,就可能成为诗人。如果情性中无诗情画意者,他可能读很多书,对问题有很多见解,他可能成为一个学者,却断不可能成为一个诗人。
虽然,诗人读书也是有益的,但读书、学问不是诗人的最基本的条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孟浩然“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
原因是孟浩然的学问不如韩愈,但他作为诗人的独特的才能超过韩愈,所以孟浩然的诗超过韩愈。宋代人的诗,特别是江西诗派的诗过于重视用典,把古代的文、史、哲等著作的知识大量纳入诗里面来,主张“无一字无来处”,以学问为诗。这在严羽看来,就没有把诗人应有特殊的才能这一点搞清楚。严羽心目中的诗不是学问的堆砌,是诗人情性的流露,情性中若没有艺术的种子,即没有艺术的才分,学识再多也没有用。
尽管这第一种解释是有道理的,但我还是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别材”的“材”就是“材料”、对象、题材。“别材”说的意思是,诗在取材上别有要求,既非一般的“言”、“情”,更非“文字”、“才学”和“议论”。在严羽看来,宋诗之所以不如唐诗,尤其是不如盛唐诗歌,根本的原因在于宋诗在取材上出了问题。
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书”在古人的概念中,是指“经”,“史”、“子”、“集”,范围十分广阔,包括了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等。
严羽显然认为“书”与“理”相关,既“涉理路”,又“落言筌”,不是从人的活的情性中来,把“书”或“理”作为诗的对象是背离了“诗者,吟咏情性”的旨义。严羽的“别材”说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他显然是针对黄庭坚如下极有影响的话: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耳。古之为文章者,其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3]
这段在当时曾激动过多少诗人、推动过宋诗的发展的话,在严羽的眼中,正是导致宋诗不如唐诗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黄庭坚认为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的说法,无异于引导诗人一味到古人的书本里“讨生活”,在诗歌里面卖弄学问,把“书”(而不是把自己的切身感受)作为诗歌的泉源,使诗歌里充塞了古人书本的陈言死句,这岂不背离了诗歌的真义?所以严羽讲“诗有别材,非关书也”,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诗学命题:诗歌有没有自己的独特的对象?哪些可写,哪些不可写?而且作出自己的回答:诗歌应该写活的、可以一唱三叹的、人的情性,诗歌不应该写古人书中的陈词滥调。
但严羽又没有否定诗人应该读书,他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意思是把读书作为加强诗人的修养的条件,多读书、多穷理,正是为了挣脱“书”与“理”的束缚,涵养人的真实情性,所以“别材”又有待于读书而达到极致。
严羽的“别材”说,后来遭到不少封建卫道士的攻击,认为严羽反对诗人读书,认为他主“俗”反“雅”、主“鄙”反“典”,说什么“天下惟雅须学而俗不必学,惟典则须学而鄙与弇不必学……”,甚至斥责他“欺诳天下后生”等等[4]。
后来的一些儒生这样攻击他,主要是因为严羽的诗学理论“伤害”了儒家的“诗言志”的传统。实际上,严羽的诗歌“别材”说,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不但是诗歌,而且整个的文学,都有其独特的对象,(即“别材”),文学与其它的人文学科的对象都是人。
但当我们试图分析文学与其它的人文学科的区别时,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与其他具体学科的区别,并不像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内容时所用的方法。
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5]。如严羽所说的那样,诗有“别材”,非关学问。诗有自身的独特对象,否则,诗歌的独立存在就没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