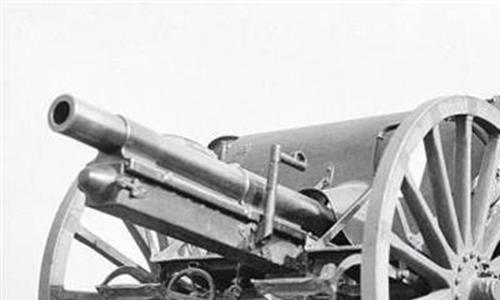杜聿明与宋希濂 太令人心酸了 抗日名将宋希濂文革时替杜聿明捱耳光!
“文革”期间,他们哪里都不敢去,躲在家里也许是唯一的办法。
宋希濂这样做了。可是,自从居民委员会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这个办法就失效了。那天,宋希濂与杜聿明合住的四合院里突然闯进来几个“造反派”,其中一人张口就问:“谁是杜聿明?”杜聿明正在院里干木匠活,替宋希濂做一个床头柜。床头柜的式样是宋希濂设计的,他手拿图纸,告诉着杜聿明下料的尺寸。
杜聿明听见有人问话,立即放下锯子,摘掉眼镜:“你们找杜聿明吗?我就是!”“造反派”们打量着对方的汗衫、围腰以及卷起来的裤腿,异口同声道:“你不是,你哪像国民党头等战犯,你是给杜聿明打家具的。”
“造反派”们转向身旁白衬衣、蓝裤子、黑皮鞋的宋希濂,其中一人说:“看来你就是杜聿明了。”宋希濂来不及答话,就被人左右开弓狠狠抽了两耳光。杜聿明箭步上前:“我是杜聿明,你们凭什么打他?”“你这个臭木匠,胆敢包庇大战犯!”“造反派”边骂边踢了杜聿明一脚。
宋希濂见状不妙,立马又站到杜聿明前头:“你们要打就打我吧,我是杜聿明。”“造反派”们围住宋希濂,个个摩拳擦掌,正欲大打出手之时,院外进来几位民警,好说歹说总算把“造反派”们请出去了。
文强写诗
文强
翘望盈盈得,天风浩荡来。
都中多喜事,笑看雪里梅。
这是文强发表在功德林墙报《新生园地》的第一首诗。有了第一首便有第二首,有了第二首便有第三首,几年下来,当他望着自己1000多首诗稿,心里就复萌了一个从学生时代便开始的追求:出本诗集。诗集通常前面有个小序,文强早早地写在这里:“近年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心之所想,一一记之于诗,其中绝大部分曾投稿于墙报《新生园地》发表,以当做我加速改造以来之诗思录亦无不可。我的诗稿欲待新生之日加以整理,以之留做重新做人的纪念。且定名此稿为《新生诗草》,兹作小序冠之于首。”
徐远举因为秉性强悍,言语尖刻,常与别人发生口角之争。那日回到舍房,文强送他一首诗:
人爱种瓜甜,汝爱种辣椒。
南人多思舟,北人多思马。
徐远举是湖北人,自然懂得文强在开导他,要他与人为善,同舟共济,不要立马横刀,打打杀杀。不过,徐远举仍有不解:“有话直说好了,何必煞费苦心,凑成五言四句呢?”沈醉拍拍徐远举的肩头:“这,你就不懂了,愤怒出诗人呀!”
郑庭笈领工资
郑庭笈
“文革”期间,文史专员们的工资突然被减少了一半,在那个年代,谁也不敢问问是怎么回事。
一天,郑庭笈在全国政协会计室领工资,出乎他意料的是,会计说接到上级通知,文史专员的薪水恢复为每月100元,至于前几月扣去的钱是否补发,还要等待上级进一步的通知。
郑庭笈慌忙摇摇手,马上表示说,已经扣去的就不必补发了,即使上级通知补发,我们也不会要的。
郑庭笈之所以自称“我们”,那是因为政协大院里出现了贴在墙头的大字报,有一张把文史专员称作“只拿钱不干活的牛鬼蛇神”,因而,他们把领工资当成一个包袱,一块心病,往往在通向会计室的青石板路上,低头疾走,可是仍然听得见一路上的叫骂。于是,他们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由一人代领。这个人自然不是固定的,而是按姓氏笔画为序,轮流坐庄。
轮到郑庭笈的时候,他采用了过去战场上经常使用的迂回战术,即从政协大院的后门进入(那里人虽少,但也有人怒目而视),这样就不先走向会计室,而是拐弯朝西走进男厕所,在那里操起笤帚,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一路扫出来,扫到会计室门口,才放下笤帚去领工资。
沈醉当三哥
沈醉
沈醉和小女儿沈美娟曾到香港,看望早已嫁作他人妇的前妻,在他的《我这三十年》里,这样记叙了当时的情景:
当他们夫妇出现在我住的宾馆门前时,我赶紧走上前去,紧紧地一手握住一人的手,把他们拉了进来。小女儿把房门关上后,我轻声对前妻说:“我很抱歉!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使你吃苦了!我更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孩子们都是由你们抚养成人。今天,我是特地来香港向你们道谢的!”她听后,也许是感到有点儿意外:“你既能原谅我,那我们以后就做朋友好吧!”我说:“不,不是做朋友,我们两家原是一家人,你是我妹妹,他是我弟弟,你们今后都叫我三哥吧!”这时,小女儿的继父拿着厚厚的红包走到我面前:“三哥这次远道而来,我们应当对三哥敬奉一点儿……”没有等他说完,我便插上一句:“我绝不是为钱而来,此行的目的,只是看看你们和孩子,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不知为什么,沈醉的记叙并不完整。据沈美娟回忆,他讲完最后这句话时,赢得了全场掌声,而最先鼓掌的,便是朋友事先安排在沈醉身后的两个年轻人。
一直等候在宾馆过道上的资深报人朋友听见掌声,忍不住拼命敲门,箭步而入,走到沈醉跟前时,竟并拢双腿,给沈醉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沈将军,你变了,分别三十年,我第一次看见你变了!”资深报人朋友又走到两个年轻人面前,禁不住喃喃自语道:“想得到的事情没有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才是新闻,一条轰动香港的新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