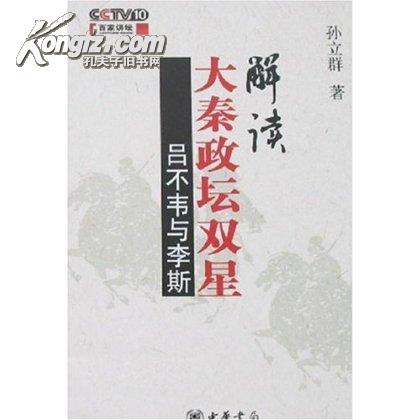孙立群讲李斯 孙立群《百家讲坛》讲李斯
我对李斯的感受,应该和N多人都不一样。不为别的,我写这位仁兄写了一年多,而且还在继续写,没有激情也有了感情,呵呵。听说百家讲坛也在讲李斯,一开始,没看,不想被别人影响了自己的思路。但是,也有热心网友不断提起,说有孙立群教授在电视高头讲李斯,问我看了没,有什么想法,觉得讲得如何什么的。
Anyway ,后来还是在网上找了孙先生讲座的视频,看了孙先生的前两讲——从政之路和力谏逐客,发现自己的担心其实多余。
孙先生的讲座,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影响我的思路。反而,我认为,我应该“影响”一下孙先生的思路才对。
李斯应该怎么写,我大概是知道的。
李斯应该怎么讲,我并不知道,但是至少,孙先生所讲,并不能让我满意。
在孙先生的前两讲中(以下所有的议论,也只针对这两讲而发,因为我也只看过这两讲),有几点讲法,我以为有欠妥当:
①关于秦国的逐客令,到底驱逐的是哪些人?孙先生的说法是“驱逐客卿”。由于这个错误犯得太过于离谱,相信当是孙先生口误。按:客卿不可和外客混为一谈。据通鉴胡注:“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诸侯来者,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
”我们也知道,秦国对爵位的授予是十分“吝啬”的,往往是非有战功者不能得之。客卿其位为卿,在秦国二十等爵位制中,大致在第十一级右庶长和第十八级大庶长之间,乃是极高级之爵位,自然更加不会随便轻授与人。
从历史纪录可知,秦为客卿者,多能擢升为丞相。如秦惠王以张仪为客卿,后至相位。范雎、蔡泽也都是先为客卿,后任丞相。客卿之位的显赫和重要,由此更可见得一斑。而关于逐客,史记明文记载:“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 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
’”可见,逐客令所要驱逐的,乃是“诸侯人来事秦者”,即秦国的一切外来务工人员,包括但不仅限于客卿。再说了,诸侯人来事秦者,成千上万,岂能尽数被秦国奉为客卿?如果真有这等好事,在下第一个报名,申请到秦国去混
②关于秦国为什么要颁布逐客令,孙先生将郑国间谍案列为唯一诱因,这样的分析未免照本宣科、流于表面。逐客令作为当时一极重大之事件,绝非只因为郑国间谍案这么单纯,而是牵涉到秦国内部的权力博弈、政治集团之间的角力斗争。秦国宗室大臣(乃至包括嬴政本人在内)对身为外客的吕不韦(前此尚有嫪毐)专擅朝政早已心存排斥,郑国间谍案只不过刚好给了他们一个发飙的借口而已。
③孙先生对于“帝王之术”的理解,似也不妥。
(按:“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孙先生将帝王之术从字面上解释为:君主如何统治天下的方法。然后又设问,“李斯你不是君主,你学帝王之术干什么?”此问可谓必然。再自答道,“用来游说,向各国君王献计献策。
”这一答,却便没能答圆,有些牵强。在我看来,帝王之术中的帝王二字,乃是动词,却又与“鲁仲连义不帝秦”的用法有所区别。帝王二字,当作“使somebody帝、使somebody王”解。帝王之术,即辅佐别人成为帝王的术,即kingmaker之术。
只有如此理解,才能解答这一问题——“李斯你不是君主,你学帝王之术干什么?”。答曰:陶弘景有言,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齐桓霸也。古罗马贺拉斯有诗:若夫砥砺,己不能割断,而能磨刀使利。萧伯纳亦云,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s。帝王之术,殆同此类。
④孙先生引了《盐铁论
毁学篇》中的一段话:“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借以说明荀子见李斯贪慕功名利禄,从而为其忧心。然而,这段话却不该引、不能引,更不可拿来作为论据。因为其所指之事显属伪造,大抵是后人附会,借李斯来说事而已。
按:李斯为秦相,约在前213年(赢政三十四年)。考荀子生卒,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约为前340-前245年。据胡适《中国哲学史》,荀子生卒约为前315-前230年。
不管采纳哪种说法,至少都可以确认,李斯作秦相时,荀子已经物故多年,自然不可能“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而在这两本书中,钱穆和胡适也都提到了盐铁论中的这段话,皆加以驳斥,以为谬误。而如果按照孙先生节目中的说法,将荀子的生年定在约前313年,则当李斯为秦相时,如果荀子还健在的话,也当有一百零一岁高龄。
如此高寿的几率当然还是有的,但应该不会太大。PS:网友也可查百度百科,可得结果:荀子(前313年?-前238年)。
⑤关于长史一职。
孙先生的意思大致是说,长史是为李斯特设的,以前没这官。而考《汉书
百官公卿表》可知,在秦国,有好几种官都同样地被称为长史。譬如丞相的属官中有被称为长史的,国尉和御史大夫的属官中也有被称为长史的,前后左右将军其下也置有长史之官。而我的推测是,当时李斯所封的长史应为国尉属官。
⑥关于李斯见嬴政,孙先生的说法是,吕不韦带着李斯见到了嬴政。
我不知道这一说法的出处,也许是孙先生别有发现也未可知,姑且存疑。按: 《史记
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依我推测,李斯能够接近嬴政,主要还是利用了自己作郎官的便利,不会是由吕不韦把他领到嬴政眼跟前,为两人撮合一段君臣因缘。
再言之,如果吕不韦真要引见李斯给嬴政,大可在李斯作舍人时便引见,何必非要等到李斯任郎官之后呢?况且,吕不韦如果真把李斯带到嬴政面前,他该怎么对嬴政说?难道说,这是我马仔,你多照顾?而嬴政正猜忌着吕不韦,又哪里还敢重用由吕不韦亲自打招呼介绍来的李斯?
说到给别人挑错,这活其实没什么太大意思,而且说多了还会讨人厌。
况且,以上我所列举出的几点,也未必尽是我对。即便尽是我对,其实也无伤大雅,并不影响孙先生讲座之优秀。
然而,孙先生在讲座中所持的另外两个观点,却是不得不驳,不可不驳。
而这,也正是我写作本文的真正初衷。
套用姚蜜姚黑的说法,孙先生可谓是一个标准的“李黒”,对李斯极端不愤,笔伐之虽未曾见,口诛之却为所亲闻。孙先生的李黒身份,通过他对韩非之死以及李斯叹鼠这两个事件的误读,可以轻易得到确认。
钱钟书先生在评论《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时,曾提出一个独到的观点:一部好的集释,当能满足两个标准——应有尽有、应无尽无。
这两个标准,其实也可以适用于为广大电视前的观众朋友负责的百家讲坛。
然而,这两个标准,孙先生却都有违背。
首先,孙先生没有做到应有尽有。这直接导致了他对韩非之死的曲解。
按孙先生的说法,李斯是害死韩非的元凶。李斯对韩非始乱之,终弃之。先将韩非拉来秦国,来了突然又开始妒嫉人家,妒嫉完了,又在嬴政面前打韩非的小报告,导致韩非被监禁入狱。韩非都进监狱了,李斯这厮还不甘心,又用毒药毒死之(这些当然不是孙先生的原话,此处但取其大意)。从而,孙先生借韩非之死,评价李斯为:暴露了他的劣根性,反映了其心理污浊。
历史真是如此言说的吗?
事实上,不管有意无意,对韩非之死的相关史料,孙先生选择性地对大家进行了“隐瞒”。
我们知道,在《史记》中,对于韩非之死,于《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和《韩世家》中都有简要提及。至于韩非的死因,则只见于《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
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孙先生的说法,便是来自于此一记载。然而,奇怪的是,在孙先生的讲座里,却将韩非之死的“功劳”全记在李斯头上,却对另外一个人——姚贾只字不提。
而在另外一部史籍《战国策》里,对韩非之死却另有一说法。概要言之:韩非之死,压根没李斯什么事,全是姚贾一力促成的(注1)。《战国策》里的相关史料,孙先生不可能没有看过。可是,他依然对姚贾辉煌的存在视若无睹,一门心思只认定凶手就是李斯。
比较《史记》和《战国策》对韩非之死的记载,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从史料互证的角度说,正因为这差异的存在,也就更强化了其相同点的可信性。韩非之死,李斯只出现一次,而姚贾二次全都在场,岂能轻易忽略、随便弃置不顾?(注2)
要知道,姚贾并非无名小辈。“(姚贾)绝其(四国)谋,止其(四国)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姚贾)封千户,以为上卿。”可见,姚贾也是当时左右国际局势、有大功于秦的厉害人物。然而,姚贾再厉害,却也架不住孙先生的大变活人(准确的说,应该是大变死人),一下便给变得无影无踪了。
韩非之死,疑点甚多,向无定论。限于篇幅,在此不能详细阐述。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根据现有史料,李斯只能被称为害死韩非的“嫌疑人”,并没有确凿证据可以定他的罪。换而言之,韩非之死,未必就该李斯负责。即便李斯真有干系,那更多的还是出于和韩非的政见不合,没必要硬扯上小人不小人什么的。
然而,孙先生在没有将所有证据呈堂的情况下,便当着众多观众的面,将李斯同学宣判为害死韩非的罪魁祸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古训云:君子于物无所苟,而况于人乎?
其次,孙先生没有做到应无尽无。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李斯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性格的主观强加和臆测。
第一讲刚开始,孙先生便引用了李贽《史纲评要·后秦记》中的一句话:“是圣是魔,未可轻易评说。”这句话我所见的版本是“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拆,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考其大意,还是以论始皇为主,李斯为辅。不过拿这话来说李斯“未可轻议”也算合适。但是,让人费解的是,孙先生既然引了这句话,却又明知故犯,开始轻易评说李斯起来。既轻议之,又复苛论之。
孙先生对李斯的感叹,从李斯对老鼠的感叹开始。李斯叹鼠,见于《史记
李斯列传》一开篇,自然少不了要讲,但讲到什么程度,就不得不慎重了。
我们先来看《史记》原文: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的这句感叹,到底应该如何解读呢?孙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李斯悟出了一套老鼠哲学,有出息的人就应该过舒坦的日子,做高官。要像仓鼠那样过上好日子。这表现了李斯在道德层面的缺失,将高官厚禄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当然,孙先生也从反传统的角度解读了李斯的这番感叹,对此我个人是十分欣赏和佩服的。
老实说,我不知道孙先生是如何推导出上述答案来的(想想著名的奥卡姆剃刀)。至少我是推导不出。从上述答案倒推回去,李斯当时的感叹应该是“人之富贵卑贱,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才对。人李斯分明说的是“人之贤不肖”!就算我们相信李斯口不择言,却也不应怀疑司马迁在用词上的考量斟酌。曲解两三字,足以谬千里。况且,平心而论,李斯一生的成就和高度,也绝不是一个幼稚地想作仓鼠的人可以达到的。
李斯叹鼠,是李斯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唱京戏的,最讲究个“碰头彩”。亮相亮砸了,后面的戏也一准讨不了好。为什么?观众习惯了先入为主。所以说,如果从一开始,就对李斯叹鼠做出了错误的解读,替他下了人品道德低劣的鉴定,试问,戴上了这样的有色眼镜之后,接下来再来审视李斯日后的所作所为,无异于疑邻窃斧(注3),又怎能做到客观公正?李斯见义勇为了,丫狡诈,欺世盗名呢。
李斯给希望工程捐款了,丫虚伪,道德有问题。李斯扶老太太过马路了,丫小人,那老太太是嬴政他妈。
有劲吗?至于吗?
再退一万万步来说,即使对李斯叹鼠,真可以解释为李斯利欲熏心,向往仓鼠。那又如何?李斯当时只是一个生活在小地方的小青年,眼界又低,见识也浅,就不许人家的思想随着际遇和阅历的改变而改变?年少时的想法,难道就是摩西十诫,不可能被更改?
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时的宏愿不过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孟德公《让县自明本志令》云:“ 孤始举孝廉,年少……欲为一郡守……后征为都尉……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孔子的夫子自道更是人所共知: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黄庭坚书风数易,及名家之后,见前作辄欲毁去。木谷实当年行棋,天马行空,力争中腹,晚年却多在低位爬活。陈世美抛弃发妻,武则天频换面首……人生一世,际遇叵测,惟因时而动,岂有不变之理?
孙先生说,司马迁把李斯给看透了。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把人看透,不等于说把人看死。
对于李斯叹鼠,作孙先生那般解读的人,历代多有。究其原因,想来只是后人在读完李斯的一生之后,以事后诸葛亮自居,强加给李斯的。
由此生发开去,再来谈谈李斯的评价问题。鲁迅先生曾说过:“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
很不幸,李斯就是秦朝人。李斯晚节不保,加以秦二世而亡,对他的评价,不免掺杂了大量水份,而且多是被泼的脏水。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在《史记
李斯列传》里,有一段司马迁自己的说话,即太史公曰。其中有一句,当引起注意:“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对于李斯,当时除了司马迁的意见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意见,即俗议。什么是俗议?大致可以理解为一般人都这么以为。也就是说,当时的一般人还是倾向于认为,李斯极忠而被五刑死。
佐证这一意见的史料已然散阙,但至少还可以找到两条。《史记
萧相国世家》载:上(即刘邦)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史记
鲁仲连邹阳列传》载:邹阳狱中上书云:“昔卞和献宝,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以上两条,同见于《汉书》)。
在这两条史料中,李斯的形象堪称正面。同时也由此可见,李斯评价的走低,是在司马迁史记出世之后。
然而,要公允地评价李斯,最主要的史料还是史记,逃不过去。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史记是怎样的一部书,司马迁又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部书。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并非一部官修史,而是和孔子的《春秋》一样,是一部私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其谓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这样写到自己的创作缘起:“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可见,司马迁是要向周公和孔子看齐的。其创作史记,带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寄托了无限的深情厚意,在在见于其《报任少卿书》之字里行间。
论史料价值,《春秋》不如《左传》远甚,却能千古推崇,何也?为其有义法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也引用董仲舒的话赞赏《春秋》道,“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司马迁写史记,率以孔子和他的《春秋》为榜样。而他对孔子和《春秋》的评价,也可视为他对史记的自期。
以上虽然扯远了,却在于要说明一点:司马迁只有丹青手,却并无照相术。其著史记,自有其义法——即主观判断和价值标准。读史记之李斯,不可不思此节。
刘静修《读史评》诗云:“纪录纷纭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北齐魏收著《魏书》时,曾自傲道:“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史家的猫腻,由此可见一斑。司马迁纵是千古公认的良史之才,远非下作魏收可比,然终为有义法在,其书也未可尽信(更何况,史记本身也存在被窜改的问题)。
随举史记两例:如:赵高和李斯谋立二世,本该是不入二耳的秘密谈话,司马迁如何能知,并一字不差地予以纪录?想来,也大抵是司马迁根据事件的前因后果揣度而出。再如:“司马相如……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 文君之窃、之心悦、之恐不得当,皆隐匿于闺房与心房之中,司马迁又如何洞晓?想来,盖也揣摩而已。
这也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司马迁不光是第一流的史学家,同时也是第一流的文学家。回到李斯列传,李斯年少时发生的事情当有许多,司马迁为何独取叹鼠一节呢?殊不知,以点概面,以小见大,正是司马迁的惯用绝技。这一绝技,在陈涉世家、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等卷中,我们都可领教得到。寥寥数笔,斯人形神已现。作为文学而言,自是无上妙品。作为史料而言,却终究有恨少之憾。
那么,到底该应该如何评价李斯呢?我也无多话可说,只说一句:“李黒”的话,不能听,至少不能尽听。
注1:见《战国策 秦策五 四国为一将以攻秦》
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曰:「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屈于内,而百姓靡于外,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带]以其剑。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
韩非(知)[短]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
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厉群臣也。」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之]。」王曰:「有何面目复见寡人?」对曰:「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
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桀听谗而诛其良将,纣闻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
王曰:「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雠]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
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于]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卞随、务光、申屠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
注2:此一段话引自:《重释韩非 一个功利主义时代思想家的死亡》,有些微调整。
注3:疑邻窃斧,见于《吕氏春秋·去宥》和《列子·说符》:人有忘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俄而,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