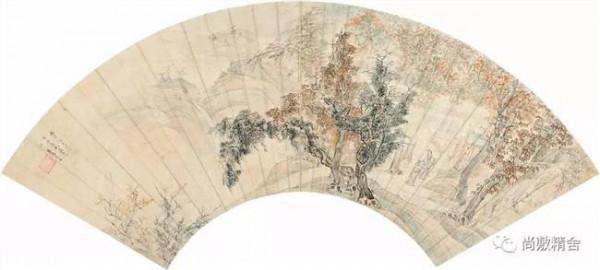许章润爱思想 许章润:中国如何炼成“软实力”——回看三十年思想线索
19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伊始,对于十年“文革”政治遗产的清算及其意识形态的清理,逐步引导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其产生原因上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难辞其咎。究其内里,其实是正面清算和清理受阻,于是演变为侧翼挺进,文化出面代政治受过,历史为当下担责,道出的是“五四”以来老故事的新版本。
经此推导,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关于东西文化的大规模论战,引发了一场涉及各个学科的思想讨论和文化反思运动。当其时,激烈反传统主义和讴歌“蓝色文明”的全面西化论重新登台,作为二者的反动,新一波传统文化复兴热潮与新权威主义上场。其情其形,一如上世纪初年的文化论战,将中国文明灵魂分裂的尴尬与精神自强的活力,再度呈现于中国大地,并于1980年代末走到僵局。
1990年代初期,以对于人文精神的探讨,重启思想进程。于是,中国文化思想图景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翩然登场,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等等亦喧哗上台。牵连跌宕中,中国文化本位的中道立场,似乎于竭力吸取和协调各种文化资源的努力中逐渐成为多数心智的思考重心。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市场强化威权,威权推动市场”的市场共产主义进程的不可逆转,文化讨论和文化心智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凡此种种,构成了1990年代中后期以还迄而至今的中国文化场景。
悲情淡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在融合
市场化30年使中国财富获得了极大增长,综合国力和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亦有较大提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学术精英不仅是改革的参与者,而且是改革红利不同程度的分享者。“事事不如人”这一鸦片战争之后一直缠绕着中国人的梦魇,至此遁入暗夜。
晚近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多所恢复,文化悲情意识逐步淡化,过去常常引发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1840情结”,不再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愤青式的激烈反传统思潮同样渐失话语主导能力,极端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已成为边缘。一些新儒学论者倡言原教旨主义式的“王道”,扭曲为一种新兴都市化的思想时尚,酝酿出民间“传统文化热”。
正是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记忆渐渐复苏。如果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立这一架构分析,最近十多年来出现的一个好现象便是,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融合进程和互动程度空前强化。比如,在大传统转化为小传统方面,知识界对于人权的倡导和法治的宣谕,藉由现代传媒,使普通百姓的权利意识随着市场化进程一同成长,民间维权运动如星火燎原,正在成为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改良与社会进步的杠杆,反过来促进了大传统的成长。
普通百姓依法维权正成为每天都在上演的活剧。
北京老汉面对“强制拆迁”的推土机,将宪法捧于胸口,以一己之身相抗,蔚为象征,感天动地,是几千年没有的事。就小传统转化为大传统方面来看,中秋、清明得列为全国假日,文化记忆获得了自己的法权安排,政治治理意识到,必须具有文化合法性方才秉具正当性,并且愿意皈依于此文化合法性,实在是一种良性发展。
凡此表明,至少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严重对立与隔离状态,正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的进步而获得逐步弥合,二者互动融洽、流转不息之际,就是中国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从而获秉真正软实力的时候。
政治成熟:民主期待“软着陆”
就此而言,晚近十年来,“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正在且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心智亟需深入考量、切身历练的问题。文化自觉不仅表明对固有文明优秀传统的体认、传承和归依,并在此基础上善予创造性阐释,含弘光大,同时表现为对于自家文化身份在世界文明图景中的自我肯定,也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人与思想者对于提澌中国文明境界的期待和担当。
讲到政治成熟,则于秉持普世价值的同时恪守文化身份,拥抱政治理想之际对于人性永怀怵惕,坚守公民理想与捍卫民族理想的统一等等,均为其中应有之义,也是三十年来,特别是晚近十多年来,中国心智逐步意识到并且局部性渐达此境的思想、政治善果。
就此而言,中国不仅需要成熟的而非愤青式的民族主义,也同时需要成熟的而非愤青式的自由主义。后者基于转型期的焦虑,激于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诉诸自由主义理念,而内里则多民粹主义冲动,如同新左派的道义批判,反映的是“胃的造反”,其极端形态其实极易滑向暴民政治,与“爱国贼”式的民族主义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也正是在此,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展示和演绎着文化对于政治的塑造作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和威权主义这几脉理路,同时孕育与活跃于当今中国,分别对应着中国的不同政治社会问题,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决方案,反映了究竟是自由优先、平等优先还是秩序优先的价值选择与进路安排。
在此,尽管致思方向有别,背后的理念悬殊,但是,通过吸取传统政道和西方民主理念来塑造当代中国的政治德性,经由宪政安排来体现政治的德性,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明的复兴,是晚近十多年来汉语政法学说的劳心劳力所在,并且日益成为此间从业者的共同自觉。
比如,从古典天命天道命题来深溯政治合法性的中国文化资源,并与自然法理念和代议民主学说相互发明,体现的便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一种政治成熟,以及基于现实政治批判主义的高度精神独立。
如同经济软着陆一样,在当今中国,民主也需要软着陆。事实上,这已成为知识思想界的主流共识。三十年来形形色色的学理与思想之积劳集慧,正在并且必将促成这一“软着陆”。
不要低俗化,不要“打棍子”
三十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特别是随着政治从神坛走向凡俗,中国社会和文化再度进入持续的世俗化过程。此种过程也就是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的“除魅”历史,始自帝制崩塌,中经“造神运动”一度中断,而于1980年代初期接续之。
此番世俗化进程不来则已,一来就横扫天下。首先,一般性的“文化研究”,特别是人文意义上的纯粹学术研究,日渐边缘化。同时,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直接以社会现实为对象,注重效率、公平与发展的学科,则获得了长足发展。
实用化成为这个时代的学术指向与理论用力之处,“有用性”兑换为研究心智的优先性,犹有过之者,对于传统和经典的研究,与实用化相伴的是低俗化。比如顶级大学的哲学系举办“总裁《论语》班”或者“老板国学班”。
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文化立场或者掺杂着文化立场因素,文化立场再换形为理论取向与理论立场,进而可能演绎为政治正确,最终难免导致意识形态化。事实上,近些年对于诸多学术论题的讨论都曾不同程度地发生过此类现象。
例如,针对颁行《物权法》异议者的理论逻辑,驳论者一方面呼吁去意识形态化,莫以法权安排担承政治考量,另一方面,最后却又以“反对《物权法》就是反对改革开放”逼视对方,实际上属于一种再意识形态化,反倒暴露了自己思想内涵的贫瘠。
而将理论立场的“左”冠以“新左派”,隐约间暗喻着其与“文革”极权“左倾”间的联系,同样背离了思想论战的常道,一如反唇相讥,指控自由主义的普世学思为“卖国”之荒谬。凡此种种,说明中国学术和思想尚未达臻真正的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有待于在今后的砥砺中渐归学术常道。
应逐步迈入“中国之世界”
三十年与世界的双向互动,缴纳了昂贵学费。中国知识思想界的文明视野得到了极大拓展,逐步体认到这个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学会了在世界体系中思考中国问题,进而有可能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艰难历程中,向世界贡献普世性的生存经验。
正是在此,国家利益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念获得了同步增长,文化本位立场与世界人类情怀交相辉映,“体”“用”之争不再有什么意义。中国的知识思想界认识到,不仅一部人类文明史是复调性的多元文化成长过程,绝非一元线性“进步史”,基于“胜王败寇”的历史还原论与天真而认真的西方文明绝对优胜观,不再享有绝对真理般的文化解释力;而且,人类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互竞、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维场景,仅以西方文明的世界观衡估这个复杂多元的人类大家园,一如仅仅以中西文明的对比甚至对决来解释中国现象,既是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死胡同,现实政治层面上也是行不通的。
借用百年前的一个表述,不妨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世界体系属于“中国之中国”。经由二十多年的发展,进入了“世界之中国”之境。晚近几年开始,中国实力增强,中国心智开始走向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话语权有所增强,而逐步迈入了“中国之世界”的过程。
因此,晚近十多年来,伴随着文化自信的渐渐恢复与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的良性发展,包括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比较文化在内的知识探讨与思想阐释,不约而同地开始注重中国百年变革这一“地方知识”所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其实,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描述,也是借径“中国个案”的分析,提炼某种普遍理论形态的基础作业与组成部分。
如何重新阐释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过程和中国文明面对世界之际,不仅会遭遇文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的分立与分离问题,而且还会不断出现诸如大传统与小传统、心灵与实践、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背逆等等中国式难题。换言之,文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浮现于当今中国的问题视域,逼迫着我们必须做出当下中国的回应。
其一,对于传统“天下观”予以现代重构性阐释,以天下观念的博大与包容,吸纳一切人类文明,重塑世界格局。以晚近中国一百多年所积累的生存经验为背景来重构世界格局的努力,既是对“天下观”的拓展,可能也是向美美与共的人类家园理想提供中国文化启示的用力处。
其二,对于“中国形象”的文化合法性阐释与“文化中国”图景的建构。对于“中国”意涵的不断阐释,也是对中国之为一种人间秩序和人世生活的应然之维的绵绵不绝的开拓、提升和丰富的过程。由此造成的历史与道义、知识与思想、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心的廓然意象,一以仁爱宽和、厚道中庸、博大中正和进取向上为依归,文质彬彬,坚毅刚卓,此其为中华也。
这是“中国形象”文化合法性的必要内涵,更是面临全球化时代,文化与制度竞争形势下,中国知识思想界应予传承接续的未尽伟业。
其三,建构中国文明的超越本体,提高中国文明的精神层次。在此,需要挖掘中国文明的人文主义心性资源及其超越禀性,包括“以德抗位”的道德主体性,仁爱礼智信的价值信念和精神追求,形成中国的自然法理论体系,剥夺世俗权力天然合法性的独断论述,形成“有法有天”的人间秩序,提炼超越意义的汉语学思。
由于超越本体的重构性阐释必然牵扯到信仰世界及其自由选择的问题,因此,需要重申的是,信仰自由是每一个体提升自己精神独立性的必由之路,也是造就公民和政治的前提,任何公共权力不应介入,也无法介入。
信守信仰自由,既是世俗权力恪守本分,对于精神尊严的应有承诺,也是建构中国文明超越本体的制度前提,有待努力者既烦且重。若说所谓“主流价值”,则皈依处在此。
其四,对于中国伦理智慧、道德理想的发掘和道义力量的涵养。大凡引领世界人类方向的国族,多半具有自己的浩然道德理想与铮铮道德担当,秉有深厚的伦理智慧,而提炼出普世的价值理念。平等、自由和博爱理念,既是政治理想,也是道德理想,两三百年来一直是响遏行云、鼓荡人心的最为美好的道德号令,一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千年心声,具有永恒的感召力。
秉持如此道德情怀的国家,才是受人尊重的泱泱国度。中国在经济发展、国力大增之际,亟需涵养和发育的正是此种道德理想与伦理智慧。
其五,族群政治、公民团结与分享的公共空间,是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过去、此刻和未来无法回避,并且愈发严峻的现实问题,考验着中国文明,需要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成熟。
一句话,中华文化的“复兴”,特别是软实力部分,尚需知识思想界的重构性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