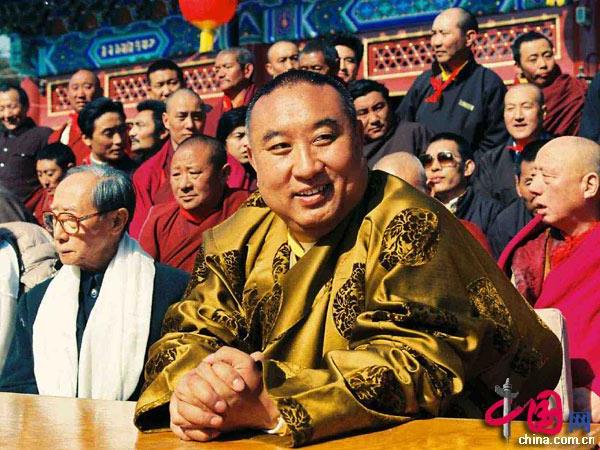余世存是谁 余世存:家世本是教化之源
当初被一家内刊杂志的主编约写专栏时,余世存想也没想,就说写家世。
余世存曾经有个愿想,希望能像司马迁把孔子等人生的失败者、失意者列入“世家”那般,把当代人的风范写出来,为当代人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秩序。
他开始梳理百年来的中国家族。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十二家。开始有朋友提议,可以把这些个案拼成一个专题做出来;也有人说,在中国,像他所写的宋耀如、卢作孚、梁漱溟的名门望族毕竟是凤毛麟角,且与普通人关联不大,“还是写身边的人或朋友的故事比较好”。
重新拾起这个系列时,余世存决定“放开来写”。他写了蒋家,也写了老外罗斯柴尔德;写了朋友蔡文彬、杨志鹏,还写了自己的家世。
在他看来,家世本是教化之源,只要我们听闻,就能看见自己的位置和面貌。
如果说透过这些名流的个案,余世存感触颇深的是“对世界的敬畏和开放”的重要性,那么对普通家族的成员以及自己的人生经历做一个梳理,他觉着本身即是一种提升,是对自己生活的加持。余世存说,希望后者能引起读者对自家探索、回顾的兴趣,“从目前的反应来看,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
余世存,诗人,学者。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出版有《非常道》、《非常道Ⅱ》、《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等。
知识界和社会存在某种脱节
南方日报:这本《家世》中的文章你最开始是以专栏的形式呈现的,当时没有集成书的想法吧?
余世存:当时是给杂志写专栏,而我本身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就这么写下来了。要现在的话就不该这么写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出专栏结集的书,而是出专题类的。
南方日报:为什么这么说?
余世存:这要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说起。多年前,我同《南风窗》编辑部主任陈初越聊过,中国市场化这么多年,在文化上的表现不是很如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但更加滞后的是,没有培养出知名优秀的图书作家。
图书作家与学院派知识分子是有差别的。这些年很多学院派知识分子在转换角色,在给报纸、杂志写作,但思路没转换过来,还是在向社会灌输学院的观念,没有从社会本身的角度与读者分享观点。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知识分子对社会是欠债的,应该把学院思考和书斋里的思考做一种转化。
说得难听一点,很多知识分子写文章像在做作业,自己没去消化一遍。我们目前就面临这么一种转折,有这种动力的人又太少了。比较之下,《家世》关注的是社会话题,不是知识分子话题。
南方日报:这也是这本书的独特性所在吗?毕竟之前关于家族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余世存:是的。但我这代也好,50后知识分子也好,很少人做这种工作,觉得看不上,跌份儿。其实问题涉及到知识界和社会的某种脱节,没有换位思考。就像阿城在美国遇到一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对方问:“大陆人民生活怎样?”阿城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人民”。
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是把自己摘出人民之外,摘出公众之外的,所以他的写作不是通俗的、公共知识的写作。我们所谓的公知,知识分子气还是太重,所涉及话题还是知识分子内部的话题。
《家世》面世后很多人感兴趣,因为它呼应了社会的需要。无论电视剧《老有所依》的热播,还是《爸爸去哪儿》电视栏目的火爆,说明社会对代际关系、宗亲伦理和家庭教育是有需求的。无论我这本书还是之前的几本书,能够走出知识界之外,是因为我意识到中国需要进入这个阶段,但现在成绩太小了。
南方日报:《家世》序言里提到,当我们“回家”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是否解答了“人类情感和认知的急迫性”。对于这个问题你自己有答案吗?
余世存:我们中国人和古典中国人的差别,远大于跟现代西方人的差别。我们其实都是现代文明下的亚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种群而已。但现代文化是“在路上”的文化,至少目前没能看到能安顿我们灵魂的东西出现。所以在人类的情感上,和认知我们处于哪个位置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多人来投入做这项研究和分析。
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知识人思考太少,还是美国的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走得比较远,想得比较多一点。我们给大众提供的答案远远不够,包括通俗写作仍然停留在戏说的阶段。
自我整理是必要的自我教育途径
南方日报:《家世》中的十七个家族,你最开始写的是哪家?
余世存:是林同济家族。林家人在从传统家族向现代家族转化的意识很早,而且意识很到位。
南方日报:林家也是你最欣赏的一个。
余世存:对。在一二百年前,林家人就提出培养专业人才,要有专业精神。这是我认为中国社会很欠缺的。我们太容易跨界,本业都没有夯实就跨界。无论是知识分子的参与,时政评论的参与,还是对社会热点的研究,实证精神是不够的。
南方日报:书中你特地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并借用罗素的话指出了经济世袭的现象。你认为这种现象目前在中国也存在,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余世存:对。近些年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老百姓一直被灌输的理论是“经济人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整个社会拜金主义横行,人情关系冷漠。但西方经济学已经意识到这点,用了新词叫“慈善经济”、“社会企业家”,并认为学习是一种价值,慈善公益是一种价值,安全是一种价值。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社会的优先地位来考虑。
几年前,北京顺义有个中央别墅区的老板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些人富起来了,老百姓也富起来了,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彰显国力?我说肯定不是,按孔子的教导,就是要教育、要学习,互相学习。
南方日报:写完名门望族后,你“放开来写”了自己家以及几个普通家族。对此你强调说这等于是一种“自我整理”,为何对自我整理如何重视?
余世存:写的时候别人也说,我写的都是名门望族,中国名门望族毕竟太少,而且跟普通人没有太大关联,还是写一些身边的人或者朋友的故事比较好。
“自我整理”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自我教育的途径。像微信都快取代微博了,大家可学习的资料那么庞杂,真正能打动自己的还是亲人。若你去回顾整理,所收获的东西的品质要高得多。我在假期时给大学的年轻人讲过关于“自我整理”的课程,希望他们能回忆起童年的第一次疼痛感是怎么来的,自卑感、金钱意识是怎么来的,自己是怎么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的,男女性别的意识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你会发现你现在性格上的不够健康或是偏颇的东西,可能来自童年或少年时期某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必须勇敢面对它,才能超越和把握住它。我在讲课时觉得他们还是挺受触动的,有的人讲父母当年声嘶力竭地吵架,他讲着讲着就痛哭,但他讲完后觉得把这个放下来了。
回到你的家庭本身,去整理你的家人,本身就是很好的自我教育的机会。我觉得比看微信上的心灵鸡汤可能更贴己。
南方日报:总的来说,透过这一个个家族的个案,你想告诉读者什么?
余世存:我从这些个案中感受比较强烈的是,对世界的敬畏和开放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能把这两点身体力行地体现的话,肯定也能做出很多成绩。比如我写蒋家是希望对大家讲明,中国国民政府最高领袖除了注重传统的仁义道德、忠孝节义外,他还对世界保持了最大的开放。
两代之间的双向学习终会回归
南方日报:你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几代中国人都处于一种“离家出走的、叛逆”的状态。这样的局面是怎么造成的?
余世存:中国百年来总会对上一代人进行反叛,有各种原因,有文明大转型的原因,也有时代的病症或现代化的某些问题。我们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中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喜新厌旧,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赶时髦,而技术的升级又太快,技术面前永远是年轻人占优势。
年轻人总觉得上一代人老土,被PASS了。而老一代人在年轻人面前总是不自信,特别是50后,知青那一代,他们觉得自己没受什么教育,上一代人也没有传承给他们优良的家风家教。
甚至可以说,50后、60后这一代人是存在很多罪行的,很多人第一桶金说不明来路,不能轻易告知孩子是正义的。他做人也不踏实,在孩子面前起码从立身处世上就不自信,他们唯一能给孩子的就是钱,供孩子读书,让他们好好听老师的话,很少有人跟孩子坦诚交流。就像野夫所写,他父亲那代人跟孩子之间是封闭的,使得孩子在年轻的时候轻视上一代人,后来原谅了,但也没从上一代人中学到什么东西。
我们说中国目前是“失教”的。比如一些官员说的不近人情的话,网友会问:“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说明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因为家教缺失了。
南方日报:那是不是下一代人更应该反思,要多从上一代人中汲取正面的东西?
余世存:肯定的。我曾对一些80后说,不要看不起50后父母那一代人,即便看不起,他们的人生材料本身就有巨大价值,也是不应忽视的。你不能总说那些话是老生常谈,你没有从你父母那些人生事实中学到正面的东西,这是你们的问题。我认为以后肯定会有“回归”,两代人会坐下来坦率地交流,上一代人从下一代人这里也要学习些东西。
这也是我说的现代人的家教和传统家教不同的地方。传统家教方面靠的是农耕社会中的传统经验,靠圣贤书就可以把天下万事安顿好,所以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是天然的灌输者,觉得不需要从下一代人身上学习东西。现代社会不一样了,既要让孩子从自己身上学到东西,同时也要从孩子身上学到东西,这就变成了一种双向的学习。
南方日报:你也提到,今天我们又自愿自觉地把“出身论”、“身份论”招回来了,那你怎么看这种体现在“我爸是李刚”等话语上的宗亲文化的禁锢作用?
余世存:这涉及到中国文化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弟子问孔子如何去治理国家,让百姓生活好,孔子的回答是先发展民生,让社会繁荣起来,弟子继续问富起来怎么办,孔子说:“富而教之”,要教育他,培养他。你看北京、深圳郊区的农民富裕起来之后,“一塌糊涂”,就是没有实行教育,还有富二代、官二代也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