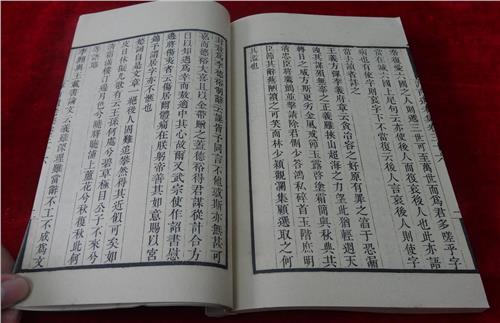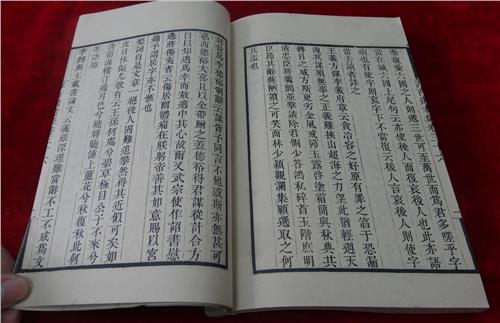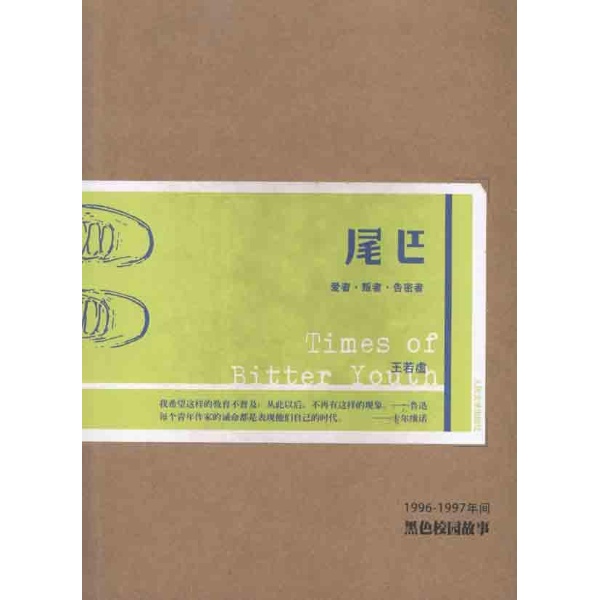王若虚的苏轼批评 论王若虚文学批评理论中理想境界的实现
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藁城(今河北藁城)人。金亡不仕,晚年自号滹南遗老,是金源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金承安二年(1197)中进士,《金史·文艺传》有传。王若虚在金元之际学术界独步一时,与元好问并称为金代文学批评领域的双璧。
作为金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经学家、史学家、文献学家,王若虚以学术精博、见解独到著称于世。他的文学批评理论,无论是宏观体系的力图建构,还是实际创作的具体指导,都对金末元初的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推重“文意”是王若虚文学理论最突出的特色,在王若虚看来,“文意”并非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在求“意”的目的下,很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文学应该在抒写作者真情性的基础之上,准确而真实地反映所要表达的事物,即“真”。
在 “真”的表现过程中,为了让这一切更加接近于事物本身,与读者趋于心灵的契合,又必须关注到为文之“理”与为文之“势”;诚然,文章先须求“意”,但仅如此,尚不足以达到文章的至高境界,惟有在备“意”之上,进一步实现“天全”、“自得”,兼融“妙理”,才算是真正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
诗文理论追求的理想境界,首先表现为“自得”。王若虚说:“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1](p477)又在《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予尝戏作四绝云》中再次提到:“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
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法嗣复何人?”他欣赏白居易为人“冲和静退,达理而知命,不为荣喜,不为穷忧,所谓‘无入而不自得’者。”[1](p524)苏轼说:“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谓之顺。
” [2](p193) “君子之顺,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2](p9)而晁补之谈到苏轼对他的教导时转述说:“吾以乐而未尝无以乐者,顺也。”[3]在苏轼看来,“无私顺理”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审美的态度,它伴随着“乐”,即审美的愉悦,而所谓“无往而不自得”者,就是自由,就是“性命自得”。
而这种“自得”自由精神境界,才真正是苏轼文章妙于天下的根本所在。《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曰:“东坡《南行唱和诗序》云:‘昔人之文,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
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充满勃郁而见于外,虽欲无有,其可得耶!故予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时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肯与江西诸子终身争句律哉!
”[1](p461)可见,王若虚对苏轼弱冠之年即有所表现的,主张文章自应出于天全、自然,而不能刻意为之的过人悟性与见解,已经表示出极大的欣赏。而“万事不我撄,一心常自得” [1](p556)则体现了王若虚在学习作文之外,对苏轼人格风范与人生境界的仰慕与追求。
由此可见,“自得”是走向文学理想境界的必备条件,但它只是登堂,尚未入室,“浑成”才是王若虚文学评论的理想境界,也是他为金源诗人指出的奋斗目标。其关于“浑成”的理论来自其舅周昂,《滹南遗老集·诗话(上)》引其语曰:“雕琢太甚,则伤其全。
经营过深,则失其本。”正是基于此因,王若虚批评黄庭坚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1](p463)
王若虚说:“物之在天下,皆妙理之所寓也。”[1](p495)他所说的“妙理”是充斥于天地之间,表现在万事万物上。他将这一哲学概念引入文学批评领域后,赋予其“为文之理” 高妙境界之涵义。王若虚推重苏轼之文、白居易之诗,评价二人作品皆富有“妙理”。
其论苏轼曰:“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1](p461)其论白居易曰:“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岂胜鞭。”[1](p552)又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肺,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
至长韵大篇,动数千百言,而顺适恰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捻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
”[1](p448)王若虚认为“自然之势”乃“诗之大略” [1](p437),“哀乐之真,发乎性情”是“诗之正理” [1](p449)。白诗正因“自然”、兼有“性情”之“真”,才显得“顺适恰当” 。
苏文、白诗之“理”何以能“妙”?王若虚认为关键就在于“浑成”。如此看来,王氏所言的文章“妙理”,应该是指作家在自由的精神境界之中,极其自然而恰切地让审美客体和创作主体在“真”的基础上完成和谐沟通,使得作品无论在“意”还是“字句”上,都透出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
对于文学理想境界的实现途径,王若虚认为一方面是追求文辞的自然平淡,另一方面是把握语意的“一以贯之”。
自然,即天然,也就是王氏所言的“天全”。追求“天全”,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观。晋代葛洪云:“至真,贵乎天然。”[4](p392)唐代皎然云:“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冥,难以言状。”[5](p1)而首先将“天全”一词运用到文艺批评方面的是苏轼。如“醉笔得天全”[6](p2072),“鞭策刻烙伤天全,不如此图近自然”[6](p721)。
在苏轼的影响下,王若虚以“自然”作为成熟文章的标准。他引用其舅周昂文论主张曰:“自然之势,诗之大略,不外此也。”[1](p437)自己亦说:“文章岂有繁简?要当如风行水上,出于自然。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
”[1](p233)而当标准一旦确定,凡与此不符者,皆受到王若虚锋芒毕露的批判,即便是苏轼,亦不例外。如:“《归去来辞》本自一篇自然真率文字,后人模拟已自不宜,况可次其韵乎?次韵则牵合而不类矣。
”[1](p388)又如:“东坡酷爱《归去来辞》,既次其韵,又衍为长短句,又裂为集字诗,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尔,是亦未免近俗也。”[1](p454)据《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一)》所载:“《孔子世家》载楚狂接舆歌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
’加两助词,不惟非其本语,抑亦乱其声韵矣。”我们可以看出王若虚并非决然反对声韵,他所反对的只是“次韵”,其中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次韵”违背了其以“自然”为落脚点的文章创作标准。
只有实现语意的“一以贯之”,才能做到浑然一气,反对堆垛,不可句摘。
这便是王若虚主张的“浑成”说。基于此,王若虚曾批评黄庭坚《食瓜有感》诗曰“固皆瓜事,然其语意岂可相合也?”[1](p472)王若虚认为文章须作全局观,既为整体,则宜融会贯通其文意。他批评黄庭坚说:“鲁直于诗,或得一句而终无好对,或得一联而卒不能成篇。
”[1](p478)批评苏叔党《飓风赋》云:“‘此飓之渐也。’少个‘风’字。又云:‘此飓之先驱尔。’却多‘飓’字,但云‘此其先驱’,足矣。风息之后,父老来唁,酒浆罗列,至于理草木、葺轩槛、补茅茨、塞墙垣,则时巳久矣。
而云:‘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兴;动者自止,鸣者自停。’岂可与上文相应哉?”[1](p421)批评司马光云:“是非有定理,而前后反复,以迁就己意,此最立言之大病也。”[1](p338)王若虚“千古以来,惟推东坡为第一” [7](p88),显然与他认为“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 [1](p417)是有着非同一般关系的。
事实上,王若虚于经、史、文一生淹通,以重辨析、重评论著称于世,对其舅周昂的文“意”之论甚为推崇:“文章以意为之主,以言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1](p437) 这里的“意”,其实就是文章整体呈现出来的充实的内容和饱满的思想情感。
“意”的重要性就在于从宏观统摄全局,以保持文章焕发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意”的最终实现,则必须要依赖于微观方面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完美配合。而“理”,便是其中至关重要、内涵丰富的因素之一。所以要做到语意的“一以贯之”,文理是必不可少的。
“文章必有规矩准绳,虽六经不能废。”[1](p151)这便是王若虚所说的“文理”,其文论中的“为文之理”,是从微观到宏观对文学创作给予的必要关照。是作家的思维逻辑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广义上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万物自然之理;一是为了表达主旨的需要,文章自身所必须具备的篇章建构,如结构、法则和脉络等。
关于“文理”的重要性,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曾明确提到:“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
”[11](p21)就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来说,剪裁、布局、联结是文章结构的主要内容,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篇作品结构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作品思想内容的艺术效果,甚至关系到作品的成败。
“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杂乱而无章,非诗也。”[13](p188)沈德潜此论虽就诗而言,然亦适用于其它文学样式的创作。所谓“亦须论法”,也就是要讲究结构的法则。当然,要讲究结构法则,但又不应把法则僵化。
而王若虚的文论观,正是将“文意”至于首位,“文理”(结构、法则和脉络等)为其而生,随其而动,这种不泥于死法的结果,便是作品能够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王若虚的“文理”主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材料的取舍。王若虚反对无关文章整体的琐碎细节的陈述,始终提倡那些发明世道人心、有益教化、彪炳史册的材料不可或缺。如:“操一生所行,类皆不道之事,独此一节,有光青史,而陈寿略之,岂非阙典之甚哉!”[1](p295)王若虚认为,文之胜在意而不在言,一味注重材料的繁富,实无助于凸显文意。因此,为文之时镕裁之功便显得尤其重要,若违此理,则必成败笔。
二、注重文章的整体性。首先,必须坚持题、文相符。王若虚认为,若是题目和内容之间出现龃龉,绝对会妨碍文章“意”的表达。其次,内容中的各个部分要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贯通全文的“意”。第三,文章须自具首尾,求得“意”之完整。如:“相如《上林赋》设子虚使者、乌有先生以相难答,至亡是公而意终,盖一赋耳。……岂相如赋《子虚》自有首尾,而其赋《上林》也复合之为一邪?不然,迁、固亦失也。”[1](p379)
三、关于“文法”、“句法”的探析。欲申文“意”,必求文“理”,而要诗文顺达通畅,从篇章结构到段落字句,都是不容忽视的。就“文法”而言,王若虚甚为关注。他在《滹南遗老集·文辨(二)》中说:“予谓左氏之文固字字有法矣,司马迁何足以当之?文法之疏莫迁若也。
”所谓“文法”者,只是借以表“意”的工具,虽然王若虚继承周昂的文意之论,但具体写作中的“文法”绝对不能是固定、呆板的模式——“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
”[1](p415)对于“句法”,王若虚说:“鲁直区区持斤斧准绳之说,随其(苏轼)后而与之争,至谓未知句法。东坡而未知句法,世岂复有诗人?”[1](p461)由此可见他反对的是说苏轼不懂“句法”的这种观点,而不是反对句法本身。
然而王若虚肯定“句法”是有条件的,他认为,“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1](p477)“自得”是就“意”的角度而言,而“句法”则是出于“字语”的考虑,如此来看,不论是为文之“文法”还是作诗之“句法”,都统摄于其“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的文学思想的。
四、文体之辨。王若虚既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同时又是出色的史学家,但他对文和史却有着不尽相同的评判标准。他说:“作史与他文不同:宁失之质,不可至于芜靡而无实;宁失之繁,不可至于疏略而不尽。”[1](p232)由此可见,在文学中,为了现“意”则完全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辞采趋于华丽、行文讲究用韵都是可以接受的。
而对于史学,他则要求以“征实”为原则。王若虚认为文学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他说:“世间万变,皆与古不同,何独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1](p494)故于继承古人成果的同时,他又结合金代文学的发展状况,通中寓变,对“文体”之说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王若虚所言之“体”,于体裁、风格之外,有时亦指文章内容的繁简和结构布局。
如“夫韩文高出古今,是岂不知体者……不必以寻常体制绳之也。”[1](p390)对繁琐之文,大加批驳,对过简之文,他同样痛予针砭。那么,宜繁还是宜简究竟该以什么为准绳?王若虚说“文之大体,固有不同,而其理则一”[1](p400)。 而这“理”无疑就是“文章正理”——惟“适其宜而已”[1](p412)了。
要关注文意的“一以贯之”,除了“文理”,我们亦得关注“文势”。在王若虚的文学批评中,“文势”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几乎于经、史、文、词等诸多方面无所不包。如其论《论语》曰:“‘子路问成人’章,胡氏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为子路之语。
此盖惑于曰字耳。观其文势,殆不然也。”[1](p79)其论《孟子》曰:“‘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之说,或以心字属上句,或以属下句。予以文势观之,语皆不安,中间或有脱误,未可为断然之说也。
”[1](p102)其评《史记》,《滹南遗老集》卷十三专设“文势不相承接辨”。评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曰:“病在太多,且过于浮艳耳……盖不唯为雅正之累,而于文势亦滞矣。”[1](p393)评蔡松年词曰:“萧闲《使高丽》词云‘酒病赖花医却’,世皆以花为妇人,非也。
此词过处既有‘离索’、‘余香’、‘收拾新愁’之语,岂复有妇人在乎?以文势观之,亦不应尔。”[1](p492)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势”是一个很古老的术语,《老子》书中已提出“势”的观念。《老子》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8](p203)战国诸子如孟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常用此字。“汉人的训诂学中,‘势’多训为‘力’”。
[9](p291) “‘势’的这种力,可以体现于主观上,如某种情状的许多次反复后给人的心理造成某个定势,予人的行为以影响力;但一般讲‘势’,是体现于具体事物的关系中的客观的‘力’,它不能孤独地存在,而必须依托于事物。
”[9](p291)“势的基本含义是事物由于相互之间的位置而引起的变化趋向。”[10](p137)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定势》专门讨论了“文势”。他说:“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
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此而已。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蕴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
”[11](p530)到唐代,柳宗元则以“势”解释社会制度形成与历史变动的原因,其《封建论》将“势”与“意”对立起来,“意”指主观的愿望,“势”指客观的趋势。王若虚的文学批评在“文意”、“文理”之外,运用了“文势”,这就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文章创作过程中不得不然,须一气贯通的写作要求。
此外,王若虚亦提倡文章境趣的含蓄中和。王若虚所言的文章,是一个泛文学观念下的特殊概念,但以求同存异的眼光具体来看,他对文和诗的要求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王若虚主张诗境须含而不露。所谓不露,颇似南宋严羽所说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12](p688)的艺术境界。
他说:“前人有‘红尘三尺险,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萧闲(蔡松年)词云:‘市朝冰炭里,满波澜。’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迹。”[1](p490)而文比诗的要求则更为朴实,他认为文更宜求“真”、求“理”。
比如他批驳马子才《子长游》云:“驰骋放肆,率皆长语耳……虽诗词诡激,亦不应尔,况可施于文邪?”[1](p386)但不论是何种文体,“直以写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厌乎人意,而不为奇诡以骇末俗之耳目” [1](p524)的含蓄中和之境趣,都始终是王若虚追求之鹄的。
要之,在王若虚看来,惟有借助于“文理”、“文势”等诸多必要措施,做到行文的自然,文意的贯通,加之淡雅尚实、含而不露的意趣追求,才可能达到“浑然天成”的至高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胡传志,李定乾. 滹南遗老集校注[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
[2]苏轼.苏氏易传[C]. 丛书集成新编本.
[3]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M].四部丛刊本.
[4]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李壮鹰.诗式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6.
[6]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刘祁,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7.
[8]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2]何文焕辑.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霍松林.说诗晬语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