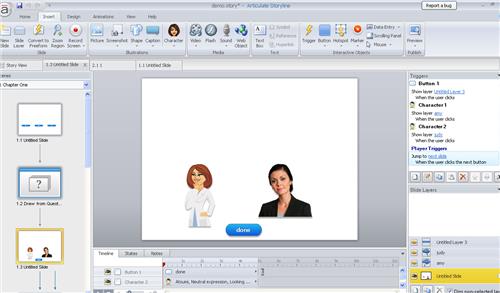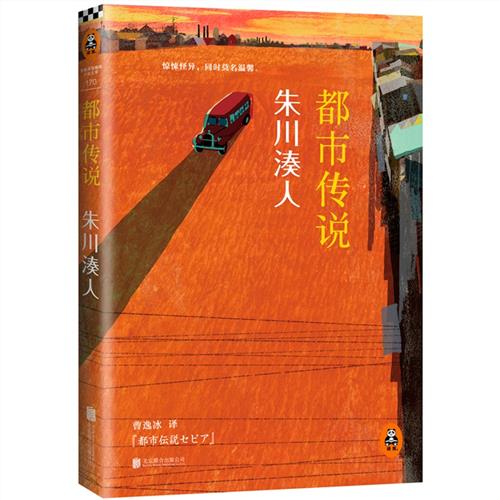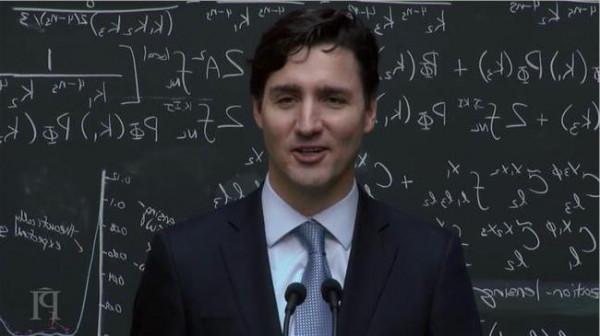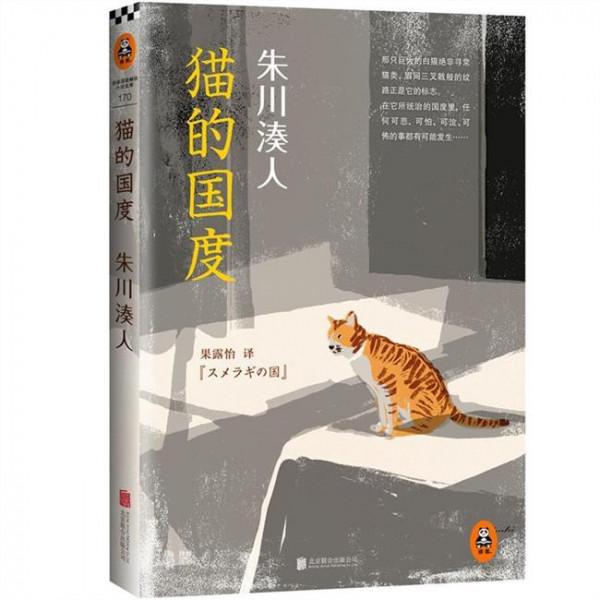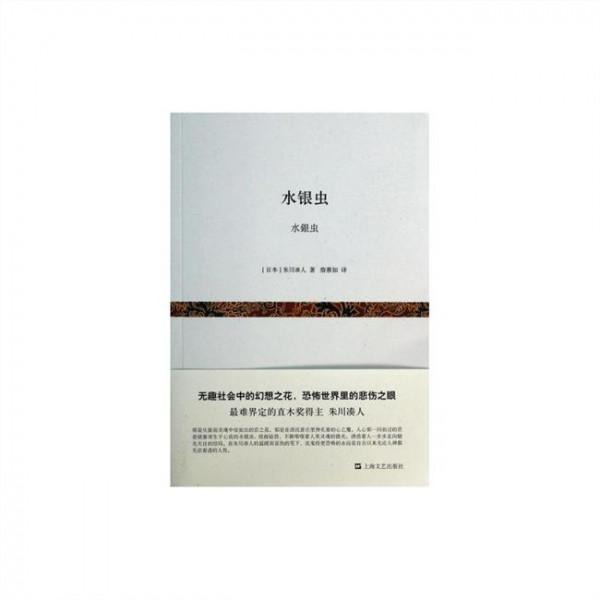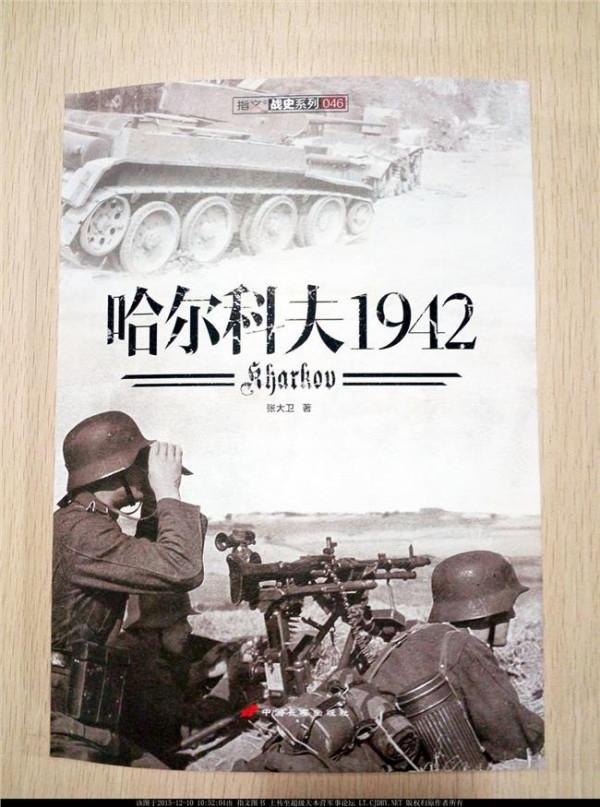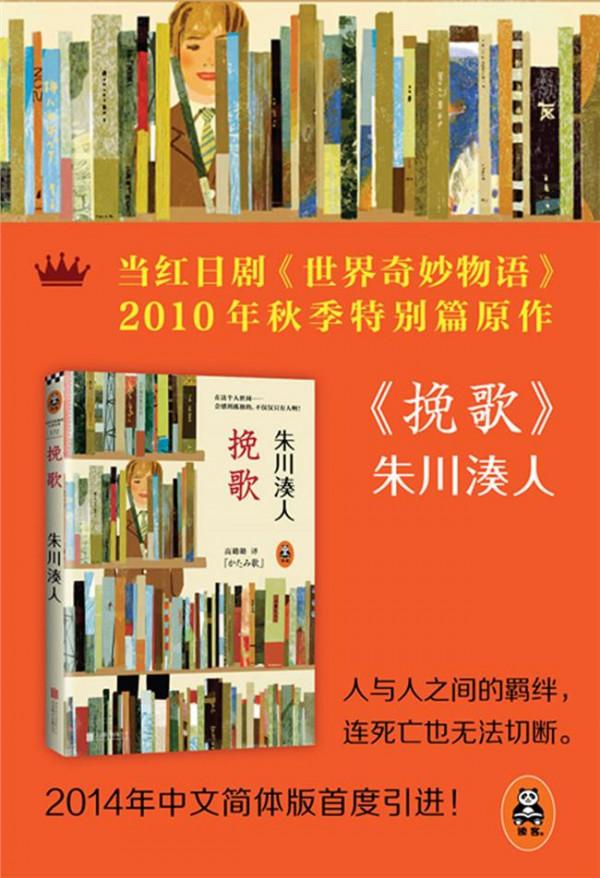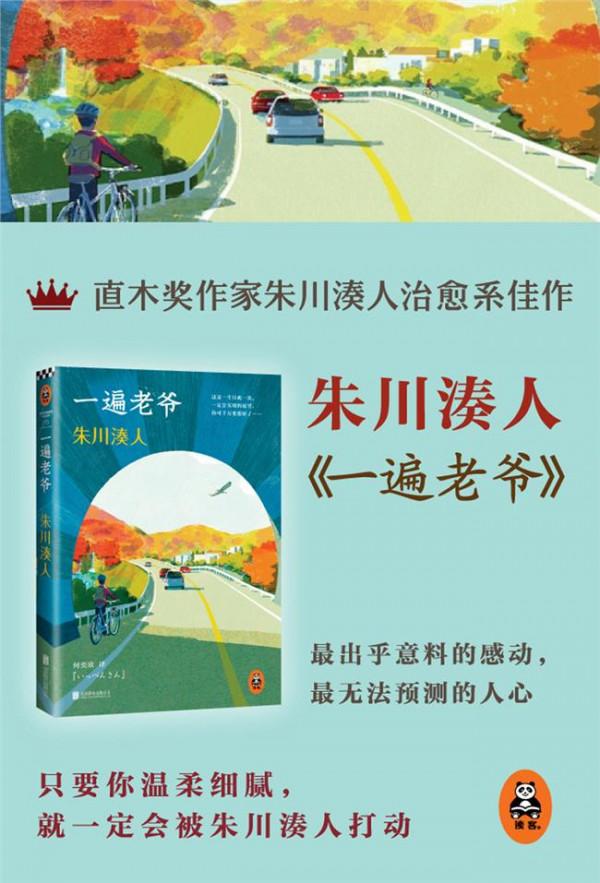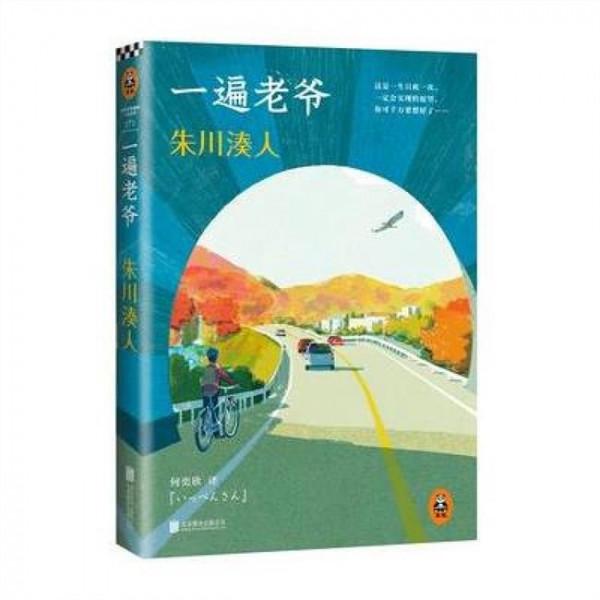朱永嘉其人 朱永嘉与余秋雨 朱永嘉:余秋雨否认文革 他做人有问题
朱永嘉(左一)、朱锡琪(左二)、金光耀(左四)、金大陆(左三)
道不同
“你们小年轻啊,肯定都是支持他(指张维迎)的说法,不支持他(指林毅夫)。”朱永嘉先生看到记者手捧的《人物》杂志封面上正好是上述二人,马上半开起了玩笑。
这个85岁的老人时不时会在网上被称作“文革余孽”,就在4月底,他的博客上还新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标题上写:照搬西方法制是一种懒人的思维方式。立刻有人在评论里拿“文革”的事情嘲讽他,但他却反思起了自己的行文——我毕竟从那个年代过来,写的东西呢,落笔还是有一点凶,显得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不大好。
这让他看上去不像一般网络骂架语境下的“毛左”。一个简单的佐证是,他与前些年几乎被民间推上右派代表位置的朱学勤,一度关系良好。朱学勤整理过其履历,朱永嘉曾任复旦历史系总支书记,后来华东局组织反修写作班,地点在李鸿章为爱妾购置的“丁香花园”,集体笔名“丁学雷”,寓意丁香花园学雷锋,朱永嘉在“丁学雷”统领历史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
他是权倾一时的海上闻人,中央领导一度想把他上调当文化部长,但张春桥不放。
“四人帮”倒台后,他曾书生意气地提议上海发动武装政变,“再造一个巴黎公社”,当然难逃牢狱之灾。1988年,已蹲过11年号子的朱永嘉提前保外就医。按照原先14年的刑期算,他出狱时应该已经过了退休年龄,“文革”前的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不必再安排其就业,然而他也算不上正常退休,于是学校只负责了住处和每月两百块生活费。
很长一段时间,他靠给台湾三民书局整理古籍维持生活,《唐六典》、《容斋随笔》、《春秋繁露》,20块美金1,000字,几百万字下来,收入也算不菲,但毕竟辛苦。后来大病住院一场,手术费沉重,是朱学勤几番介绍他到“沙龙性质的习明纳尔(seminar)”去讲课,地方在郊区,参加者“有一些老板什么的”,接过去半天一天,讲讲明史,讲讲曹操,讲课费开得颇高,生活就此宽裕下来。
和朱学勤的来往近年渐少,朱永嘉没有深究原因,“可能是因为忙,也可能是因为毕竟道不同吧”。尽管能接受各种意见,也很少跟人红脸,但他始终坚持中国走西方的路不行。至于为什么不行,他会跟你从将近3,000年前的历史娓娓道来:“春秋时期就有市的概念,但这个市是有从属性的,是为了满足官僚阶层需求而存在的;西方的市呢?市民社会。
中国没有这个概念的。”朱永嘉生在上海,虽然身材高大体格健硕,看上去不像上海人,但一开口便是笃悠悠的吴语普通话,很多停顿和语气词,还要在句尾加上“的”,和网上的战斗檄文判若两人。
“要走西方那条路,说到底就是要利益再分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够好好谈的,利益再分配,那就要乱的呀。”他举了一连串的例子,牛李党争唐亡,新旧党争宋亡,东林阉党明亡,帝后党争清亡,当然还有后来的合作和内战,“(走西方的路)是逻辑推演出来的,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要天下大乱的”。
这是一种混合了旧式读书人忧国忧民的“左”,以至于朱永嘉也并不受很多自诩左派的人士欢迎。连他自己都说,如果不是反右的时候他正好肺病开刀,躺了一年,早在1957年他就该被划了右派,也就不会再有后来的市委写作组领军人物、姚文元背后的笔杆子朱永嘉。
朱的父亲1930年代开始做进口玻璃生意,直到1948年蒋经国为抑制通货膨胀,在上海推行了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的金圆券改革后,父亲预感到“就要不行了”,便把大部分存货都托学徒和亲戚带到台湾。小时候家里的生意做到什么程度,朱永嘉无法说得确凿。
但1959年全国陷入饥荒,物资极度匮乏,朱家实在没办法,只好给台湾去信,没想到对岸每月汇来的股息竟有500美金之多。在这样的家境下,朱永嘉在读高中时就瞒着长辈偷偷加入地下党,不能不说带有一些“原教旨”的共产主义者气质。
这甚至可以从他的住所布局看出来。从提篮桥监狱出来27年,朱永嘉始终住在复旦当时安排的第一宿舍老楼里。房子是一组1940年代日据时期的旧式连排屋,坐东朝西,虽然有两层楼外加三角斜顶,但一进门便是窄而陡的楼梯,每层楼两个房间,厨卫和过道皆尺寸迷你,每个房间的面积也差不多就在六七平方米。
因为年代久远,门外的马路不断新修抬高,夏天暴雨总是要倒灌进水,门卫回忆起2013年上海的特大暴雨,“水涨了哈结棍(非常厉害)”。
朱永嘉腿脚还利索,卧室仍设在二楼,一楼的小书房一面开窗,另外三面墙,书堆得铺天盖地。一开始房间里连书架都没有,只有两个蓝色铁管上下铺,他便在床上摊书。后来历史系的后辈看不下去,替他置了书架,他也不把上下铺处理掉,挪到隔壁房间,竟把那里变成了外来务工人员临时落脚点。“这样我就在家里也可以田野调查,了解一些他们的生存状况。”
除了女儿安排照顾他起居的保姆,在上下铺临时落脚的多是周边做钟点工的阿姨。靠南面一排房子里的一户人家,家里举家移民,本来的住家保姆一下子找不到下家又不愿意回乡,就去央求家里有空床铺的朱永嘉,能不能借宿几日。这就算开了先例,之后的人来人往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模式,“我也不收他们钱,(他们)出去做工么,有时候回来顺便帮我买买东西,就是跑跑腿,买东西我还要算钱的。”
复旦历史系图书馆员李春博从2006年起帮朱永嘉整理一些资料,李记得朱永嘉常常与宿舍旁边的摊贩聊天,有次城管要抓摊贩,摊贩躲进了朱家,老先生还挡着城管与他们理论,最后血压飙高去了医院。
他从身边的务工者们那里得到了很多农村的消息,土地荒芜,无人务农,于是深深发愁。他去历史里找答案,但发现眼下发生的变化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宅基地和承包田不就是北魏的永业田和口分田,赋税制度的变革也大体都能找到对照,“中国的三农问题啊,这样下去没有出路的。”
即便如此,他仍相信,如果能回到共产党“最初的革命传统”、“为公、为人民”,这些难题便有了解决的可能。他不否认至今仍怀念毛时代,2009、2010那两年的12月26日,他给毛写情真意切的汇报信,或者去学校食堂吃碗面。
他一字一顿,说得特别慢,像要说服记者又像是自问自答地评价毛:“(党内高层)严格限制子女的,恐怕……毛还算一个吧。”谈到1950年的大榆洞,他更是定定看住你,用丝毫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毛是绝对没有意思把位置传给儿子的。
对毛的崇敬和追思被带入了他的“文革”叙述里,比起否定“文革”,他倾向于认为毛的本意是发动一场有理想的改革运动,但个中执行层面的偏差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文革”变为一场失败的教训。部分现当代史学者告诉《人物》记者,朱永嘉愿意如此频繁和看似诚恳平实地讲述“文革”,也是替毛和朱永嘉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构建合法性。
在朱永嘉之前,“文革”叙述多来自受害者,少有的另一方声音或语焉不详如徐景贤,或像聂元梓那样索性“翻供”,一口咬定自己“在法律上没有过错”。相较之下,朱永嘉的回忆显得相当详实,仅仅从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到1968年“一月革命”收尾的4年间,就整理有20余万字。他准备把回忆分为三部曲,第一部刚刚做完,接下来的两部,是从1968年到1973年林彪事件基本处理完毕,和1973年之后的“最后的文革”。
他评价姚文元勤恳朴实,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除了文艺方面,其他的知识有点薄弱;张春桥城府比较深,行事狠辣,胸襟也不开阔,然而在姚文元批示要发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后,张却敏感此事可能影响到老领导邓拓,要给他打招呼,提醒他当心。
云谲波诡的癫狂时代,一个招呼当然无济于事,就像朱永嘉的“再造一个巴黎公社”救不了倒台的“四人帮”。但他想着,毕竟姚、张对他有知遇之恩:“当时我对局势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分析,姚文元和张春桥失联,那肯定是出事了。
出事了,无非是汪(东兴)动手,华(国锋)做的决定,背后还必须有叶帅支持。怎么办?要么乖乖投降,要么,两军相逢勇者胜。”他提议武装政变,也深知以上海手里的这点兵力并无可能,所以说了“搞一两个礼拜不行,搞一天两天也可以”。
写作班子的人又拟了“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口号,这些话后来都变成反革命罪状,但朱永嘉想得很开,他觉得自己说不说这些,“排排坐”排下来都差不多,毕竟自己是上海文斗派(区别于武斗派)的领头。
1976年10月18日,原先计划好的仙台鲁迅纪念展,他还是照旧作为代表团团长带队前往。行程中有一次累了坐下来歇一会儿,他眼看盯梢的人“急得要死,拼命在找我”。从日本回来以后旋即被隔离审查,他想想自己砍脑袋应该还不至于,毕竟“文革十年,我没有升官呀”,便给母亲带话说,“在里面估计时间长了,给我带一套二十四史吧。”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做“文革”口述史多年,他认为朱永嘉有作为历史学者的基本素养,比如回忆到某一事件时,会特意翻阅如《文汇报》、《解放日报》当时的文章,并联系当事人比照记忆,以求在基本史实上不出错。金光耀过去攻中美关系史,因为自己的知青身份逐渐转而对“文革”发生兴趣。2002年替本科生开设“文革”史课程的时候,金光耀的导师、复旦历史系的老总支书记余子道,把朱永嘉介绍给了他。
与外界想象略有出入的是,朱永嘉其实并非一开始就愿意谈论“文革”。金光耀自和他认识起,前后做了他两年的思想工作才“终于取得信任”,对方答应开始做口述。而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每次金光耀提到“文革”,必会被朱永嘉岔开话题。金光耀分析,这一方面缘于话题敏感,另一方面则因为朱永嘉对自己和金的要求都很高,“同意谈了以后,必须把背景材料都准备好,他也都要看好。”
有学者拿他和同门师弟朱维铮做比较,同样替写作组出过力,朱维铮对“文革”几乎闭口不提,这被认为是歉意的一种表达;而朱永嘉乐于开口,则有粉饰“文革”的嫌疑。与两人都有过接触的金光耀觉得事情可能并不是那么非此即彼。
朱永嘉从提篮桥出来以后的身份近乎闲人,而朱维铮彼时已成名成家,既没有谈“文革”的时间,更有诸多顾虑。在去世的半年前,朱维铮约金光耀谈了两个多小时,回忆自己在“文革”初期作为《文汇报》记者,前往北京办事处参加中央领导接见,并和五大造反派接触的一些碎片。
此后朱维铮安排弟子逐一在病榻前交接学术研究的未竟事宜,又在去世前一周再度约金光耀周六上门做“文革”访谈。然而就在周五,他的肺癌病情突然恶化,最终于周六下午去世。
金光耀做过不少“文革”小将乃至干将的访谈,在他印象里,朱永嘉即便对毛的大部分都是信奉的,也始终反感暴力,并且能容得下不同看法。其他不少毛的追随者会一上来就要问明金对“文革”的看法,当得知他持否定态度后,便不愿多言语。
在与朱永嘉对谈数月并一次次核实、修改,历时两年写成口述史后,他的判断是,朱永嘉“并没有刻意要讲自己的‘文革’叙述”,而除开观点不同外,在历经曲折后仍能执着梳理历史,这也让金光耀心怀敬意。
虽然被下放到黄山茶林场7年,金光耀治“文革”史时,对这位曾经的“文革”风云人物依旧抱有理解。他甚至引用复旦元老金冲及的话来描述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无从选择——“如果我在,我也不能保证不会走朱永嘉的路。”(金冲及在朱永嘉之前担任罗思鼎小组组长,后随石西民一同调任北京,“文革”期间石西民被打倒,金冲及亦未在“文革”前线担任工作。)
几乎如出一辙的,朱维铮也因为跟随《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一起炮打过张春桥,在1970年被隔离审查。朱维铮的师弟刘其奎曾笑他“因祸得福,不然说不定会落得与朱永嘉一样下场,坐个十年八年监狱”,而朱维铮并不言语,只点头称是。
朱永嘉意外地在这一点上和金光耀站到一起,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不止一次提及历史的偶然性,甚至带上一点宿命论。虽然需要翻看当时的报刊才能确认,但他大约摸记得林彪事件发生半年前,《文汇报》上层刊登过一篇用了笔名的文章,内容不大合张春桥的意。
当时报社有个年轻人是写作组过去的,张春桥要了解情况,便问那个年轻人这篇文章怎么回事,对方随口回答文章是空四军(空四军的第一政委王维国为林彪集团骨干人物)写的。张春桥立刻安排下去写了针对林彪的批判文章。
“这篇文章恐怕制造了紧张,所以林立果来不及搞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然后便是林彪外逃,坠机于蒙古国境内。直到一切尘埃落定,朱永嘉才得知那个报信的年轻人不过为了交差,信口胡说了一个空四军。他亦说不清如果没有这个插曲,历史的走向是否会迥异。
陷入宿命论的时候,连带着遵从一生的信仰也变成了一种不那么牢固的存在。他订阅了大量报纸和杂志,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聊到国际局势,他反而并不赞同左派的美国阴谋论,相反认为“美国的外交,还是有点理想主义的”。他也能接受西方国家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但又时而觉得“资本主义毕竟是虚伪的”。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知识分子只有依附在政权的皮上才能有所作为。然而他又一早被开除党籍,体制内把他当作体制外。
最终,他退回到古时士人的行为准则里,没有害过人,身边的人——即便是“文革”时候挨过整的——也都对他评价不错。“我已经85岁了,还求什么呢?”他像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词,并终于下定决心,“但求一个做人一以贯之吧。”
在这个标准下,便无所谓左派,也无所谓右派。他可以和当时同在写作组的老人们回丁香花园,“没什么别的,就是叙叙旧”,也可以完全不喜欢“乌有之乡这种恶煞的面孔”。另一个不符合他传统士大夫价值观的故人是余秋雨。他在丁香花园时,对这个颇有才华的年轻人多加照顾,没想到多年以后,曾经被刻意栽培的年轻人矢口否认那段过往。朱永嘉没有觉得余秋雨否定“文革”有多要紧,关键在于“做人,不能是这样做的呀”。
他还稍微有点沉浸在这愤懑里,隔壁邻居正好牵一条哈士奇出来溜达。雪橇犬直奔朱永嘉,他便摸了一会儿狗。又有不知道哪家的小孩放学经过,先同“朱爷爷”打招呼,又看到大狗,被吓了一跳。
他被这一幕逗得笑了起来,转而向记者求证:“你看我的晚年生活,颇不寂寞的吧。”
他转身把门旁两只旧搪瓷饭盆拿进屋,不一会儿盛了些水和猫食出来放好,之前一直躺在窗边、被西晒晒得眯起双眼的一黄一白两只胖猫,便倏地跳到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