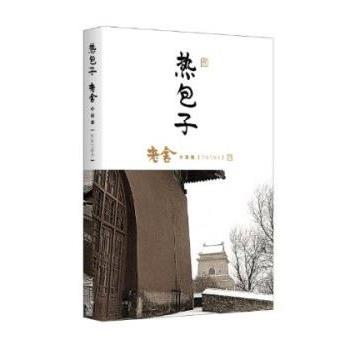刘海玲:从蔡楚生的《新女性》看“五四”以来“新女性观”的衍变
从蔡楚生的《新女性》看中国现代“新女性观”的演变
刘 海 玲
内容提要: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中,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女性观的两次激变至关重要。蔡楚生拍摄于三十年代的电影《新女性》,即通过对三个女性命运的刻画,形象地诠释了左翼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妇女观”对五四时期生成的自由女性观的取代,在艺术层面上前瞻性地实现了中国现代妇女问题在意识形态上的质的飞跃。
关键词: 蔡楚生 新文化运动 左翼电影 女性观
从“奴隶的奴隶”到“能顶半边天”的主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几千年苦难深重的中国妇女确实以亘古未有的速度走上了解放之路。其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左翼革命文学时期,通过思想交锋、文艺宣传、社会运动和生活实践等形式,实现了新女性观的两次重大转变,即从传统“三从四德”的“封建妇女观”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倡扬的“自由女性观”,再到左翼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妇女观”,这是现代妇女问题在意识形态上的质的飞跃。
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分析蔡楚生导演于三十年代拍摄的电影《新女性》,并叹服艺术家蔡楚生前瞻性的思想高度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一、“妇女解放”:对封建伦理纲常的一次颠覆
我们常常讶异于西方如尼采、叔本华等哲学家对女人明目张胆的蔑视和辱骂,对西方资本主义进程中以女性为主体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壮大便觉顺理成章。但在近代中国,有关“男女平权”、“婚姻自由”等妇女解放问题却首先是由男性的思想家提出的,这不禁令人追问处于男权社会中心的男性知识分子提出妇女解放问题的逻辑起点。
女性主义在西方和当代中国被定义为女性关于性别平等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随之采取的行动,而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也绝少走出国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可能。几千年的传统使囿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藩篱中的中国妇女很少能具备思考自己解放自身的自觉和勇气。
因此周作人在其译的《贞操论》序中说,“女子问题,终竟是件重大事情”,女子自己不管,“总有极少数觉悟了的男子可以研究。”①口气固然自负,但不能否认这是当时中国关于妇女问题的总体社会现实。
当近代知识分子对日益衰落腐朽的封建中国彻底失望,转而到西方寻找救国强邦的方法时,“民主”、“自由”、“科学”的新思想就成为近代直至五四高举的旗帜。“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中国以传统纲常为中心的政治伦理,使身为男性的有识之士亦被捆缚其中,如鲁迅所言,“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
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而最底层的“台”,“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
②要打破这极其荒谬又极其顽固的封建制度的“铁屋子”,绝非容易之事——在中国是“哪怕挪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因此,以西方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为参照,从最底层最基本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中国妇女问题出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出了对封建政治伦理的挑战和颠覆。
近代维新改良主义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以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观为前提,提出男女天赋平等、人权平等的思想,为妇女解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辛亥革命领导人孙中山更是大力提倡妇女教育,主张妇女参政。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彻底批判封建主义,提出了“打破父权专制”、“打破男权专制”的口号,提倡女性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使妇女解放思想伴随着新文化运动迎来了第一次高潮。
《新青年》特设“女子问题专栏”,撰稿者大多为男性,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都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阐述自己关于妇女问题的认识。
例如陈独秀从独立人格的构想出发批判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尊重个人独立自立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妇而不见有一独立自立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
……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而此丧失,他何足言。”③对“为子为妇”者的自主独立人格的张扬,侧重点是对“为臣”附属顺从的奴性的批判,目的是彻底颠覆“君为臣纲”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观念,子、妇、臣的独立和解放,所实行的是命运一体化的捆绑式操作,其理如蔡元培改写的“一家犹一国也”。④
中国男性知识分子还希望,姐妹妻女若独立自主,也可以促成男子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独立,从而形成一个“良善”的理想社会,“我们中国的姊妹们若能把这种‘自立’的精神来辅助我们的‘依赖’的性质,若能把那种‘超于贤妻良母人生观’来辅助我们的‘贤妻良母’观念,定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生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那种‘自立’精神”,“其实是善良社会绝不可少的条件。”⑤
总之,对于近现代知识分子而言,妇女问题是几千年封建中国所面临问题的表征之一,妇女解放是推翻封建君权统治建设现代社会的必然步骤。正如文学革命中“言文合一”的主张,究其实质是为了“新民”、“变法”、“救国”,也可以这样说,妇女解放问题的提出和实施是近代思想家们对理想中国建构的衍生物。
对此当代学者刘思谦归纳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实质而言,是由男性的子一代‘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为主导对父辈封建文化的批判、反抗,形成观念上精神上的无父无君时代。
”“由于女性在这一结构中整体上的被压迫、被剥夺地位,由于她们处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种男性权力统治的最底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喊出反封建反传统口号的同时,必然要提出妇女解放的要求。”⑥此后关于中国女性观念的思考和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始终伴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动荡曲折的社会发展进程中。
父权社会使女人沦为非“人”的男性附属品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积淀在厚重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历史长河中,要彻底揭开“铁屋子”式的文化之障,不能仅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上的探讨,与之相随的是社会实践层面上的妇女解放运动,文艺宣传层面上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
拍摄于1934年的《新女性》则是这三个层面构成的系统中历时性的评价和展望。蔡楚生在导演了遭到左翼阵营激烈批判的《南国之春》、《粉红色的梦》之后“清醒过来”,成为“为大众所有的作家”⑦,决心“把社会真实的情形不夸张也不蒙蔽暴露出来”⑧轰动影坛的《渔光曲》面世不久,蔡楚生又导演了以自杀女演员艾霞为原型、由著名影星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片名“新女性”即可看出蔡楚生着重表达的是中国妇女的现代转型。
影片中的王太太是中国传统的附属型女人,她是另外两个女性主角韦明和李阿英的陪衬,导演并没有过多地介绍她的生活史,观众可以约略地作出判断:王太太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嫁给王博士后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
蔡楚生对王太太进行了漫画式的讽刺和批判。丈夫有博士头衔有社会地位有经济收入,王太太表面上非常满意自己的人生归属,尤其是看到过去的同学韦明简陋的生活条件后。但实际上她没有职业、没有收入也没有家庭经济支配权,生活空虚自不必说,就是日常开销也只能或低声下气或撒娇耍赖地乞求丈夫。
她对丈夫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毫无约束能力,虽然也可以在王博士的风流事败露后大吵大闹,但根本改变不了自己今后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遭驱逐的奴隶地位。
王太太的经历在展示着旧式妇女的人生:在男人处于权力中心的夫妇——男女结构中,女性必然失去独立地位成为依附型的女人,无论女人怎样打扮修饰或者还受过教育,都无法摆脱被忽视被歧视甚至被抛弃的边缘化命运。对囿于中国传统婚姻中可悲的旧式妇女的批判上,蔡楚生导演与五四新文化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二、韦明之死:以“五四”精神塑造的“新女性”的失败
“女性”是二十世纪初期新兴的词汇,确切地说,它是在五四时期和大量西方话语一起进入中国的,与“启蒙”、“民主”、“文化”、“知识分子”和“个人主义”等语汇交杂在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个重要的中心词。
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代表着一种“Modern girl”的形象,是西方的、现代的、青春美丽的、自主独立的知识女性,如《海滨故人》、《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当一个女人在惨痛的生活经验或在新思想的熏陶中觉悟到自己也是一个“人” 而不是男权高压中的保姆和生育工具时,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觉醒并出走,“女人”也可以成长为“女性”。
出走的娜拉们意味着“中国女界”的一点一点“超于贤妻良母人生观”的“新鲜空气”,是对封建传统旧有秩序的象征性颠覆。
《新女性》中的女主人公韦明就是这样一位“新女性”形象。
五四时期的中国妇女运动提出的关于妇女的权利问题可以归纳为:政治以及公众活动参与权;经济独立权;婚姻及家庭生活自主权;教育权。韦明的道路是这个时期女性人生道路的代表:接受教育—男女同校—自由恋爱—先行同居—父母反对—从封建家庭出走。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现代女性争取男女平权、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所不约而同选择的人生之路。
争取婚姻和家庭生活自主权,就要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俗,当然女性首先要逃离的是父权家庭。觉醒并出走的娜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几乎成为女性的楷模,但娜拉毅然告别的是“妻子”的角色,而中国的“娜拉”们却是在努力使自己成为“妻子”。于是我们发现这个时期的新女性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生活轨迹:走出父权专制的中国女性又重新生活在夫权专制的阴影之下。
因此,五四时期主体意识已然觉醒的中国女性通常经历着两次出走:第一次是对“父为子纲”反叛,第二次是与“夫为妻纲”告别。 但第二次的告别无疑是对女性身心的重创,换句话说,第二次“出走”的同义词通常是同样获得自由的男性对女性的“放逐”,例如《伤逝》中“觉醒的”子君的命运。“新女性”韦明刚刚脱下西式的婚纱、结束热闹的婚礼,抱着才出生的女儿,即惨遭丈夫的遗弃。
娜拉走后怎样?敏锐而深刻的鲁迅在继续探讨女性的出路时毫不留情地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⑨摆在新女性面前的是两次人生考验:子君先以“回来”宣告了女性第一次逃离的失败,又以死亡拒绝第二次更为严酷的拷问。但更多的“娜拉既然醒了”,就“只得走”,所以韦明究竟怎样“走”就格外引人关注。
接受新式教育的韦明有自立于社会的资本。鲁迅的 “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的忧虑对于韦明来说仿佛已经不是问题:韦明把女儿托付给姐姐,自己成为一所私立女子中学的音乐教师。她既是受学生尊敬喜爱的教师,还是受读者追捧称赞的作家,身边又不乏有钱有权或者有才华的追求者。钢琴、作曲、讲台、小说、旗袍、舞会,构成了这位追求个性解放独立人格的五四新女性的几乎全部生活,拥有知识,趣味高雅,更能自食其力。
韦明仍然坚守着“自由”、“平等”的五四精神。韦明没有像子君一样退回到遏制自由的传统家庭中去,当韦明贫困交加急需女儿的救命钱时,面对老鸨的劝说,韦明反驳道:“什么?你要我去出卖?只有奴隶才出卖她的身体,那不是人做的事情!
” “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虽然韦明最终还是不得不“卖”己救女,但她决不肯为钱屈就王博士。也许有人对此感到疑惑,我认为由此恰好可以看出编导赋予韦明的思考逻辑:作妓女出卖的是一夜的身体,委身王博士却是卖掉一世的自由!
鲁迅曾预言,“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⑩而绝境中的韦明,偏偏固守着自由和尊严。追求自由和独立,是五四新女性韦明在思想上所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经历了种种磨难依然苦苦挣扎的精神支柱。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韦明具备强烈的女性意识,决心成为“不倒的女性”。也许韦明仍然对心仪的男性存有爱意和些许期待,如对编辑余海涛(郑君里饰)流露出爱慕之情,但饱受了“父权”与“夫权”构成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深重压迫之后,韦明们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
电影中的几处设计颇有用意。第一处,韦明拿出了送给女儿的玩偶——一个女性的全身造型,韦明称做“不倒的女性”,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人生期许。第二处,韦明观看舞场上演出的双人舞剧:当女人遭到男人的虐待时,在众人浅薄的掌声中韦明转面不忍目睹,气愤之情溢于言表;当女性扯断捆缚在手脚上的锁链进行反抗并获得胜利时,韦明露出了欣慰解脱的笑容。
第三处,王博士请韦明去“大饭店”时,韦明反抗并斥责道:“结婚!
结婚能给我什么呢?‘终身的伴侣’!终身的奴隶罢了!”对王博士虚假的求婚,韦明不去辨别对方到底真心还是假意,感情的有无对韦明来说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婚姻对于女性已经失去正面的价值。韦明给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取名为《爱情的坟墓 》,隐约显现出曾遭放逐的知识女性所具有的更加激进的反抗精神。
总之,丰富细腻多愁善感才貌双全的女性特征,辅以平等而非奴隶的“人”的自觉和“不倒女性”的主体意识,使五四精神塑造下的新女性韦明散发着格外光彩的人格魅力。
但是,《新女性》的编导并没有让韦明得到人生的幸福,而是让“决心不倒的女性”彻底地倒下了。
推测当时中国的电影审查放映制度,编导是用了曲笔,把置韦明于死地的原因归咎于韦明生存环境的男权特征,却使电影《新女性》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女性主义色彩:韦明常处于男性色情欲望的旋涡中,作家加上“女“字小说就能出版,配上漂亮的照片更能热销,如果再有秘史、自杀等花边新闻,不但报纸连篇累牍,甚至还有热闹的追悼会!
用老鸨的话说,“这个世界,我们女人,要想弄点钱,不沾着这个,难道还有旁的路好让你走?”。男性编织了无所不在的性诱惑、性暴力、性勒索的网,令新女性韦明无法挣脱。
韦明怒斥到,“你们这班狗,设下了种种的圈套,叫我们女子不能不在各方面出卖给你们!……”韦明选择自杀,是因为她知道,这个世界决不会给追求自由的新女性一条生路的,“孩子!……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小资产阶级女性韦明短暂的人生惨遭重重打击最终毁灭,她痛苦中“救救我!”“我要活!”的泣求没能奏效。她虽然确信,“你们这天罗地网,你当永远是天经地义的?哼!总有一天……” 但她并不知道正确的女性解放之路在哪里,她对姐姐哀叹到“我实在不能活下去了……这社会,我们没有能力改造它……”。
对出走的娜拉们,鲁迅虽然也曾设想,“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但鲁迅也叹息,“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⑾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解读:韦明身上集中体现了五四时期倡扬的“独立”、“自由”、“平等”的“自由女性观”,是五四时期新女性的代表。而韦明经过种种奋斗最终自认失败,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社会实践证明,五四“新女性”和“自由女性观”已经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必然遭受社会的重创和失败的命运。
但电影《新女性》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三、李阿英:左翼革命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
1935年正是中国左翼革命文艺以及左翼电影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虽然早在20年代中期就有革命文学的倡导,但直到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才第一次成为文艺家创作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站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⑿“左联”成立不久,“左翼剧联”成立,夏衍主持下的党的电影小组加入到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等进行左翼进步电影创作。席耐芳(郑伯奇)曾代表左翼电影界宣称:“要创作出“暴露性的作品”,“赤裸裸地把现实的矛盾不合理,摆在观众的面前,使他们深刻地感觉社会变革的必要,使他们迫切地找寻自己的出路。这也是中国电影界的一条崭新的路。”⒀
30年代初期的左翼电影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反映工人、农民等受压迫阶级的苦难生活和奋起斗争的题材,而且众多的左翼电影家把目光投射到中国女性身上,以这些“奴隶的奴隶”的苦难为题材,激发起人们对黑暗腐朽的社会的憎恨。
如左翼电影开拓性的作品《三个摩登女性》(1933),以三种社会类型的女性为表现对象,小资产阶级女性周淑贞,已不再单纯进行命运的抗争,而是进一步把自己的个人追求与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女性的呐喊》(1933)通过叶莲姐妹的悲惨遭遇,写出了工人群众遭受的层层压迫;《脂粉市场》(1933)叙述了一位职业妇女的悲惨遭遇和她最后投入群众洪流中的思想觉悟。
此外,还有《前程》(1933)、《神女》(1934)、《女儿经》(1934)、《四姊妹》(1934)、《船家女》(1935)、《小玲子》(1936)等,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描绘,可以说是中国左翼电影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标志。
但真正站在女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双重角度,把对女性命运的观照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新女性》堪称左翼电影创作中最早最鲜明也最成熟的作品。
《新女性》中对王太太的批判和对韦明的悲剧命运的刻画体现了左翼革命文学“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而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新女性”——李阿英形象的初次亮相,不仅实践了左翼革命文学“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的创作要求,而且还前瞻性地演绎了中国“革命妇女观”的涵义和女性形象类型化的发展方向。
青年女工李阿英身上几乎没有了女性的特征,她穿着玄色的短衣长裤,梳着齐耳的短发,声音粗犷洪亮,办事利落快捷,性格也刚强、果决、独立。她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女性所常遇到的诸如爱情、婚姻、生计、心理等各种烦恼。
在李阿英拿着《黄浦江 》、《新女性》的歌词请韦明谱曲时,导演有意把“不倒女性”玩偶放在画面的前景,与恰在身后的李阿英形成映衬,玩偶无论在衣着、发式、形体还是色调上几乎是李阿英的翻版,这组画面内部的隐喻蒙太奇处理蕴涵着影片对真正的新女性——“不倒女性”的内涵阐释。
“被动、献身、温顺、幽雅,这四种为旧时代的作家所用力地描写,以教育陶冶他们同时代或后世的女性的,在新型的妇女是不容一些存留的了。新型的妇女不是以幸福的结婚作为浪漫史终结的纯真少女,也不是因丈夫或自己的不是而被遗弃的妇人,更不是悲叹着青春不幸独守空闺的寡妇,她是立足在职业工作的场所,经过社会人群中长久的锻炼,境域的颠沛并不能使她嗟怨,命运的嘲弄更不能使她屈服。
她有着四种基本的特质:能动、反抗、果敢、决断。这四种特质是她在生存斗争的场所中养成的。”⒁李阿英的的形象正代表了30年代进步力量对新女性的理想标准。
对待这两个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新女性,蔡楚生通过一组巧妙的对比蒙太奇镜头鲜明地表达了是非褒贬:韦明与王博士在舞场中享乐,李阿英安排着自己充实的日程表;放纵起舞中男男女女旋转轻移的皮鞋、辛苦劳作中劳动者艰难迈动的草鞋;舞场上陪着王博士跳舞的韦明,夜校里带着女工唱歌的李阿英,钟楼上大钟指针的旋转……当韦明从舞场的空虚中归来,李阿英上工去的巨大身影越发映衬出韦明的渺小。
蔡楚生对此解释道:“我们用这种象征手法,把对生活报有崇高理想和革命斗志的女工李阿英和软弱彷徨的知识妇女韦明构成一种鲜明强烈的对照”。⒂
在对比中韦明终于有所觉悟,临死前嘱咐姐姐“去找阿英姐罢!”她已隐约意识到李阿英的路应该是女性应该走的路。自杀的韦明经过抢救苏醒过来,李阿英劝导她:“个人的复仇主义自然不中用,但活着就无论如何是一切的前提”“只要再站得起来,到最后是一定会胜利的”,韦明在李阿英的身上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胜利的希望,决心 “丢开一切个人无谓的烦恼,来开始我的新生”。
影片的最后导演用了这样一组蒙太奇镜头,来表达左翼进步电影所承载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
1、(全景)夜校中李阿英走上讲台,指挥众女工们唱歌。
2、(近写)病床上韦明仿佛听到了画外的歌声,脸上浮现出激动的笑容。
3、(全景)众女工歌唱“我们去战斗!我们向前冲!新的女性——”
4、(近景)医生向余海涛和姐姐一边讲述韦明的病情一边摇头。(画外歌声)
5、(全景)众女工歌唱,“新的女性,是生产的女性大众……”
6、(近景)李阿英满怀激情地歌唱。
7、(全景)众女工歌唱,歌声由深情转为急速。 “……新的女性,要和男子们一同,翻卷起时代的暴风!”
8、(近景)韦明用力想坐起来,呼喊着“您救救我!我要活啊!我要活啊”
9、(全景)李阿英和女工歌唱,“暴风!……不做奴隶天下为公!无分男女世界大同……”
10、(近景)韦明挣扎地呼喊着:“我要活啊!”倒下。姐姐伏在韦明的身上痛哭起来。
11、(叠印)工厂厂房与火车汽笛,汽笛鸣响。
12、(特写)火车汽笛,汽笛鸣响。
13、(远景)无数的工人走出工厂。
14、(远景)汽车驶来,后景是工人们。
15、(近景)王博士和年轻漂亮的女子在车里,王博士拥抱女子,顺手把韦明自杀消息的报纸扔到车窗外。
16、(全景)女工们走在街道上。
17、(特写)女工们的脚踏在报纸上,走过。
18、(近景)李阿英与女工并肩英姿勃勃地前进,身上撒满阳光。
汽笛声、歌声和泣诉声相交织,李阿英与众工人姐妹迎着光明前进与韦明不甘的死亡相叠映,对这样的设计蔡楚生说: “为的是让许许多多的韦明感悟到只有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才能克服她们的软弱;只有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伟大行列中,才能在这些斗争的胜利中同时求得自己的解放。” ⒃
在编导看来,韦明的存在和死亡仅是小报新闻的花边材料,不久以后将随着人们扔弃的废纸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和明确的革命方向的李阿英“到最后是一定会胜利”的。由此,“新女性”的正确内涵是具备了 “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妇女。新的女性应该把个体意识转变为革命意识,把自身解放融入民族解放、阶级解放,才能同时获得妇女的彻底解放。
《新女性》的主题歌——《新的女性》(孙师毅词 聂耳曲),概括性地表达了编导对30年代新女性内涵全新的理想性想象:“新的女性,是生产的女性大众;新的女性,是社会的劳工;新的女性,是建设新社会的前锋;新的女性,要和男子们一同,翻卷起时代的暴风!暴风!我们要将它唤醒民族的迷梦!暴风!我们要将它造成女性的光荣!不做奴隶天下为公!无分男女世界大同,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
近代以来由男性知识分子和社会革命者相继探索并生成的女性观,同样获得了女性的广泛认同,如隐去女性性别特质而以阶级解放民族独立为人生目标的新女性形象,就得到了当时的女革命者女作家们的高扬:冯铿说从不把自己当作女人,谢冰莹也说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丁玲宣称我们和男性都一样,“真正的新妇女是洗掉她们唇上的胭脂,握起刃来参加进伟大革命高潮,做为一个铮铮锵锵,推进时代进展的整个集团里的一分子!
烈火中的斗士,来寻她们真正的出路!”(冯铿《一团肉》)在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中,把自身“出路”融入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的中国妇女也因此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迅速走上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男女平等之路。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为代表的一批左翼进步电影借助大众娱乐工具——电影的形式,对现代妇女命运以及妇女解放道路进行了一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探索和实践,实现了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自由女性观”到左翼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妇女观”的意识形态转变,并成为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电影实践中一座意义重大的里程碑。
注释
① 周作人:《贞操论·序》,《新青年》第4卷第5号。
②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211页。
③陈独秀:《新青年》第1卷第5号。
④转引自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作家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154页
⑤胡适:《胡适作品集》(6),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5页。
⑥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页。
⑦蔡楚生:《会客室中》,《电影•戏剧》1936年第1卷第2期。
⑧蔡楚生:《八十四日之后》,《影迷周报》1934年第1卷第1期。
⑨、⑩、⑾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161-163页。
⑿载《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
⒀席耐芳:《电影罪言——变相的电影时评》,《明星月报》第1卷第1期,1933年5月1日明星影片公司出版。
⒁金仲华:《妇女问题的各方面》,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36-37页
⒂、⒃蔡楚生:《三八节中忆〈新女性〉》,《蔡楚生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第470页、第471页。
注:本论文在2006年1月14日于汕头召开的“纪念蔡楚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并收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1月版的《蔡楚生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