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头连岳 死别的日子就在前头——摘自《我爱问连岳2》
连岳: 再次地震了。平日里碌碌的人们,也许突然因为一点点类似劫后余生的感觉,而突然醒悟究竟要的是什么,继而将这种自省延续上一阵子。那一年的9月21 日,我还在故乡,有挺强的震感,但无死伤,毕竟是隔了一个海峡。
然而那阵仗,对于当时十五六岁的我来说,足够令我兴奋和后怕。房屋轰隆隆作响中,明明线路不通的电话忽然响起。正冷战的我和她,大难临头时,破涕而笑。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怎么还记得那么清楚呢。我不完全相信记忆这回事,隐约觉得它在不知不觉中一定被我们一厢情愿地篡改着。
中间是是非非,后来我一意孤行离开故里。连分手都没有说。来到异地,决心跟过去完全断开。交男朋友,不去想她。也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其他方面,为人处世也完全不同了,并非有意。
我可以改变的只是和男人交往而非女人。浑浑噩噩过了这几年,越来越不认得自己。心里却越来越清晰地塑造了一个她,用回忆加上想象。渐渐地也不排斥和现实中的她联系,只是发发消息,不敢见面。
言辞间也拉拉扯扯过几番。 持续恶梦和不断的自杀念头,这些都阶段性地出现。在严重的时刻,我考虑过去找心理医生,不过都还暂时捱过去了。她说当年我什么也不说就消失以后,她给我写信打电话我都没有回音,她是走投无路去找过心理医生的。
治疗时医生发现她无法被催眠,只好开药。但是她没有吃,挺过来了。所以后来我再联系她时,她始终有些畏惧,是呵,一朝被蛇咬。我自己的手腕上,也有痕迹。或者可以说,这种感情,从一开始,就带给我们绝望。
那时,不是指望别人理解,是连自己都不能认同。我们也都以为,就这么远远望着,在心里的一角幻想着明知不可能的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就够了。不过我和她不同。比较早的时候,我确定我是双性恋。
她始终不认为自己和同性恋双性恋有何关联。只是,无论和男人女人在一起,我都会想她。但我也只能无奈地想,过去的,在心里就好。 然而前几天我被一个梦,吓醒我了。梦中和我缠绵的女人,没有脑袋。我猛然觉得,这么多年分开,我一直想的爱的那个人,只怕已经不是她了,是我在脑子里生生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了。
所以梦里,“她”砍了用来装饰的头颅,我的潜意识在嘲笑我。意识到自己爱的是一个虚无的人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忽然间我找不到原先赖以活下去的理由:看着爱的人在远处生活,两处沉吟。
如果我爱的人,是已经不存在的,是和现实个体分离了的,那这个理由,如何成立。 我愚钝,不能了生死之意义,走这世上一遭,若不是为了所爱的人,若是为了社会游戏中的名利骰子,我恐怕无法接受这样的理由。
需要问一个意义,才能活下去,我算是一个虚弱的人呐。 祝一切好! 沉默是美德 ———————————————————————————- 沉默是美德: 我很少在专栏中说自己的事情,一则是因为害羞;再来我认为我只是一个观点提供者,自己个人的资讯出现在文章当中,相当不专业。
今天,在经历了新年前后从地狱到天堂的心境旅程后,请允许我破个例,说一件我自己的故事。
你说到的那次地震发生之时,我和我老婆正在一购物中心吃饭,第一次震感我感觉到了,她没有感觉,我没说出来;第二次餐厅的吊灯开始摇晃,所有人都感觉到了,邻桌的两位姑娘有这样一段对话:“可能地震了!
”“不要太害怕,说不定只是因为有人乱跺脚,楼才动的!”我们照例悄悄窃笑一通。可是我的心情相当灰暗。 她由于持续低烧住院,各项检测的结果逐渐出来,都不太乐观。而医生最终的“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症)的诊断,她比我更早知道。
我到医院,刚进她病房时,还见她神情自若地在病床上开着笔记本改文件。一看到我,瞬間就情绪崩溃,哭到不行,一边含糊不清地说:“你以后一个人怎么办?” 在联系了异地最好的医院和专家之后,在出发之前,她想回我们鼓浪屿上面的家里住一晚。
经过菜市场时,她问我:“家里的煤气还有吗?”我说: “有,我昨天还用过。”于是买了一些菜。她像往常一样将菜洗净切段,打火后,煤气只烧了一两分钟就没了,而时间又过了晚上7点,岛上不再送煤气罐了。
只好用微波炉蒸了饭,从冰箱里搜刮一些干菜将就着。我们觉得白饭也挺美的,一边吃一边聊天,她先吃完后起身去收拾出行的衣物,她刚走了几步,我坐着体验到了所谓的悲伤。这个我从15岁就开始爱的女人,宽容我的鲁莽与冲动,接受我的一切缺陷,支持我两次三番赌博式的决定,她离开我,可能痛苦不仅仅等同于抽离一根肋骨,它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完全没了依托。
而我们吃的可能是最后一顿饭,却没有煤气…… 于是莫名其妙就逬出了眼泪,喉咙里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这岛屿在晚上过分安静了,而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辈子也不会掉一滴泪的坚硬之人。
我现在在病房里继续写这个专栏,说明情况已经好转了,只是需要精心治疗的病,原是一次可怕的误诊。
我原来产生的厌恶态度已经消失了——既然自己的所有能量,都不能给爱的人多一分钟,那么世界变得如何,爱情会如何演变,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愿说自己的事情不让你烦,我已尽量克制。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就算和一个人相爱了二十多年,这也不会让人觉得足够,与相爱一个小时的长度相若 ——当然这只有在你觉得要真正离开的时候才感觉得到。也许活到一百岁,真正要离开时,还是会像这样觉得孤单。
我现在很庆幸在二十来年当中,我强横、霸道地不理会别人的看法,只过着我们想过的生活,爱一个人就是为她而活,背叛世界也无所谓的,因为到了今天,我才知道,就算这样也会觉得时间不够,死别的日子就在前头。 祝开心。 连岳 2007年1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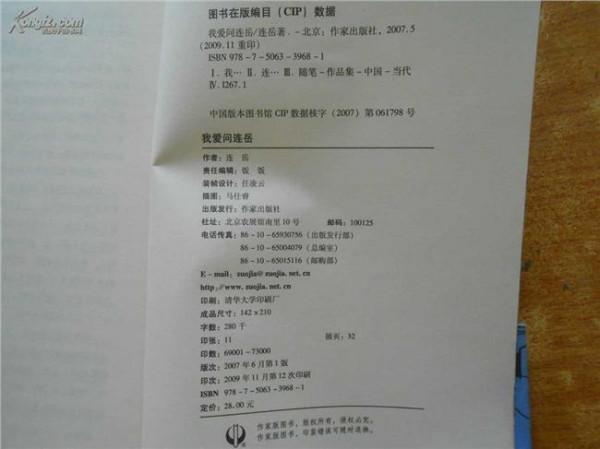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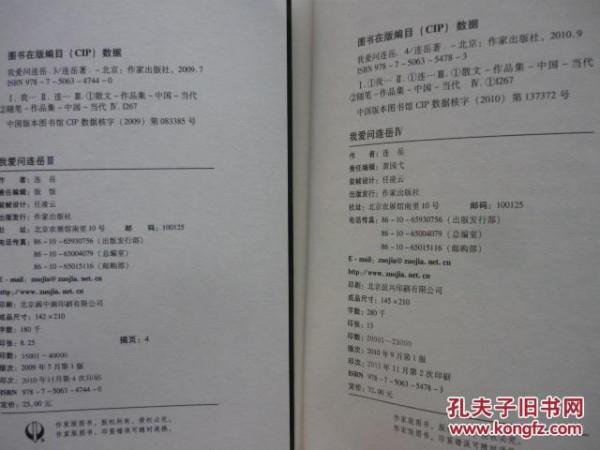
![>《我爱问连岳Ⅱ》(连岳)扫描版[PDF]](https://pic.bilezu.com/upload/b/c1/bc1953061aa71cc43da3d9d38923da0a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