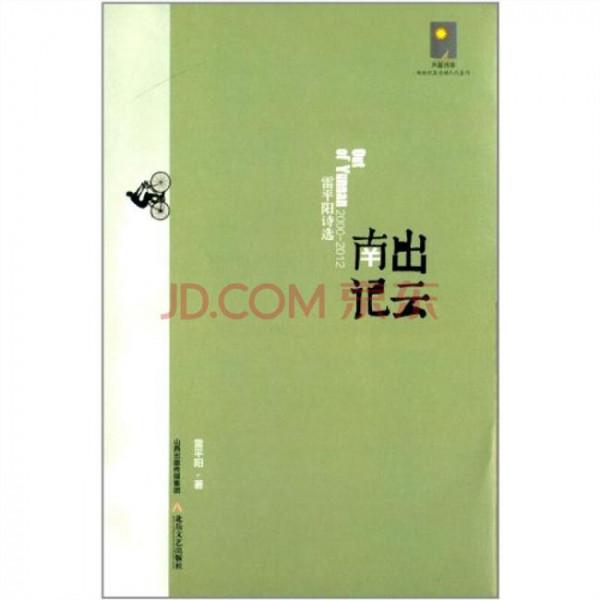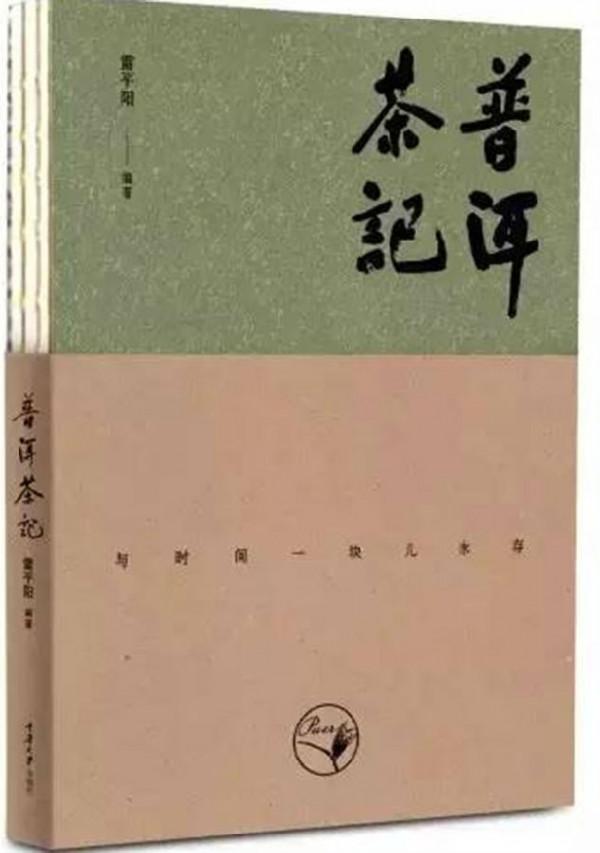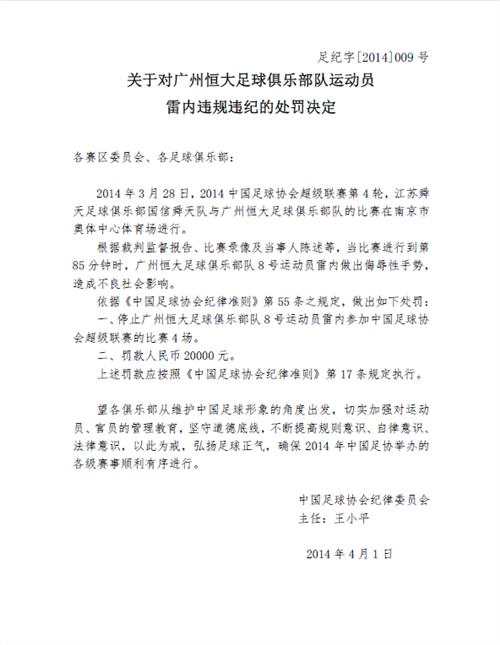重生雷平阳 诗是经验的生长——读雷平阳《云南记》
雷平阳《云南记》中的诗作,有一部分是我在过去的阅读中零散地读过的;这次,我收到这部诗集后,用十余天的时间断续地读完。合上这部诗集就感叹“诗是经验的生长”。当然,这个经验是诗人的生命经验和创作经验。虽然,这本诗集的作品大多反映的是诗人生活所在地的“云南经验”,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诗人其诗作大量地使用了某一地域元素,就界定该诗人是只能写某地域或有地域归属的诗人。
云南之地是诗人的生活之地,亦是生存之地;这个“云南”与“山东”“河北”等地是诗人的生活、生存之地并无差异。至少“地域元素”、“云南经验”没对我的阅读构成什么障碍。
在这本诗集中,我看到了诗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看到了诗人对日常生活谦卑的细腻体察与敏感;看到了客观事物一旦出现在诗人笔下,就立刻是主观的,就会显示着诗人内心深处被重重遮蔽的隐秘。因此,我在读《云南记》中的每一首诗时,都会很轻易地被诗人带入他真实的感情与真切的现实里。
在我读完《在坟场上寻找故乡》时,曾哑言半晌。不是失语,而是突然面对阔大无边的漠野和死寂的惊愕。诗中,诗人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又是那么的坚定。
这首短诗,让我想到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该怎样去做一个幸存者;该怎样去发现一缕阳光、些许愉快以及坚定生存下去的决心。诗中的主体以个体形象“我”出现时,呈现着一种遗世独立的孤绝的姿态,“我”与世界的关系既是疏离的也是对立的。“我”感受着外部世界的巨大敌意,甚至伤害,其内心装着落寞、困顿与犹豫。他一方面表现出个体的抵抗,一方面表现出对生存条件的依赖,“拨开草丛,踉踉跄跄地寻找故乡”。
我一直质疑“诗意的时代”这样的说法。时代是当下的存在,是现实。现实中有真相、假相。时代是否有诗意,是人在现实生活里的精神状态。雷平阳没对时代引吭高歌,也没有刻意对时代挖苦。雷平阳是个不屑于表现世俗乐趣的诗人,这也就注定了他必然要与现实生活对峙,他的诗歌创作不仅需要他有鲜明的立场还需要有文化道德。
以他的《回乡偶书》(一至五)为例,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良心负担和歉疚感。这五节短诗看上去是叙家事,可稍一沉淀,就“赖城市所赐,很多人,都没有扛住/无孔不入的降服,患上了梅毒和淋病,身体里那本/邪恶的《传播学》,令人不寒而栗”。
很多年以来,一直有人在讨论诗歌的“纯粹”与“现实”的问题,当然是在讨论诗人的内心情感与外部世界的问题,诗人的生活是来在内心还是来自客观事物?我至今还没看到脱离现实而纯粹的诗。当然,任何一首诗中所呈现的现实,也绝不是“完全的现实”,诗人手中的笔不是照相机。诗是主观的,诗人先想象自己,再围绕那个想象来营造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现实”。雷平阳诗中的“现实”,都是他经历的也是他营造的。
雷平阳在白描现实时,是湛然而透彻的,是带着敏感体温的柔和色调。他在使用修辞和意象时,又常常带有冷峻而深刻的力量。他的长诗《春风咒》,就是一个代表。
我不能下定义一般地说雷平阳具有如何强大的超越性的想象力,但我可以说雷平阳具有整合文化的特殊才能,或者是让感官和思想有力结合的才能。读他的诗作,没有任何“门槛”,简朴的语言,惯常的事物及场景,看两眼很容易就亲切起来,而读过几行、几节后,他的“感官”就把你带到他思想的深邃处。然后,就是读后的“反刍”。诗歌的力量往往就在这“反刍”里。
我对《云南记》的反刍是:雷平阳是个严谨的诗人,其严谨表现在对他对语言和生活的伦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