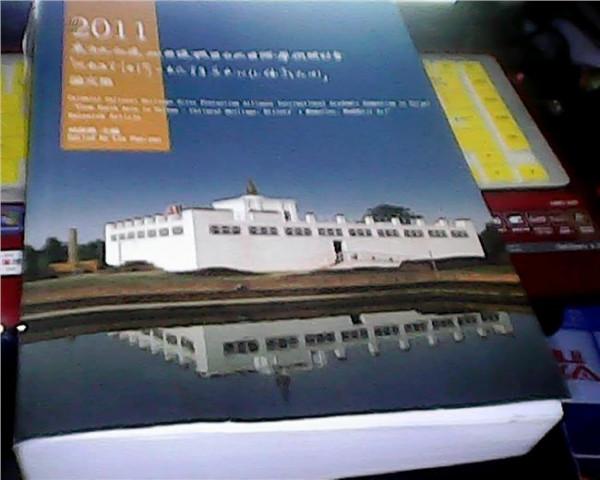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閒來翻書(九十六):陸揚《清流文化與唐帝國》
“2016,中古史研究的陸揚元年”,宣傳中如是寫到。這是從榮新江教授前些年的評價轉化來的,當年,榮教授說“今後若干年的中古史研究,將是一個‘陸揚的時代’。” 這真是好大的口氣!好高的評價!雖說上師(最初知道的往復的雲中君,今則多以微博名呼之)未必肯如此自視,但內心或以此自期,而學術,當然要有這樣的氣魄!
達不達到則是另一個問題。此亦如孔孟所言,不可以聖人自居,而不可不以聖人自期。 說上師有此氣魄,從他討論的主題即可看出。
在新文化史、醫療史等等日益甚囂塵上之際,他的關注點返回到了,或者更應該說,是始終集中於“政治史”——當然,此“政治史”早已超越了當年,可以說是結合了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等的“政治文化史”。
這無疑是理解傳統中國最爲重要的面相。何炳棣一直強調要做第一流的題目,這就是!那些總是聚焦於新奇、邊緣的研究者,即使可以做得非常成功,卻永遠無法成爲一流的歷史學家。 在集中於政治史之上,上師更要突破陳寅恪等舊有的對中晚唐政治結構與文化等的解釋框架,提供一個全新的、在他看來“更”具有信服力的解剖視角與闡釋體系。
所謂“制度化皇帝權威爲核心的新政治秩序”,便是作者的“新”解釋。這裡,他所更爲強調的,是“皇帝權威”,而不是“皇帝權力”,即皇帝本身在政治結構之中的位置所體現的象征性意義。
這也就是在強調不同於“私人性皇權”的“制度性皇權”,仍然有其重要性及合理性。不過,指出這一點似乎沒有什麼新奇之處。
雖然沒有詳細地梳理研究史,但印象中許多民國學者都有這種認識,只不過很多也並沒有去特意強調,因為在那一代學者眼中,有些常識是不需要提的。 對於墓誌史料的應用當然是本書在材料上的一大亮點,尤其是有些文章幾乎完全建基於數方墓誌而闡發一個大問題。
但更爲重要的是,他對於其所強調的史料書寫的“修辭學”色彩、言外之意等的理解與抉發。作者善於在歷史記述的細節隱微之中,輔以豐富而又常常是合理的想象力,勾勒出“隱匿”甚至“消失”在以往歷史記憶之中的另一種歷史的真實。
這奠基於作者對於時代宏觀把握的深度,並不是輕易做得到的。書中最初幾篇,讀下來的感受,是仿佛看到了徐高阮《山濤論》的影子。鄙意以爲,《山濤論》應該作爲歷史學專業學習研究方法的基本教材。
上師雖然自述本書是兩部仍待完成專著的略縮版,其中對於某些問題之研究的缺失似乎可以理解,但是,就本書所呈現出來的內容來看,竊以爲,有些問題,儘管也在他的關注視野之中,但卻似乎被排斥於其所構造的宏觀架構之外。
個人最爲關心的,是中晚唐之思想變遷問題,在他的解釋體系中居於何種位置。書中曾提到,清流文化與古文運動或文學復古,即使常常是同樣一批人物,卻並非同一潮流的不同面相,會在不同的社會圈和實踐中採取不同的立場,傳遞不同的聲音,代表不同的身份(頁241)。
在我看來,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說法。涵蓋整個中晚唐的核心政治文化,與中晚唐最爲重要的思想變遷,竟然完全無關,參與其中的人竟然也像人格分裂一樣,表現著完全的不同,難道是正常的麼? 書中有些地方,似有推論過度之嫌。
如僖宗時鄭從讜開府,所擇皆“一時選”,此《新唐書》明言此在“言得才多也”,即指從讜所擇者,有才學,有時望。
而書中申論在京師士人眼中,這種“一時選”是利用一流人才化解危機的正確手段,即強調清流人士之重要作用,此即不知從何推論而來?又朱溫擧張廷範爲太常卿,是故意向清流文化核心價值挑戰的一種信號,而裴樞恰恰捕捉到了,其反對則意在維護自身清流領袖的政治資源,守住這道防線。
對於朱溫與裴樞究竟是否有這樣明確的意識,此處的解釋僅能說是猜測。 在論述清流文化時,上師指出,其核心成員以翰林學士等詞臣爲重要身份象徵。
那麼,這些詞臣在當時的政治架構中究竟居於何種地位?唐代的情況不太了解,宋初的情形,一則上師已引,即宋太宗所謂“一佛出世”之語,詞臣仍舊得到非常高的評價與重視。但這是否即代表著清流文化的延續,不無疑問。
《續長編》曾記載,“(蘇)易簡數振舉翰林中故事,前為承旨時,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見上,不復有欵解之意,但嚴顏色責吏事而已”。此即表現出宋太宗對於不同職位的待遇差別,其榮寵則僅限於學士。對學士本身的優待,能否即代表著對其所代表的清流文化的尊重呢?若如上師所言,從詞臣到宰輔,是清流文化下的正常升遷途徑的話,清流文化下的士大夫及其影響力,就不應限於詞臣的身份。
這裡,或許也需要在更爲寬廣的視閾中予以考察。 2016年3月草,5月6日稍作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