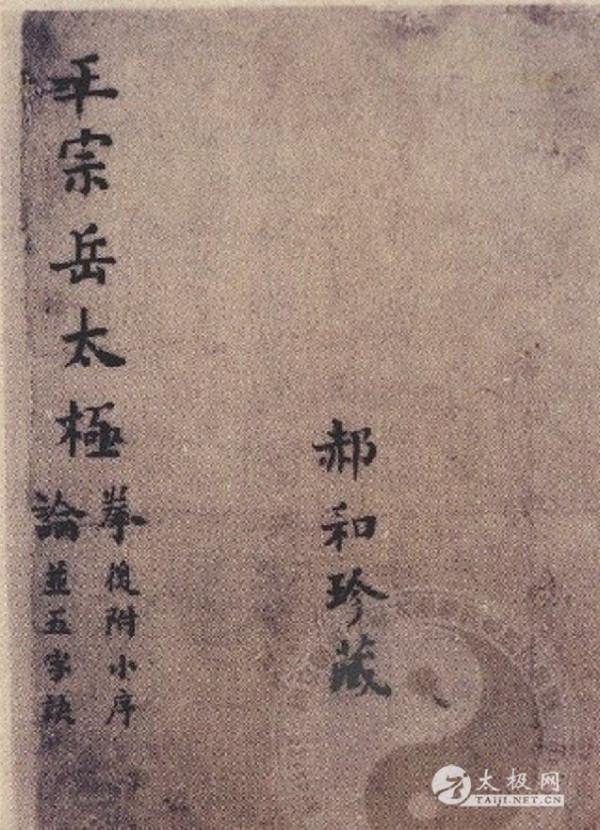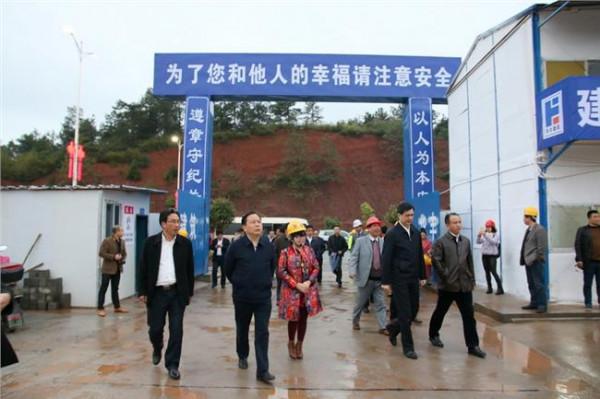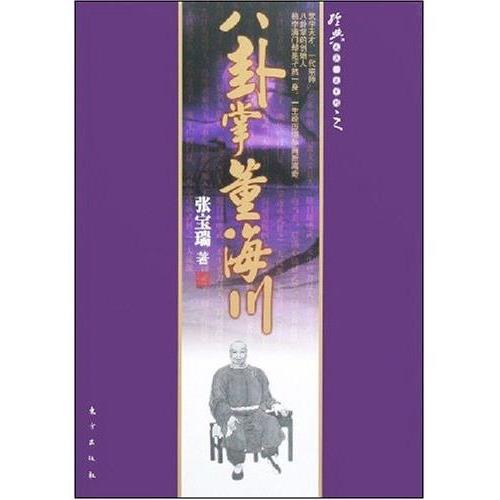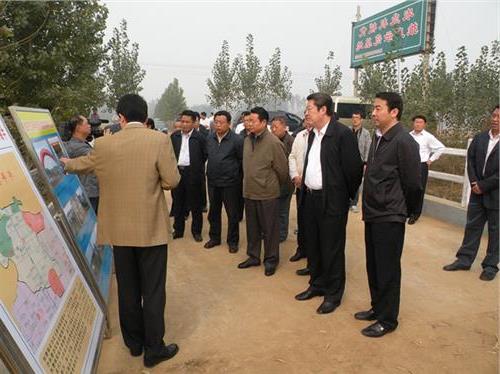雷海宗历史的碎片 雷海宗 历史的碎片
雷海宗 历史的碎片 雷海宗人生的三个碎片,被他的学生记录如下: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
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这是1962年春,雷海宗在南开大学重上讲台。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
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这是1932年,雷海宗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当时的学生刊物《清华周刊》上“教授印象记”描绘的形象。
——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做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也听不清讲些什么。
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这是1957年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后,为了对新生进行阶级教育,学校安排新生旁听批判雷海宗的大会。
从1932年到1962年,一位学者的人生在1957年被划断。 雷夫人记得,1957年夏,天津市召开“反右”大会,会上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很沉痛地对夫人说,“对不起你。
”次日,他突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我俩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历史系叫他作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
等到雷海宗摘掉“右派”帽子后,系里纷纷来人,对他说,这门课无人教,那门课无人讲,“恨不得他成为孙大圣。”1962年春,患慢性肾炎已3年,严重贫血,乃至全身浮肿、步履艰难的雷先生,坐三轮车来到教室,重上讲台。
史学大家何炳棣上世纪30年代求学于清华历史系。他认为,由于近20年来学界对陈寅恪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但“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
当时蒋廷黻担任系主任。他采取的革新措施之首就是聘请雷海宗回母校主持“中国通史”这门基础课程。雷海宗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即开始以文化形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
因此,何炳棣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显然更加多元。“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
” 雷海宗开启了史学界的风气,堪称一代宗师。然而后世研究者看得很明白:他的学术观念和思想,与后来取得学术话语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左。“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资产阶级史学权威,在解放前就曾以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违的文化史观闻名于世。
虽然,解放后的雷海宗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觉得找到了真理,发现了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但在当道者眼中他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必须清算。
” 他在1957年的遭遇,被后人称为“蒙难”。当权者甚至拟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批判计划”,“以批判雷海宗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重点,一共十五项题目。
”“披着史学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苏反共政治经验的老牌右派分子”等罪名不断袭来,温文尔雅的雷教授终于声嘶力竭地承认“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2002年,雷海宗诞辰100周年之际,南开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但有观察者感到遗憾:现在的纪念者大多也是当年历史的亲历者,读他们的回忆文章,还是感觉有些史实较为晦涩,不提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