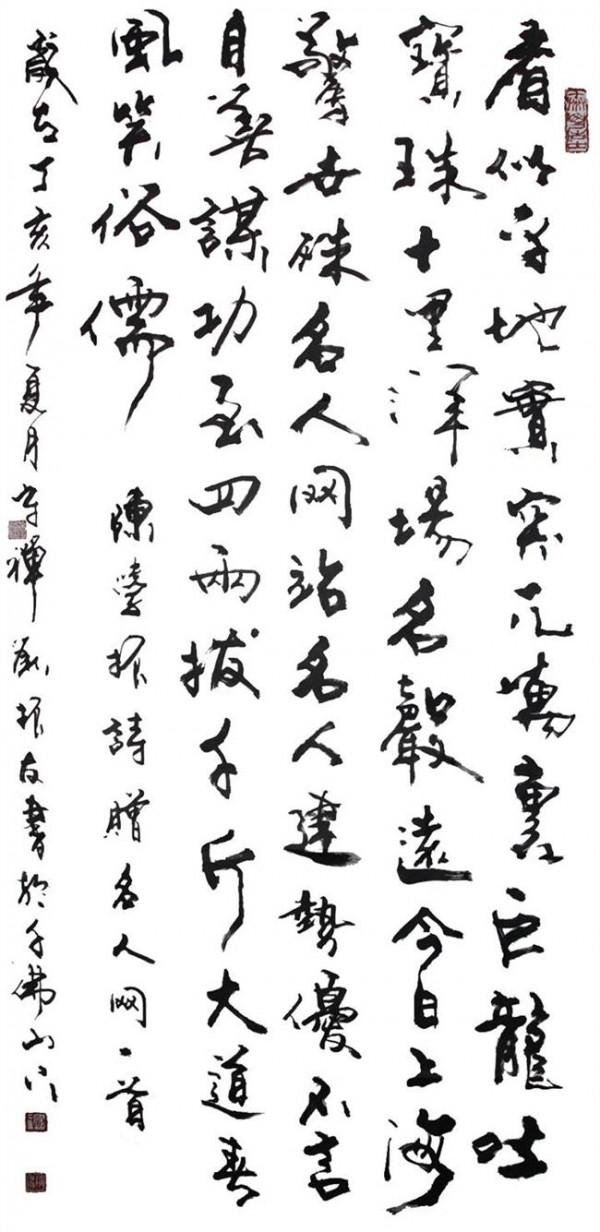段正渠的油画卖 旺火:段正渠的油画艺术
看人作画如观人洗澡,一个正襟危坐,一个一丝不挂。你洗吧,我看着。他不愿意,拿工作需要威胁,放点音乐哄着,不为听只让他尽快安静。他半推半就侧对着我,点支烟,把跨从左边送出去,左手托住右肘子往跨尖上斜斜的一支,下巴一升,嘴唇做个地包天,‘扑’的一口烟吹上去把面目迷离了,手臂带着烟卷顺势探去软软的像伸出个鸭颈。
大姆与二姆揉一下烟屁,中指在烟腰上一弹,整个手臂像只长脖鸭子被优雅的噎了一下。然后迅猛的将烟头摁进马利牌丙稀盒做的烟缸,挤出来七八个旧烟头,同时另只手就抓住了刷子。
其实,我看过不少人作画,相同的地方都不好看,不同处都好看。尽管有时‘很丑’。 正渠笔一上手就呡紧嘴巴、再呡紧、更紧,似在为谁保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死也不能说,不是不想说。
‘说破天,最终要看画’他不画画的时候这样说。画画时,我看到他最显著的是那双手。一戳一挪横扫竖刮,像是与那片麻布搏斗。更像拿自己的肉身打磨一面石崖,三合一的调色油从手背流向臂弯,一条一条的流,不管什麽颜色都像大红一样的壮烈。
肢体无限的变换,唯一的约束就是那衣服本身。看来洗澡之说不仅贴切更带些实用。‘绝对的自由纯粹扯淡,瞎胡弄。’不画画时他这样说。一旦开画,整个身子不是猫着就是探着,好像那画布上有一只四处飞纵的萤火虫,捉住一个又一个,总也捉不完。
累了,回过身给我一颗烟自己一颗烟,打火机在我眼前一晃而过,点着了自己的我的没点着。这人平常很懂礼数的。‘画画的时候,师在于我,不在于他’不画画时他也这样说…… 撇开人看画画。
阔笔涂抹,气息酣畅。表情与性格不仅留存与面容,扳船的方手上有、卷起的浪尖上有、陷入黄泥的大脚板上有… 一条线便是一曲完整的色彩笔锋的交响。
粗砺处有层叠的细腻、纯净饱满的色泽、力道丰沛的行笔;生熟褐黑调制出稳重瑰丽的灰色调,结实通透; 文字太难形容这挥洒淋漓的观看。 以往在抽象画家那里看到的那种突出的秩序和节奏,竟然被他那么妥帖的不露声色的表现着,却不着一痕。
决绝肯定中时时处处有逸动,严谨浓密里自自然然的拆出一撇‘不合适’。没有玄技,材料本分,平常手段,只有十足的快感――愉悦的快感。 他之与快感几近贪得无厌,用他自己的话说――‘过瘾!
’ 正渠手快但瘾大,一张画一遍一遍的画,每遍都很薄最后却很厚,厚的不是颜料――是痕迹。用‘痕迹’要将边缘丰满、将物体凿塑,非得经过一遍一遍的去、留方始成为可能。更要依‘痕迹’使画面得到烘托、甚至强调,其心力将百倍与直笔描画。
恁有如何超凡的功力、多么高深的‘笔墨’旨趣,最终,都严格的服从于内容。做到这一点,一赖于他的情智,二赖于他不自觉的对那‘快感’的强烈渴望以及因渴望而激发的冲动。内容就在这快感之下,一丁不剩的转化为,‘一眼看去’的那张画。
看他做画是件痛快的事,就像听陕北民歌;观他的画是件幸福的事,就像喝了北方烧; 看完之后要去说画,那就十分麻烦了,用正渠的口头禅解决这个麻烦就一句:‘去球,有啥说的。
’ 是呀,即便真有一只七十公斤的巧嘴八哥,又怎对那四百众的油画作品下嘴呢。我宁愿将自己比做那个三尺长的黑嘴护法――乌鸦。他也满世界飞,‘大长了见识’,却也像哪钢铁的火车一样,没使自己变白。但至少他在哪个窗口沐浴过一次光照。就将这聒噪的文字权做又一茬浅薄的风,只为着吹开些艺术的蒙尘,好呈现大家对哪人希翼的新景吧。 0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