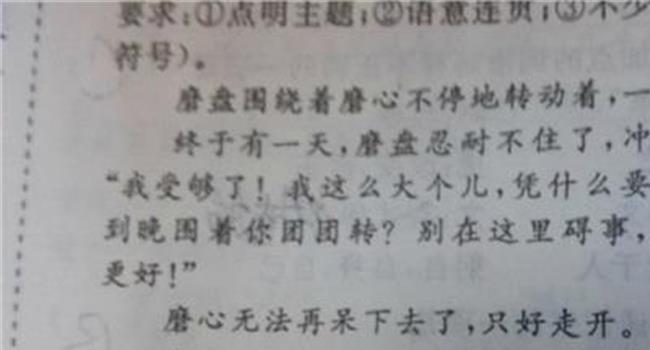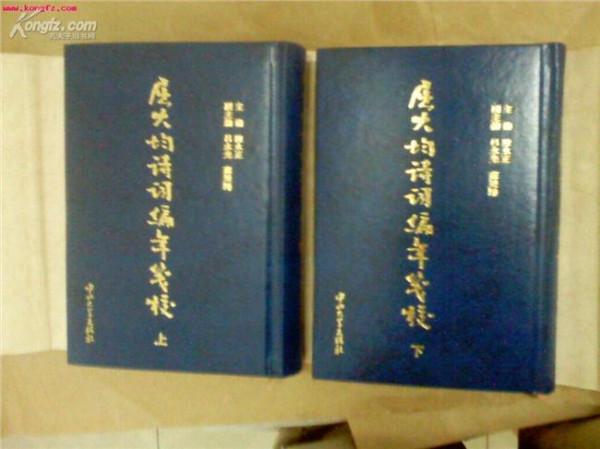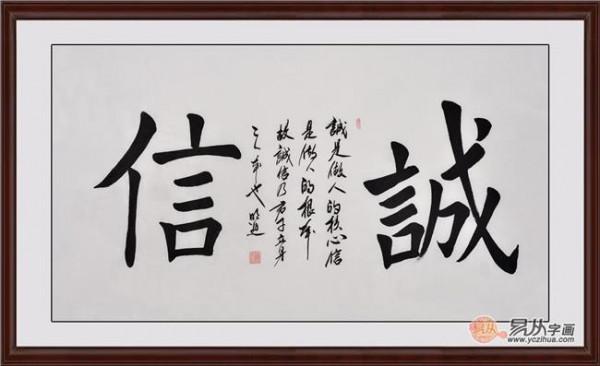屈大均诗词 清代的诗人和诗词
清代诗词数量浩繁,作者队伍庞大,流派众多。仅晚清徐世昌辑的《晚晴簃诗汇》就收录诗人六千一百余家,超过《全唐诗》二千二百余家的两倍。词的方面,据《全清词抄》收录四千余家,比《全宋词》收录的一千三百余家多三倍。
读清人诗,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清初和晚清时期的诗歌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较高的艺术价值,评价也高,但对于中期却往往评价不高。这一时期诗歌量大,可谓洋洋大观。但内容多平庸空泛,格调“肤廓浮滑”、“无创新意”,给人一种风骨衰微的印象,而此时恰恰为康雍乾盛世。
清诗这种发展情状诗评家谓之“马鞍形”。这也是有原因的。清初,正当沧桑变革,国内民族矛盾尖锐。一大批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诗人,写了不少表现民族大义、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使清初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闪耀出以诗歌为武器参与民族矛盾斗争的战斗光芒。
其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和作品,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屈大均、钱谦益等,其作品质朴浑厚,激越苍凉。吴伟业创造“梅村体’,与钱谦益同称一代诗史。这一时期产生的大量优秀诗篇,有力地转变了元明以来衰颓的诗风,形清诗马鞍形的前一个高峰。
为什么康雍乾盛世,值得称道的好诗反而少了呢?应该说这与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和禁书毁版的思想文化禁锢政策大有关系。康熙初期还有平定“三藩”的武事,但到了后期,转向对全国文化思想方面监控。到了雍、乾时间则全心全力于钳辖文化,控制思想,大兴文字狱。
有论者说:“无论就时间之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来看,都是没有先例的”(见周宗奇《血光之灾——清代文字狱纪实》)其特点是禁书毁版与文字狱并行。那时结合编纂四库全书,“以征代禁”收缴大量民间书籍,有的加以毁禁或作篡改。
据史家考证,这一时期“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版八万块以上。”至于民间由于惧祸而自毁的书籍则不计其数了。不仅如此,清廷还在一些重点地区建立“观风整俗”使,加强社会监控,形成严密的监视网。
“一狱兴起,遍查各地。从藏书富家到地方书肆,从案犯内宅到旅人行箧,莫不为查禁之对象。”一案牵连人数多者一百余人。以至“民间告讦之风盛炽,士习民风败坏”(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
康雍时期享誉诗坛的著名诗人查慎行,本名查嗣琏,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八年因为在皇后佟佳氏丧期观看洪昇《长生殿》首次演出而被撤职。和他一起观看的几十位官员、名士包括其友赵执信和作者烘昇均被削籍归里,查为警励自己而改名慎行,号梅馀。
他在为赵执信送行的诗里写道:“荆高市上重相见,摇手休呼旧姓名。”荆、高,即指荆轲和高渐离。可以想见当时诗人、学者们是怎样一种小心翼翼“颤抖”的心态。然而,就是这位“慎行”先生最后仍未能逃脱皇帝的“文网”。
雍正四年,他的三弟查嗣庭在赴江西任乡试主考官时出事了。原来,按一般乡试,考生要经三场考试。这次,第二场二题为“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四题为“百定盈止,妇子宁止”。雍正知道后就联系起前时汪景祺《历代年号论》文章案。
由于汪在文章中指出,“正”字有“一止之象”。并举例说凡是以此为年号的帝王大都不吉利,没有好下场。为此汪被雍正杀了头。雍正以为查嗣庭出的考题,前题点出“正”,后题点出“止”,是有意为之,实属大逆不道。
为罗致罪名,还说查是刚被整掉的隆科多的“死党”,又从抄出的日记中发现他对康熙皇帝的“用人行政”多有“攻击”。三罪并处判以“凌迟”极刑。查嗣庭时已62岁,早在他从江西主考任上回京,不到三天,就被抄家逮捕,入狱后不到半年即含冤而死了。
但人死了罪不能免,仍“戮尸枭示”。他的大儿子被判斩监候,另一个儿子病死狱中,还有两个不足15岁的小儿子均被流放三千里以外。当大哥的查慎行这次又受到株连,以“坐家长失教”罪而“放归回里”,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
其二弟查嗣王栗,亦康熙时进士,有诗名,遭“谪遣关西”,后死在“戍所”。他们的子女也都被戍三千里之外。可怜查家一门四进士除四弟早年“过续”出门,未遭此难,其余三家两代人,家破人亡,均未幸免。查家的全部财产充为修筑海塘工程的资金。
再举曾久为乾隆皇帝赏识的大诗人沈德潜为例,据《清史稿》记载,在乾隆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讦举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乾隆发现在该集前面有沈德潜写的传,有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的话,惹恼了皇帝。沈德潜此时已死去十年了,但乾隆仍没有放过他,竟“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基碑”。
清廷的文化高压政策,杀一儆百,使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学术自由受到极大禁束,造成残酷的精神迫害。乾嘉时期被誉为“青莲再世”的诗人张问陶,在一个风雨之夜喊出自己心灵的独白:“百年身世一浮萍,几盏醇醪养性灵。读罢离骚还痛饮,不妨我醉众人醒。
”在另一首《盛事》写道:“无灾无难不公卿,才算平安过一生。细领痴聋真妙处,始知愚鲁最聪明。”还有年轻诗人黄景仁那首无可奈何的心灵调侃:“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漂尽悲秋气,泥絮沾束薄悻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青鸟秋虫自作声。”这种饱受精神压抑的内心世界,正是在“盛世”光环下一些有才华诗人心态的真实写照!后来,道光五年(1825)龚自珍以《咏史》为题,对当时“万马齐暗”的现状发出了撕肝裂胆的呼唤:“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诗中前两句已为许多人引用过,其实后面两句更深刻地表达了他对文字狱严重摧残文人学士心灵的义愤。他仰天长啸,问齐国田横的五百义士哪里去了,难道都被封官列侯了吗?
清代重视汉文化,从康熙开始倡导经学。他说:“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后来在乾嘉时期形成颇著名声的乾嘉学派,或称乾嘉考据学,广泛涉猎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包括儒家的经典经、史、子、集乃至天文、舆地、历算、文字、音韵等多方面的研究考据,成为有清一代的主导学术,对清代诗坛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实际上,乾嘉学派与清代历朝的诗人群都有密切渊源的关系,也可以说历朝的学者群与诗人群,只是从各有侧重来区分。像顾炎武一般认为是清代经学的开山大师,但也有名诗传世;钱谦益是清代早期诗坛领袖,同时也是位考据学者。
乾隆中期进一步对科考制度进行变革,除首场“四书”文不变外,把经文列为二场,并增加“八言八韵律诗”的科考。经学与诗学成为科考取士的必备科目,不懂经学或不会做诗就不可能中举考进士。因此,清代的诗人兼学者和学者兼诗人的情况比较普遍。
除顾炎武、钱谦益外,在宣南居住过的除诗人外也兼学者的还有施闰章、彭羡门、王士禛、朱彝尊、袁枚、赵翼、张惠言、程恩泽、龚自珍等等,不胜枚举。这种诗人学者化现象对清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一方面,提高了诗人的学术文化层次,扩大了诗人的知识视野,开拓了诗歌的境界。尤其清初学者倡导经世致用,直面人生;乾嘉学者讲究考古知今,“抱经世之才,治以富民为本”(时人评戴震语);在学风上朴实勤勉,困厄不辍,不图荣利等,都推动了“诗教”广布宏扬。
即使在康雍乾盛世的文化专制下,一些诗人关心百姓疾苦,反映世道人心,褒贬吏治民风,直抒个人胸臆的作品,仍不绝于书,折射出我国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诗歌文化传统的光辉。
另一方面,由于清廷长期的思想禁锢政策,大兴文字狱等,给清代诗坛带来严重消极影响。其直接后果就是大多数诗歌作品不敢揭露社会矛盾,不敢批评时政,不敢自由表达个人意愿,只能按皇权意愿,或歌功颂德,或模山范水。
不少有才华的诗人,躲进古文献中,将“故纸堆”当做“安全港”。最典型的有洪亮吉,他是乾隆进土,授编修。他的诗文富有奇气,才华出众,与黄景仁齐名,为江左名诗人。嘉庆时因上书皇帝语多过激,对皇帝大不敬,被贬戍伊犁。后得赦还家,改号为“更生斋居士”,潜心研读经史。正如他的老友张问陶所云:“全焚诗笔留心血,重制儒衣想泪痕”。后与著名学者孙星衍论学相长,世称“孙洪”,在经学研究上颇有成就。
乾隆时期,与大兴考据的同时,在诗坛内部,出现了沈德潜的“格调”说与翁方纲的“肌理”说,更助长了诗歌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蔓延和发展。如沈德潜强调诗的音律节奏,结构对偶,把“格式声调”看成写好诗的关键,将“温柔敦厚”作为诗的原则。
翁方钢在《志言集》序中说:“为学必以考据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所谓“肌理”即是义理和文理。这样,在诗风上一味拟古,出现“学问诗”、“考据诗”,把引经据典,作为诗学时尚。在语言上晦涩板滞,读起来懵懂不明,或枯燥无味,所谓“雅文镂彩太纷然,开卷沉沉我欲眠”(张问陶句)。
严重影响了诗歌作为励志怡情的形象艺术的光彩。实际上,当时袁枚就批评过那种“误把抄书当作诗”的现象,张问陶也强调“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饾饤古人书”,“模宋归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
晚清诗人张际亮也明确指出“或以议论考订为诗,或则轻佻浅鄙,无与于风雅之旨”。然而,“天教伪体领风花”(龚自珍句),这种消极影响成了康雍乾盛世诗歌的“硬伤”,使当时诗词的质量处于一个颇为平庸的低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竹枝词作为一种由民歌演化过来的诗体,在康熙年间诗坛领袖王士礻真的倡导下,得到了广泛发展。钱大昕说“王贻上(士礻真字)仿其体,一时争效之”。乾嘉以后,作者日众,许多中小官吏、知识分子,纷纷拿起笔来,以竹枝为体,用通俗的语言、清新的笔调写出大量竹枝词。
宣南地区自然成为作者的“大本营”。无论是反映社会生活,记述历史事变,描摹人间苦乐,大都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与诗歌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八股调毫无共同之处,给当时令人窒息的诗坛吹进一股股清鲜的空气,使人耳目一新。
晚清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举起“诗界革命”的旗帜,提倡“我手写我口”,他写的二百首《日本杂事诗》和八十九首《已亥杂诗》都是竹枝体诗歌,对当时的诗坛影响很大。
清代,到了嘉道时期,正处在走向下坡的历史转变期。内则国库匮乏,国祚日衰,灾害频仍,民生凋敝;外则帝国主义列强入侵,鸦片大量输入。严重的内忧外患,使清廷疲于应付,苟延残喘,对知识分子文化思想禁锢政策有所放松。
众多仁人志士从埋头考据的学风中纷纷走了出来,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国计民生,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真是“九州生气恃风雷”,宣南成为众多文人士子结社、修禊、酬唱、吟啸之地。龚自珍,作为这一时期出现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的代表人物。
他的诗文以磅礴的气势,强烈的爱国热情,深刻揭露和抨击清王朝的黑暗与腐败,呼唤变法改革。他的诗瑰丽奇伟,大歌大哭,打破嘉道诗坛的一潭死水,唤起新一代诗风的兴起,使清诗走向马鞍形的后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