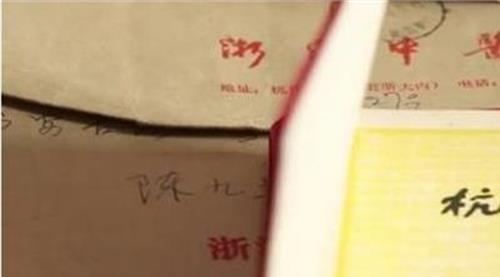“人”这个字何其难写——我与诗人张志民的交往经历
“人”这个字何其难写
——我与诗人张志民的交往经历
□郁葱
熟悉诗人张志民先生的人,一定会记得他的《死不着》、《社里的人物》、《祖国,我对你说》等名篇,我小的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当代叙事诗就是张志民的《死不着》、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和闻捷的《复仇的火焰》。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正值“文革”时期,这些书都被封存了,还是图书馆的一个阿姨从书库中偷偷翻出来给我看的。70年代中期我开始写诗,以后又做编辑,与我曾经敬重的大师们开始有了联系,接触多了,我对张志民先生的评价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一个真正的好诗人。
张志民先生是宛平人,宛平曾经是河北省的一个县,后来划归了北京丰台区,但每次我向他约稿,志民先生寄来的简历都注明“张志民,河北宛平人”。而且几次见面时他都对我说:“我是河北人,老家是河北。”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另一位现居住北京的河北籍的“著名作家”,前一段电视台采访,记者问他:“您长期生活在北京,那您觉得自己是北京人还是河北人?”那位“著名作家”犹犹豫豫地说:“应该算是北京人吧。”其窘态让别人都觉得尴尬。我不是说人家这么说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但我知道,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是应该把祖籍的那捧土看得很重的。看那段采访时我想起了志民先生,更多了对他朴素、真诚人格的敬佩。
张志民先生正直忠厚,处事低调。大概真正有内蕴的诗人都是这样,与这样的长者交往心里踏实、充实。《诗神》编辑部几任主编戴砚田、旭宇和我都与张志民先生交往甚密,《诗神》创刊号的第一组诗便是张志民先生的组诗“大西南”。我曾经多次跟张志民先生约稿,许多名家的稿子编辑部都是不能改的,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但志民先生寄稿时总是注明“删削随意”。有一次我在电话中对他说,他的诗作有作者写了评论,我们想发出去,志民先生赶忙说:“可不要,刚发了我的诗,别再占刊物的版面了。就寄给我吧,我自己看看,给人家回个信就行了。”其内敛和大度让人感慨不已。
1989年7月《诗神》编辑部在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举办“昌黎酒神杯全国新诗大奖赛”颁奖,请张志民夫妇来参加颁奖仪式,颁奖结束后买返程车票,先生的夫人来找我,问我车票买了没有,我说:“阿姨您放心,已经订好了软席车票,我现在就去拿。”阿姨对我说:“郁葱,我就是想跟你说,不要买软席,买硬座,我们跟大家坐在一起回去,行吗?”我说:“按志民老师的资历,应该坐软席的。”(当时张志民先生是《诗刊》主编,而且我记得好像志民先生是享受副部级待遇。)阿姨坚持说:“不要了,他说的就买硬座,也省得给你们添麻烦。”
后来,张志民夫妇还是坐硬座回的北京。
1993年的时候,《诗神》编辑部策划了一个栏目“纵论中国当代新诗”,我出了几个题目请张志民先生和其他诗人回答,他特别赞同宽松的文化氛围,他说:“如果没有宽松的形势,就没有今天的繁荣。”当时《诗神》的办刊风格就比较超前,他很认同,特别主张创作上和办刊物上要体现个性。我在回答《诗神》编辑部的五个问题中也提到:“很赞同张志民老师的观点:文学界不应该仅仅是阵地。垒一个阵地或挖一个战壕和谁‘对峙’?火药味总不是个好味道。”张志民先生对探索、对先锋精神的宽容,对我策划的刊物风格的理解,一直让我深深感动。
了解张志民先生的人也许会记得他的许多名篇,但他的一首题为《“人”这个字》的诗我却记得更深:
听书法家说:
书道之深,着实莫测!
历代的权贵们
为着装点门面
都喜欢弄点文墨附庸风雅,
他们花一辈子功夫
把“功名利禄”几个字
练得龙飞凤舞,
而那个最简单的“人”字
却大多是——
缺骨少肉,歪歪斜斜……
每次读到这些诗句,我都觉得这首诗和臧克家先生的《有的人》异曲同工。
张志民先生去世后,我们在《诗神》1998年第5期头条发表了这首诗。
1998年4月7号那天,《人民文学》杂志社的诗友商震来石家庄,谈话中得知张志民先生去世了,我当时很吃惊。前一段知道他患病,我还给他去信询问病情,志民先生很快回函:“由于身体情况,很久没有给你们写信,请原谅。我的病经过住院治疗,情况还算可以,请诸友放心。”没有想到,那竟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张志民先生“是最具长者风范的诗歌前辈”,这是我对一个好人,一个好诗人,一个我们河北人永久的感受。
又想到了张志民先生诗中写到的“人”字,这个字很简单,但何其难写啊!






![邯郸学步续写400字 [邯郸学步续写400字]邯郸学步续写400字](https://pic.bilezu.com/upload/3/e6/3e6775d6414f7cd12ccbf37aa21812b1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