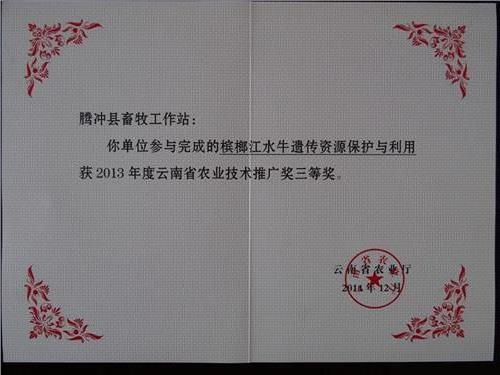荣禄谥号 戴海斌|仕途得自“武”事的荣禄 谥号却为“文忠”
传统史书首重纪传一体,旨在“以人系事”、“因事见人”。近代学术屡经思潮变迁与方法论更新,越来越多史著渐不以人物为当然主角,更有甚者竟已全然不见“人”的踪影,遂有学者发出历史研究中“人的隐去”的叹息(罗志田《经典淡出以后:20世纪中国史学转变与延续》,导言,第6页) 。
据笔者所见,政治史或许仍是目前最注意且不吝“深描”人物的研究领域。马先生写荣禄,不仅详道其生平,并历数其交游,尤其致力于廓清那些作用于荣禄仕进、影响于晚清政局的重要人脉关系,于传统政治运作深得三昧。
这种写法,已不止于描画荣禄本人的行状事功,或近似梁启超所谓之“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
此处“伟大”,姑取其“宏大”义项而不涉褒贬意,亦如梁氏提示“关系的伟大”,足以承担起串联近代中国“史迹集团”的功能,而可“将当时及前后的潮流趋向分别说明”。
在马先生看来,历经道、咸、同、光四朝,长期身居中枢的荣禄,“关注大局,用人无满汉偏见”,“与满汉、南北、新旧各派政治力量关系微妙,是沟通各派的关键人物”(3、235页)。满洲亲贵如醇亲王奕譞、恭亲王奕訢、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与荣禄关系亲疏不一,而尤以醇王对其政治地位的推挽之力最巨。
荣禄是不折不扣的“七爷党”,“终其一生,与醇王的交谊最深”(33-36、61-67、332页)。荣禄与端王政见分歧,是导致庚子变乱的一大渊源。
两人不和,固有神机营与武卫军争胜的近因,也与刚毅附端抗荣、火上添油相关;但马先生眼光能放得更远,注意到荣禄与载漪之父惇王奕誴“历来不甚融洽”,早在同治朝他就在惇王手下负责慈安太后普祥峪陵工,牵连贿案遭弹劾,惇王始终未出面做过一丝辩解。据此,“庚子前荣禄与载漪的不谐,似可从荣、惇早年关系中找出潜在的因由”(60页)。
荣禄仕途发达除了攀附醇王,还离不开军机大臣文祥与李鸿藻的提携。马先生多项举证,说明“文祥-李鸿藻-荣禄是清季权力关系中比较清晰的一条人脉线索”,而相较之下,“翁同龢与荣禄的关系则过于表面化,且时有暗中倾轧的迹象”(333页)。
翁、荣关系涉及晚清政治史上南 / 北、恭 / 醇、帝 / 后之争多处关节,是聚讼纷纭的一桩公案,高阳、林文仁、陈晓平等学者均有论列。马先生罗列异说,推原其实,指出“荣禄与翁同龢建立交谊,是因为醇王奕譞的缘故”;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元年,荣、翁奉旨承修陵工,“往还十分密切”;光绪四年“荣禄的受黜可能与翁难脱干系,至少有间接的关系”;“甲午战争爆发后,荣禄回到京城,能够迅速得到任用,翁氏也曾予以支持”;在汉纳根练兵问题上,两人“意见不同,甚至产生激烈的冲突”(41-42、74-75、105-110页)。
而戊戌年四月,翁同龢开缺,伴随了中枢权力的再调整,实质是一次“易枢”。马先生明确点出“徐桐、张之洞联手‘倒翁’,是这次易枢的明线;刚毅在慈禧面前对翁进行倾陷”,但论及荣禄的作用,一则谓“暗中也推波助澜”,再则谓“似无主动的推动”(166-167页),似尚游移。
不过,区别于很多人物研究一涉立场分歧势必说成水火的粗暴两分法,本书还是能从历史现场出发,平情讨论,尤其注意到晚清官场之“复杂多变”,“荣、翁心存隔阂,虚与委蛇,猜忌难除。
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仍然存在政治合作的基础”,“戊戌年春朝局中翁同龢与荣禄的关系完全不像康有为说的那么紧张”(75、169页)。
确实,如果看得再远一点,政变之后,荣禄还两次保护翁同龢得免于难。荣禄去世时,翁同龢有日记:“报传荣仲华于十四日辰刻长逝,为之于邑,吾故人也,原壤登木,圣人不绝,其平生可不论矣。”翁以荣比作原壤,意谓其有所失礼,但孔子不绝原壤,应以效法,不失故人之道,不必再论恩怨。此明显作的是“恕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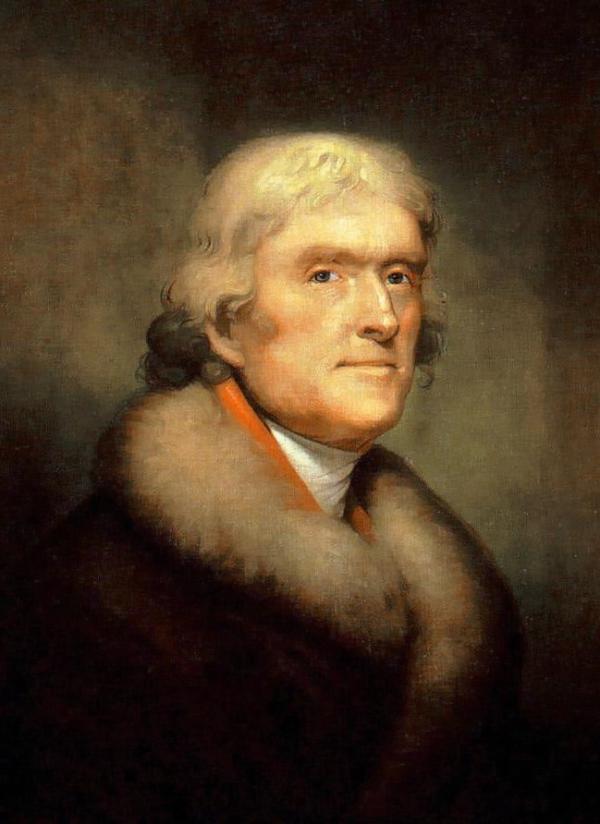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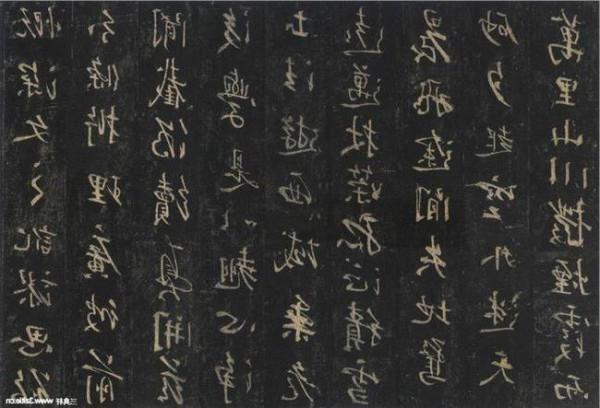


![>绝世唐门王冬被h [热门]戴华斌h王冬儿绝世唐门同人](https://pic.bilezu.com/upload/d/25/d25f60fa1a189ca0f744ad05e0992db8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