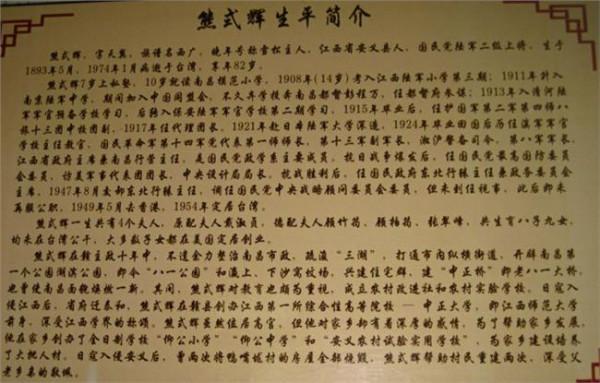任剑辉先生 任剑辉:故剑生辉雪落无痕
任剑辉这个名字对于内地的观众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在香港有无数戏迷和影迷把她唤作是一代偶像。她不仅是香港怀旧文化中不断被重复塑造的人物,更是大部分香港人成长的记忆之一。
电影与戏曲的关系始终是伴随中国电影历史的一个话题,而“性别易装”也在中国电影的各个时期凸显出独特的审美趣味。任剑辉是香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粤剧名伶,以女性身份扮演“文武生”,有“戏迷情人”
之称。而至她息影为止,演出的电影超过300部,这些影片不但把任剑辉舞台艺术的精华部分保存下来,也创造了不少令人难忘的、在舞台上不曾出现的角色,正是电影把她的声、色、艺保留下来,并广为流传。
今年恰逢任剑辉去世15周年,香港电影资料馆在任剑辉的“金牌搭档”白雪仙女士及好友的协助下举办规模较大的“任剑辉纪念展”,本报记者也特别关注此次纪念活动,并采访相关人士,使得读者对于香港电影历史有更丰富全面的了解。
▲与任剑辉合作最多的是白雪仙,故多称“任白”。
▲1964年任白投资拍摄的《李后主》成为了她们的告别影坛之作。
▲任剑辉是香港四五十年代粤剧名伶,作家迈克在《戏迷情人》一文中谈道:她如此潇洒地走出了性别的界限。
▲《帝女花》是任白的经典之作。
戏曲“易装”电影相随
我们都知道以前演戏是不能男女同台,所以不得不出现“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直到上世纪30年代初此项禁令才在香港开禁。而有意思的是1913年香港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有一说应为1909年《偷烧鸭》为香港第一部电影),其中由黎北海饰演庄子,其兄黎民伟反串庄子的妻子。此后,从四五十年代的粤语戏曲电影、武侠片,直至八九十年代的商业电影,“易装”始终是不曾中断的艺术形态之一。
说到任剑辉,她是从传统的粤剧班子训练出来的,她1912年出生于广州,自少年时起便跟随女武生小叫天学戏,但她的身形、台步深受文武生影响,后多反串书生和才子,但多是那种英气、刚烈风骨的“小武”书生。她经常来往于广州、香港和澳门演出不同的剧。及至50年代中期,与任剑辉合作最多的是白雪仙,故后多称“任白”组合。
“任白”的光与影
当时香港的电影制片人看到粤剧红火都愿意找舞台名伶演出,他们希望将戏曲电影化,但是粤剧演员都更重视晚上在舞台上的大戏,比如“任姐”(任剑辉)并不愿在电影上演舞台上的戏,所以50年代的时候任白组合多出演一些“时装片”,其中配几段自唱的插曲。即使这样戏迷、影迷们也很满足,因为看电影只需要很少的钱,而看大戏就是十几块、二十块钱呢。这对于经济上并不富裕的戏迷来说是很好的办法。
但是到了50年代末期,各种类型的电影以及电台都来抢娱乐市场,粤剧本身就有些低落了,于是不少粤剧大戏也纷纷搬上银幕,其中主要的就是任白的拿手剧目,像《帝女花》、《紫钗记》等等。这样直到60年代中期,由任剑辉主演的电影已超过300部,其中1964年任白投资拍摄的《李后主》成为了她们的告别影坛之作。
给人以最理想的状态
其实说到任剑辉的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来捧场,就是因为她的角色给予人心理上的启示,这也涉及到任剑辉为什么成为香港流行文化不曾被忘记的代言,以及现在有关“女性主义”等新学术理论的最佳承载的原因。或许正是任剑辉在舞台上带来的文武调和与阴阳调和,包括精致的戏词和本身的艺术修养结合得十分完美,所以带给许多人的感觉就是“这是人最理想的状态”。
香港影评人、填词人、作家迈克在《戏迷情人》一文中谈到他的认识:“如假包换的男人咬紧牙关实践他们的责任,任剑辉则挥着水云似的衣袖,把‘做男人’升华成艺术,道德沉重的包袱无声无息的消失了,什么光宗耀祖传宗接代,什么开枝散叶顶天立地,不再有他们的地位。她证明了男人一样可以吐气如兰,一样可以粉面含春,一样可以因美而存在。而且她如此潇洒地走出性别的界限。”
继续在流行文化中产生影响力
任剑辉对于粤剧戏迷来说,并不像京剧票友对梅兰芳的称呼是“国宝”或“大师”,是膜拜的对象,任剑辉是一个可以接近的“偶像”,她一直就不是站在很高的地方,是受普通人尊重和欣赏的人。
这次香港电影资料馆在11月29日(任剑辉逝世十五年忌日)开始举行她的纪念展,也恰逢“粤剧日”,希望在四五十年代兴盛,60年代后期低沉一时,又在七八十年代经由任剑辉的徒弟重新兴起的粤剧能够持续下去,并使得后辈们能够继续传承。
由于版权的问题,一些令人怀念的“戏宝”如《帝女花》、《九天玄女》以及落幕作《李后主》都无法取得放映,但幸运的是,资料馆近年来从美国搜集回来《大红袍》,虽然是缺本的,但却是遗失多年的珍本,有不少海外的华人特意坐飞机来香港观看,另外还有一系列图书包括一些剧照展、座谈会等极为丰富的内容。
口述:罗卡(香港资深电影文化研究学者)
采写/整理:本报记者张悦
■影响
吴宇森早期得意之作
《帝女花》(1976)是吴宇森惟一的粤剧长片,影片根据任白经典剧目的灵感,讲述明朝长平公主落难的故事。虽然经典程度不如龙图、左几50年代拍摄的版本,但他本人却非常喜爱这部初显风格的歌舞片,是他的十大得意之作之一。
关锦鹏再剪《李后主》
关锦鹏在他的纪录片《男生女相》和《念你如昔》中都以任剑辉的粤剧电影参与叙事。90年代,任剑辉过世以后,关锦鹏曾就任白的落幕作《李后主》重新剪辑,剪出第二版,但是只有小规模地公映过一次,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再放映。
巨制舞台剧《剑雪浮生》
5年前由“春天舞台”投资几百万元制作的《剑雪浮生》取得很好的效果,舞台剧是拿陈宝珠的复出和任剑辉、白雪仙、唐涤生的仙凤鸣传奇来营造话题效应,吸引观众。
也正因为当时香港舞台界欠缺新剧,在《剑雪浮生》上演之前,已经创出预售百场满座的骄人成绩,该剧的轰动效应是香港许久不曾出现的了。
口述:罗卡采写:张悦
■电影笔记
安能辨我是雌雄?
郎有千斤爱,妾余三分命,不认不认还需认,遁情毕竟更痴情,倘若鸳鸯劫后重和併,点对得住杜鹃啼遍十三陵?———唐涤生《帝女花·相认》
这段哀怨的唱词对于内地的观众来说多少是有些陌生的,但是对于香港的普罗大众,《帝女花》或许就像某种始终存在的背景音乐,即使如今不再是年轻一代所追赶的潮流,但在他们的儿时或多或少都会受过那哀怨而深情的唱腔的熏陶。
就像关锦鹏在他的纪录片《男生女相》中所说的:“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听过无数次任白(任剑辉、白雪仙)的《帝女花》”,他更是借着“女扮男装”的任剑辉的“易装电影”,巧妙地带出这种“性别倒错”的潜移默化可能就像“胎教”一样,是形成他日后性取向的某种因素。
对于热爱港片的内地观众来说,任剑辉这个名字多多少少应该有点印象,她就像香港怀旧文化的一个标志,时常会极其自然地出现在片中某个角色的口中,仿佛她就是一直以一个十分清晰的姿态存在于港人的记忆之中。而和任白长期合作、写下《帝女花》的粤剧创作名家唐涤生,亦即是高志森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奇作《南海十三郎》里那个放荡不羁却落拓一生的天才编剧十三郎的徒弟———唐涤生。
任剑辉的“性别易装”在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例子,1963年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凌波就反串了梁山伯一角,结果红遍港台,尤其凌波到台湾宣传时,整个台北为之癫狂,《梁祝》因此成为台湾60年代一个惊人的文化现象,关于它的影响和讨论可以说至今方兴未艾。
焦雄屏曾在《女性意识、符号世界和安全的外遇———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十年》一文中阐述:“60年代的台湾仍是道德保守的时代。
观众如果认同祝英台角色,将对爱情的渴望,或对婚姻的不满,投射在梁山伯身上,那么反串梁山伯的凌波自然得到众多的影迷。爱恋一个替代性男人,既非‘性’,也非‘异性’,这是多么不受威胁的外遇。这是性革命时代来临前的精神脱轨,也说明一整代女性在传统认命,妥协下的压抑和精神出口。
我认为这不是台湾独享的,香港也有众多太太戏迷的反串小生任剑辉,日本更有全是女人的宝塚歌舞团。凌波影迷中最死忠的是中年欧巴桑族群,原因就在她们的处境上。”
短短几句话就已经道明任剑辉、凌波等在五六十年代受欢迎的时代背景,而凌波风靡于台湾是因为黄梅调是国语唱腔,任剑辉则是粤剧名伶,故而更为香港观众接受。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性意识的开放,“性别易装”
这种表演方式在9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同性恋身份获得认同的一种心理投射,任白《帝女花》的曲词“不认不认还需认”甚至一度成为香港同志剧场的宣传标语。
而在90年代的香港电影中,这种女性易装的现象也变得更加班驳复杂、难以分辨。林青霞在《东方不败》中的易装造型,与令狐冲之间的暧昧感情几乎改写了金庸原著《笑傲江湖》的故事,但是林青霞英气逼人、美艳无匹的扮相却让一切都变得可信。
杨采妮在徐克导演的《梁祝》中部分易装男性,最后又恢复女性身份,当然徐克坦言他是以异性恋心理来处理其中情节的,而关锦鹏则在《男生女相》中直斥徐克破坏了“同性恋族群最美好的集体记忆”。
据说张国荣在和林青霞等一众好友打牌时曾经开玩笑说,有机会他要拍一个全新版的“梁祝”,写梁山伯本来就是个同性恋,结果发现祝英台是女儿身而气得吐血身亡。不论这个玩笑里包含了多少张国荣个人的心理投射,对于“梁祝”这个古老的爱情传说在当代显然已不止一种诠释方式。
吴君如在《洪兴十三妹》中则扮演了一个外表和内心纠缠于矛盾之中的貌似女同性恋者,因为男性形象更有利于江湖争斗和感情受到伤害的原因,十三妹掩盖了自己的异性恋身份,化身为一个男性形象掌管整个钵兰街。而在舒琪导演的《虎度门》中,由萧芳芳扮演的文武生冷剑心则明显有任剑辉的影子,台下的中年女戏迷为之痴迷不已的情景或许就是任剑辉当年被追捧的景象再现。
从40年代到90年代甚至直至现在,任剑辉“性别易装”的光芒和魅力,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显现出更加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她不仅仅是香港怀旧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典型,更是我们更多了解香港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侧面。□表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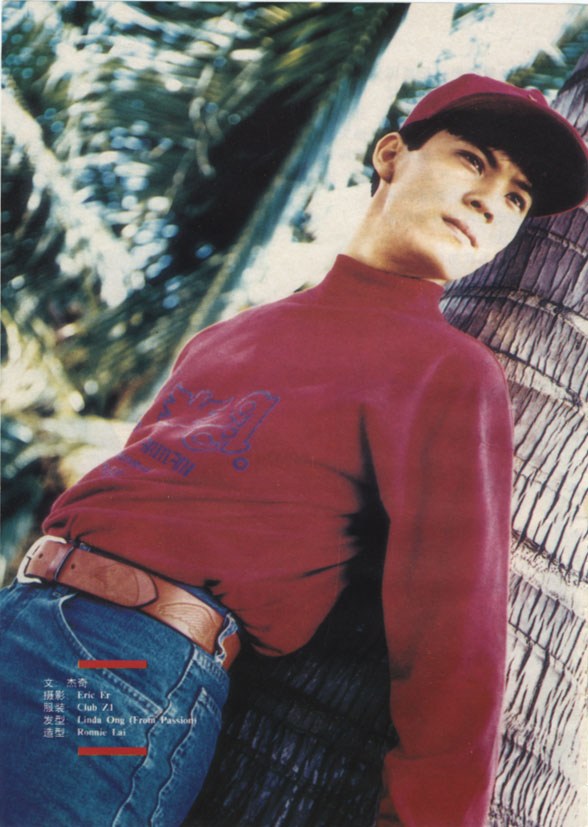

![>陈茂辉少将 陈茂辉[开国元勋少将]](https://pic.bilezu.com/upload/c/3b/c3bbe5fa40f648f683005be89039bfd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