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讲演录 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发议
之所以选择牟宗三的《周易哲学演讲录》来进行讨论,是因为该书具有极佳的代表性。一方面,该书是牟宗三后期易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另方面,牟宗三又是学界公认的当代新儒家的突出代表。故而,透过该书,我们不仅可以看清牟宗三本人的新儒学思想之成败得失,而且可以看到整个当代新儒学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不打算详细点评该书,只想对其做一个整体的把握,并就其中所反映出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
我们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谈到:儒学复兴的根本是要将传统儒学的核心原则,即中庸原则,升级为二重性原则;二重性原则可以归结为“异则”和“并建”两个思想要点,和“一体二用”、“二用相重”、“体用不二”三个核心论题;真正的儒学应通过贯彻二重性原则而按照“乾坤并建说”的“兼两”模式来展开,并表现为气化论、阴阳说和格局论“三个内核”;早期儒学因未能明确二重性原则而无法有效展开,也就不具有自身的“真操作性”,就不得不去通过与其他学派相糅合来获得“伪操作性”,从而使得汉儒走上了“阴阳消息说”的歧路,宋儒则不仅未能摆脱“阴阳消息说”的影响,而且走上了“理本论”以致“心本论”的迷途;对待“西学东渐”,我们应先回溯到儒学尚未出现偏失的原点,回溯到《易经》和孔子,然后将“佛学东传”和“西学东渐”合并看待,方能真正看清西印中三家各自的本来面目。
据此,我们可来审视牟宗三的易学思想,乃至整个当代新儒学。
牟宗三师承熊十力,所走的依然是“援佛入儒”的宋明老路。这意味着,在他心目中的中华传统其实是以宋儒(含明儒,下同)为样板,是立足于宋儒来看待“西学东渐”,而不是将儒学回溯到更早的原点再来合并看待“佛学东传”和“西学东渐”。
这就表明,他所理解的儒学,其实是片面的儒学,明显偏向了关系观,偏向了“心本论”。也就注定了,他所试图建构的新儒学体系,总体上是不成功的。其学术成就如同其师熊十力一样,表现为“高度开新”强于“立场返本”,虽然极大地深化了对“异则”的认识,但在对“并建”的认识上却是从王夫之的倒退。
我们先来看《周易哲学演讲录》中所表现出的对于“异则”的认识。牟宗三秉承熊十力“以心解乾、以物解坤”的易学思想,不仅承认世界有法则各异的乾坤两面,而且将这两种不同的法则明确提升为两条逻辑原则,即乾为“创生原则”、坤为“终成原则”。
他提出:“乾卦代表创造性原则,是纲领,在这个纲领下,终成原则就在这里面完成万物之为万物。所以中国文化尊乾而法坤。……尊乾就是以创造原则为尊,为纲领,法坤就是取法于坤。终成原则代表母道,照宇宙论讲,坤是终成原则。
”[1]他将这两条原则看作是儒家最为内在的东西:“《易经》从这两个原则讲一终始过程。这是儒家的义理,既不是道家的,也不是佛教的。……这是儒家的灵魂。”[2]他认为:“先秦儒家的古义是即存有即活动。
两个‘即’字白话文就是:它是存有,它同时是活动,两者分不开。从存有性方面说,它是理。它同时有活动性,从活动性方面说,它是神,是心。”[3]他这里所谓的一面是“存有”一面是“活动”,如果换成二重论的话说就是,一面是“存在者”一面是“存在着”,一面是“实体结构”一面是“关系构造”。
针对“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彖》)和“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彖》),他从本体论的角度解释说:“‘资始’那个地方,原来什么也没有,……它原来不存在,我使它存在,这个是始;存在以后,你照这样而存在着,这就落实了,真正成一个现实的东西。
”[4]换成二重论的话说就是,“资始”其实就是指“构造环节”,是世界得以开显所依据的“构造方式”;“资生”则是指“结构单元”,是世界具体展开所表现的“结构样式”。
针对“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易经·系辞上传》),他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指出:“人的智慧方向有两种方式:一、圆而神;二、方以智。
”[5]所谓“圆而神”和“方以智”,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悟”和“析”,或说“直观体验”和“分析思辨”,也就是二重论所讲的“内容逻辑”和“形式逻辑”。可见,牟宗三对于“异则”已有极为深入的体认。
然而,对于“并建”的认识,牟宗三却显得极其肤浅,甚至错误。按照王夫之对“乾坤并建”的规定,乾坤两面应是“时无先后,权无主辅”[6]。这里涉及了两个规定,一是“时无先后”,二是“权无主辅”,且都是逻辑上的规定。
对此,牟宗三如同其师熊十力一样,只以“体用不二”而在效果上保留了“时无先后”的规定,却以“心本论”而在逻辑上取消了“权无主辅”的规定。在牟宗三看来,虽然“创生原则”和“终成原则”皆不可或缺,但却有主次之分。
他认为,“创生原则”是“主”,“终成原则”是“次”,自然“轻重、本末要分清,主从要分清”[7]。所以,他认同朱熹“先理后气”的观点,认为:“阴阳”只是气,是形而下;“所以阴阳”才是道,是形而上。
他甚至明确表示讨厌把太极解作阴阳混元之气的说法,[8]而这正是当年王夫之在相反的方向上用力极深的地方。可见,牟宗三对于“并建”之于儒学的意义并无认识,明显是从王夫之的倒退。根本的,是他对于儒学所取的辩证观立场没有认识。
我们知道,关于新儒学的体系架构模式,牟宗三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源自佛学的说法,即所谓“一心开二门”。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牟宗三的逻辑立场和逻辑学思想,都明显偏向了关系观。将儒学看作是“心学”,这是熊十力和牟宗三共同的错误,实质是仅以宋儒为样板来看待儒学。
事实上,儒学并非所谓“内圣”之学,而是“内圣外王”的“兼两”之学。儒学所立的的“体”不是“心”,也不是“物”,而是“气”。“气”为体,“心物”皆为用,即“一体二用”。
所以,儒学的体系架构模式,应是“一体开二用”,而不是“一心开二门”。由此可知,牟宗三关于新儒学具体内容的另外三个著名观点,即所谓“道德的形上学”、儒学“三期说”和“三统说”,就都大成问题,都是立不住的。
“道德的形上学”之不可取,是因其“心本论”的偏颇立场已根本背离了儒家的中庸原则。“三期说”之不可取,是因其抹杀了汉儒的存在,并且忽视了孔子与荀孟的差别,以致看不到儒学曾有一个尚未出现偏失的原点。
“三统说”之不可取,是因其根本就是“乱说”,存在一系列逻辑错误:其一,其所谓“学统”与“政统”其实只是一统,而非两统,“德先生”与“赛先生”(即科学与民主)只是“耶先生”一人而已。其二,其所谓“道统”其实是指偏向了关系观的“心本论”,而非兼备“心物”两面的真正的儒家道统,并且,其所谓“学统”与“政统”的划分,混杂了学科领域和学科层次两种意义上的划分。
如果我们修正了其中的立场偏失,并厘清了其中的混杂,就不会有有“道统”而无“学统”和“政统”的局面出现,就不存在要“保内圣、开新外王”的说法。
其三,将儒学的落后归结为所谓“内圣强而外王弱”的说法,其实是混淆了立场与高度。“落后”是高度问题,意味着内外两面皆不够现代化;而“内圣强而外王弱”是立场问题,意味着立场偏失。
其四,其所谓“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纲领是根本不可能的,是对儒学的原则性误解。于儒学而言,“内圣外王”只是“二用”,而不是“体用”,能且只能由基于中庸原则的“一气之体”同时开出。
总之,牟宗三对于儒家所取的辩证观立场,以及与之相关联、相呼应的“并建”,几乎毫无体认。在他那里,人类文明是东西二分的,而不是西印中三分的。他立足于宋儒来看待儒学,自然要将印中两家混杂在一起,也就看不清西印中三家各自的本来面目,摆不正三家各自应有的位置,以致在其《周易哲学演讲录》中出现了许多错误。
譬如,他说:“全部的哲学理境,就是一个分别说的世界,一个非分别说的世界。分别讲,一切的哲学,从古到今,古今中外都一样,从柏拉图下来都是分别讲。
中国儒、释、道三教中,儒家孔子、孟子都是分别讲,《庄子》里面有非分别讲,庄子能了解非分别讲,境界很高,在《齐物论》就可以看出来了。完全把这个理境凸显出来,完全表现这个非分别说在佛教的《般若经》。
……西方都是分别讲,只有一个能表现出非分别讲,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他讲得并不好。分别讲都是方以智,《般若经》那个非分别讲就是圆而神。”[9]此中,他说西方是“分别讲”、佛学和庄子是“非分别讲”,是对的;但他认为“非分别说”与“分别说”是层次高低的关系,是错的;并且,他没有看到,儒家其实是“兼两”地讲,是一面“分别说”另一面“非分别说”。
又如,他说:“佛教跟中国的文化那个基本的情调、心态组合,所以中国吸收佛教比吸收基督教容易。……佛教讲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儒家讲性善,每一个人皆有良知、良能这个善性。所以,每一个人皆可以成尧舜。……基督教不可以说人人皆可以做基督,你只能做基督徒,你不能做基督,因为基督是个神。”[10]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不仅违背历史事实,而且也于学理不通。
说中国吸收佛教比吸收基督教容易,这完全是没有依据的。“佛学东传”从汉代开始,其精华直到宋代才被真正吸收,历时千年。“西学东渐”大致从宋元开始,迄今亦不过千年。如果要说难易,其实都是一样的难易。如果从历史事实上看到,“佛学东传”没有像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那样充满血腥,则是因为近代以来的西学除立场差异外,还兼有高度的差异,且西方文明原本是“好战”的实体观文明,自然在这个意义上要完成对西学的吸收会要显得困难些。
如果说难,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成立的。至于说到佛教以为人人皆有佛性,儒家人人皆有良知,而耶家人人都成不了基督,于是将佛教与儒家归为一类,耶家为另一类。这话表面看似乎很对,但其实经不起推敲。虽然耶家认为人人成不了基督,但人人可成基督徒啊,因而人人皆有“可成基督徒性”啊。
这不是一回事吗?他没有看到,西印中三家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其实是立场上的差别。严格地讲,儒家作为辩证观传统,性善论不是其合法的代表,真正合法的儒家人性论应该是善恶二重论。
性善论成为儒家正统只是宋明儒推崇孟子、贬抑荀子的结果,只是历史的阶段性特征,不是全貌。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因为儒家有性善论的一面,所以可与佛家融合;同样,也因为儒家有性恶论的另一面,所以也可与耶家融合。
再如,他说:“初步的思考是逻辑的思考,逻辑的思考是平常的思考,并不玄。玄思的境界一定比逻辑思考高,依《道德经》言玄之意义,其层次在逻辑思考之上。在中国传统里,魏晋以后的玄学是最高的学问。”[11]他的这一段话,是典型的基于关系观立场才会说的话。
因为在他那里没有辩证观的位置,也就只有把关系观与实体观二者对立起来,且按照关系观的逻辑而当作层次差异。如果进一步深究就会发现,此段话还有一个更深的根本性的错误,那就是混淆了两种“高”,即:将关于境界的玄思与该玄思自身所实际达到的境界混同在一起,错误地以为只要是玄思就一定境界高。追根究底,则是将立场差异混淆为高度差异。
从逻辑上看,如果不能区分三个立场,就必然会导致出现立场与高度的混淆。譬如,他说:“不能看到西方的方以智就全盘抹杀我们自己的文化,但也要看到我们的毛病,光讲圆而神不是足够的。……我们现在也需要科学,也需要训练逻辑,逻辑就代表方以智啦。
也需要自由,民主政治。……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吸收这个方以智的精神就叫作现代化。”[12]这是典型的混淆立场与高度。“圆而神”还是“方以智”,这是立场问题;“现代化”则是高度问题。
中国人之所以显得偏于“圆而神”,那只是宋儒的表现,是受“佛学东传”影响的结果,是宋儒的立场偏向了关系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需要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以便矫正宋儒的立场偏失,但这并不等同于现代化。现代化是指高度上的反身重构,意味着“圆而神”和“方以智”两面都要提升。
不能分辨立场与高度,还会有一个直接的后果,那就是不能真正吃透西方。譬如,他说:“亚里士多德一定要通过本体属性来看事物,本体是个体物,……那个体就是substance。……从本体属性说,最基本的命题是主谓命题,这种方式看事物,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考方式。
但是,现代人从十九、二十世纪以来,从符号逻辑出来以后就不采取亚里士多德式的方式思考,他们通过最具体的观念,最具体的观念就是actualization,这个观念重关系。
从这个观念转出‘现实的事实’,首出的观念是事实,是缘起集,actualization可译作‘缘起集’。所以,维特根斯坦的《名理论》头一句就说:世界是事实的总集,不是物的总集。……罗素出来重视关系逻辑,这表示一个新的世界观,代表一个新观点的出现。
”[13]牟宗三作为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其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逻辑学功底,向来被学界所推崇。但从他的此段话来看,只能说明他还远未吃透西方逻辑。
事实上,他的此段话的前半段是对的,后半段却是错的。维特根斯坦的“事实”其实是“原子事实”,罗素的“关系逻辑”之“关系”其实是被实体化了的关系,二者的逻辑实质还是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的,都依然是实体观的形式逻辑,只不过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态,前二者都是对后者的反身重构。
还有一个地方表明牟宗三对西方科学存在着误解。他在讲解“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经·系辞上传》)时,说:“这两句话根本是paradox,这句话根本是非科学的,反物理学的。物理学的速怎么样呢?物理学的速是加速,要加劲啦。
不加速就是静,物理学所谓静就是等速运动。假定永远等速,没有变化,你不知道它动呀。没有一个加速,它就是静啦。‘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两句话根本是违反物理运动的,根本是非科学的。
神呀,不要加速,它就自然会速;不要行,它就到。”[14]在这里,他犯了三个错误:一是理解错误;二是牵强附会;三是对物理学的解说也只能算是一知半解。我们来看《易经·系辞上传》原文:“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畿也。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畿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从原文的整体意思来看,这句话的准确含义无非是说,(通过“极深而研畿”,即可实现)“无为而治”、“事半功倍”。可见,这根本就无须也不该与物理学对照起来解释。
从牟宗三所给出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理解到的物理学,其实也只是牛顿力学,认为等速运动就是静,加速运动才是动。如果他能对物理学有一个全貌性的了解,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运动是有环节的,位移、速度、加速度、跃迁,等等,每一个运动的环节都可以被看作是运动或者静止,关键取决于我们从哪个运动环节的意义水平上来打开力学现象域。对亚里士多德而言,“速度”就需要外力来维持而已经是“动”了;对爱因斯坦而言,“加速度”也被等价于引力场而变成了“静”。
并且,从力学史来看,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也就是大致相当于《易传》成书的时代,人类对运动的认识尚只达到了“速度”的环节,还没有形成“加速度”的观念,根本不可能会去大谈什么加速不加速的问题。
可见,他的这种“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这种误读和歪解,会要把我们引向一个歧途,似乎易学与物理学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似乎有一个可以脱离物理学原理而神乎其神、高高在上的易学原理。这种误导显然是有害的。
综上可知,在牟宗三的易学思想中,虽然极大地深化了对于“异则”的认识,但却完全未能意识到“并建”的重要性。他立足于宋儒来看待儒学,也就以偏概全而错认了传统,错认了儒学,以致看不清西印中三家各自的本来面目,不能真正指明儒学现代化的方向。
虽然左冲右突,但终不得其门。这也正是当代新儒家们所普遍存在的问题。症结就在,重“异则”而轻“并建”,以致不能最终提炼出二重性原则,也就不能确立中华辩证观文明所独有的“兼两”模式的“真辩证逻辑”,不能懂得正统儒家的“一体开二用”的“乾坤并建说”。
对此,学界正在从多个角度,试图对牟宗三所代表的前辈新儒家做出修正和超越。诸如:李泽厚的“儒学四期说”,并提出了“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观点。[15]成中英的“新新儒家”,认识到“孔子的哲学是包含极广的,涵摄了孟子与荀子的重悟(思)与重学(知)、重义与重礼、重气与重理、重力行与重清明的多重性格”[16]。
并指出当代新儒家的问题在于,“未能系统地掌握古典性与现代性的要点对照是一根本的缺失。
往往以一概全,……至于径在道德理性一条鞭的基础上对治科学与民主两课题,犹不能解决所有现代性的根本问题”[17]。林安梧的“后新儒家”,认为中华传统的核心概念不是“心”,而是“气”,是兼具“心物”两端的辩证性概念,并提出“不再只停留于主体式的转折,而应通解而化之,由主体性转折为意向性,再由意向性开启活生生的实存性”[18]的“存有三态论”。
等等。他们的这些努力,都已明显地表现出对“并建”的关注,和对“兼两”模式的接近。
但可断言,如若不能最终自觉到提炼出二重性原则,这些努力就都还只是一种尝试,都不是最后的解决,都必然会要遗留或者引发新的困难和问题。譬如:李泽厚就主张所谓“西体中用”而被讥为“新马克思主义”[19];成中英在列举“古典性与现代性的要点对照”时,依然是在采用“两家模式”而不是“三家模式”,依然把印中两家混杂在一起;林安梧的“存有三态论”,依然不是采用“一体开二用”的模式,而是试图排列为一个线性的序列。
可见,离了二重性原则,新儒学就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所以,我们认为,儒学复兴还得接着王夫之来。虽然当代新儒家们已经在“高度开新”即“异则”上进行了开拓,但在“立场返本”即“并建”上普遍不足,甚至明显是从王夫之的倒退。我们需要在王夫之“乾坤并建说”的基础上,同时深化对“异则”和“并建”的认识,并提炼出二重性原则。唯有如此,“兼两”模式的“真辩证逻辑”方能真正成熟,儒学复兴才能真正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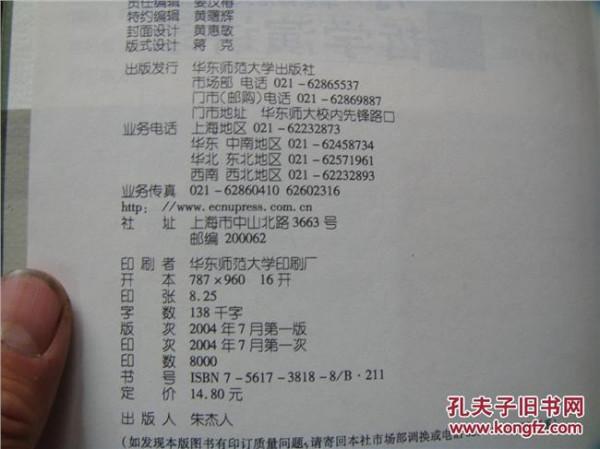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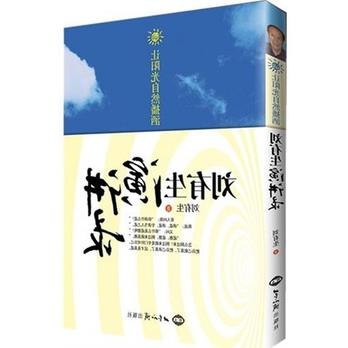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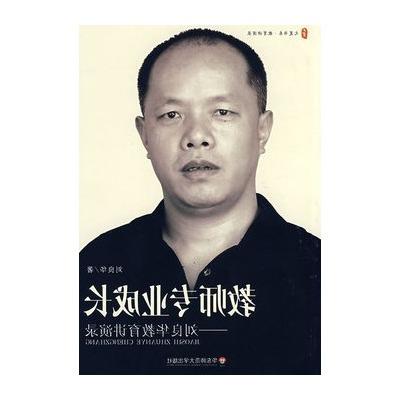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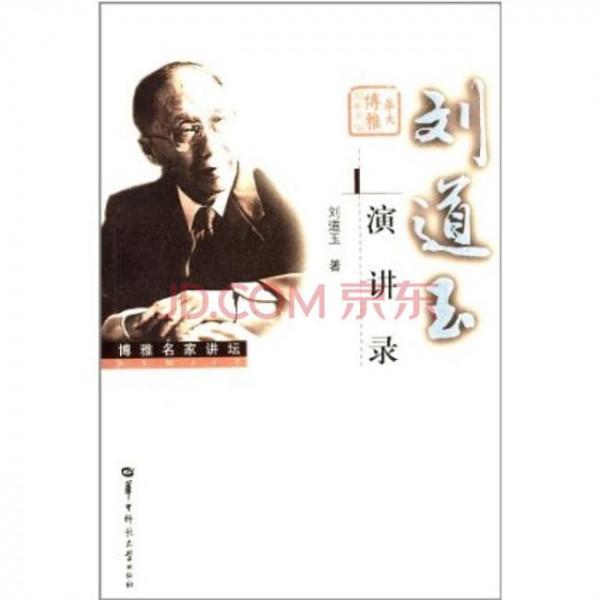
![>刘有生生气 [刘有生演讲录]不尽孝道 跟老人生气 容易得哪些病?](https://pic.bilezu.com/upload/a/9b/a9b6404b7cb9db961a0c99eb78d85ccf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