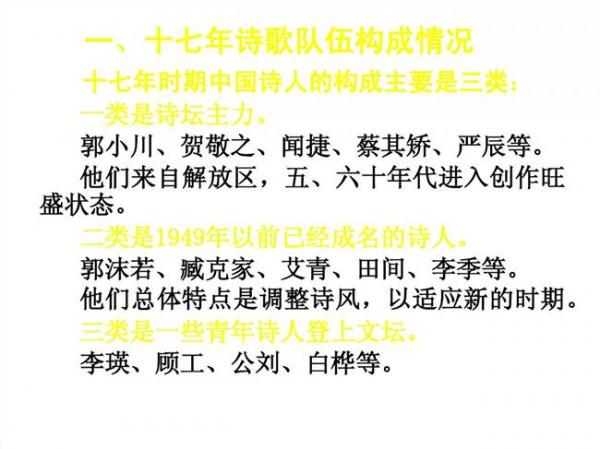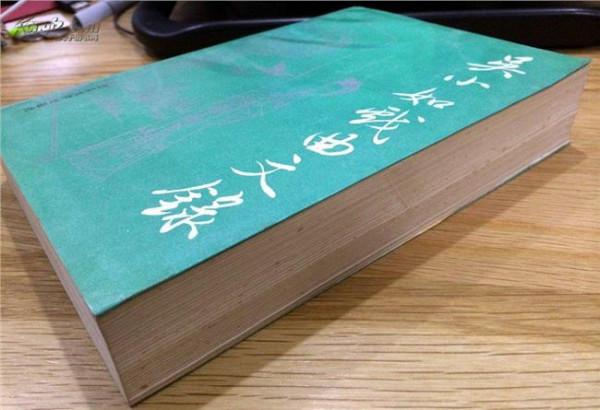梁小斌的诗歌欣赏 关于梁小斌的哲理散文欣赏
梁小斌,安徽合肥人,1954年生,朦胧诗代表诗人。自1984年被工厂除名后,一直靠阶段性的打工为生。下面是一九文学网小编为你带来的关于梁小斌的哲理散文欣赏,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关于梁小斌的哲理散文欣赏篇一:失去了锁链之后
红色舞剧里的那个吴清华猛然挣脱了柱子上的锁链,向洞开的牢房奔去,可是晃荡的铁索仍然在响:"你就这么走了,你到底还要不要我。"这位身着红色衣裳的丫鬟向柱子回望一眼,以示与锁链告别。
因为吴清华是穿着地主家的衣裳奔向红区的,这自然引起了连长的发问:"你为什么要参军?"我记得吴清华扯开了胸前的衣扣,露出了脖子上的鞭痕和被铁链捆绑过的印迹。我在想,如果她是拖曳着一根链子在进入红区后再忽然倒下,就会立即有一群儿童团员去搀扶她,那么"你为什么要参军"将是一句多余的话。
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的确可以失去自己身上的锁链,但暂时不可以失去自己脖颈上的伤痕。难道可以说,无产者必将失去自己身上的伤痕,那么,她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将失去最后的阶级甄别依据。
一块石头离开了一堆石头,她不愿意再做石头了,但是她必须是带血的石头才能进入红区,这是我们的革命文学最早的看上去最为朴素的悖论。
果然,女奴隶怒不可遏,好像是因为他们在问伤疤是怎么来的而愤怒,其实,她对围拢过来的儿童团员们的警惕目光表示愤慨,她撕开胸口遮盖,露出鞭痕。接着,她喝到了椰子水,成为消失在白云、蓝天、红旗组成的画面里的一道和谐色彩。
按照我头脑里的怪念头,如果是吴清华在必须奔向红区的途中,在雨林里多耽误几日,她遍体鳞伤都慢慢愈合了,那她将怎么办?千万不要在椰林里采中草药等养好伤再说啊。她被鞭子抽打昏了过去,是大雨将她浇醒,也许大雨在洗涤着她的伤口,也许雨水令其伤口糜烂。
这个时候,椰林里的滴滴甘露似乎没有什么立场,它根据吴清华的需要而定,如果吴清华报仇心切的想法稍有迟疑,雨水就会更加晶莹,野果子和中草药同时会奉献出来映入她的眼帘。她如果真的养伤,从理论上讲有些创伤是甚至不留痕迹的。
忘记带上锁链出走(譬如讲将锁链裹在包囊里,面呈给连长),这绝对不是小事情,但这形成了我们文学理想的疏漏。在欢腾解放的时刻,无产者将手中的锁链扔向远远的大海,后来发现他又不得不把生锈的铁链从大海深处重新捞回来。捞回来的目的不是为了重新戴在脚腕上,而是要把它重新锤打为桂冠戴在头顶。
曾经有过的苦难,或者说正在受难,是通向欢腾舞蹈场面的路条。我观看奴隶们欢腾的舞蹈,看见一束红光照亮天下的所有圣品。我感到寒冷,这非常像在大雪天,你不论将什么物品从室内搬到室外,所有物品都适合在雪天摆放。一个无产阶级的身份证明:铁链,从牢房扔向雪地,雪花覆盖着它,这看上去更像是革命的静物图画。我们开始描述,忘掉了铁链是有人扔到这个相框里的,相框里多了一根铁链。
那个女奴隶挤进了人数已经凑足的革命队伍里,她晃荡了一会又开始跳舞。这个欢腾场面马上表现出它的虚怀若谷,革命队伍正期待她前来补缺。
我经常想,在那道红色光束下面拍拍自己的身上,希望能从身上拍落点红色雪花。我走到雪天,看看有许多人都拍拍自身,让雪花落下,表示他是从雪天里回来。我混进红色雪天,从身上没有拍下什么,我是在雪停了很久之后才走进雪天。
关于梁小斌的哲理散文欣赏篇二:苦难,如果仅是为了震撼
摄影记者贺延光静悄悄地将照相机对准病房里的小患者,他想拍下点什么。但是这个小女孩发现了有人在拍她,便急忙用手中的杂志挡住了脸,并说:"叔叔,您不要拍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呢。"
这个小患者大概也只是躲在病房里看杂志,并不是在这里生病。还有,这真是诗的逻辑:只要她妈妈不晓得她在生病,小姑娘自然也就是健康的了。小姑娘在说话,制止了对一种真实境遇记录的发生。
感谢贺延光记下了孩子的话,我也像当年背诵语录一样背诵着它,就是这句话,背在身上真是比辞海还要厚重啊。
我也要学会去制止什么。1981年我参观了北京的星星画展,第一次看见了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这幅和领袖画像一样巨大的父亲画像原来是由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堆积而成,父亲正端着水碗却暂时没喝,不知是等待着水该凉一些,还是期待着阳光把水晒热。而父亲扶着碗沿的拇指上的污黑指甲却清晰可见。
这就是逼真的艺术所带来的震撼效果,开始我想说:父亲这幅画,画出了解放后中国农民的苦难和淳厚,这几乎是一句空话。我是空旷展览大厅内众多簇拥观众的一员,我们在震撼之余也不知到底该怎么想,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在《父亲》面前我们徘徊接着走开,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父亲"终于也在说:"艺术家同志,请不要这样画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变成这般模样。"
我也的确在套用小女孩的心声,因为站在苍老的父亲面前,我们还不会想到他还有妈妈,因为逼真已经是底蕴,已经像大地一样。在逼真的后面,不会再有什么,于是,艺术家可以尽情地去画。
倒是当年审查这幅画的干部懂得:逼真的农民形象要有所遮蔽,这就有了画家在父亲的耳朵上画了根圆珠笔的妥协方案,以示父亲也有文化。父亲固然"有文化",但他苦难的面容,一经发布已经尽人皆知,唯独至今没有听到他母亲的哭声。
我们开始热衷于艺术的逼真运动,还是在北京,在那个"798"艺术工厂区,现在有一组矿难雕塑矗立在露天。那天我远远望去不知道广场上的一群人怎么都变成黝黑黝黑的模样,我蹲下身本来想揭开地上死者的被单,原来被单是以石头铸成。
雕塑群中,除了有死者,还有活着的孕妇和孩子。我们打着领带穿着皮鞋从这里经过,那个被石头铸成的孩子,只是抬头看他的母亲,而从不抬头看我们。在参观者中,还真有胆子大一点的小朋友,拎着汽球,围着矿难雕塑满场跑,他想惊动他们,但他们仍然纹丝不动。小朋友终被他的母亲喊回了身边。
到底是满足了一个灾难事实的描述,还是满足了艺术家以求逼真的艺术心理,我耳边又继续响起那位病中女孩的箴言。现在该由那位黯然神伤的孕妇说出:"雕塑家先生,请不要把我们铸造成已经死去,也不要把我浇铸成已经怀孕,我们的妈妈还不知道我们躺倒在这里。"
这大概可以成为批判家们批判我想掩盖人间真实苦难的口实,是的,除非他们没有母亲,除非他们只是苦难本身。我也曾以凝重的心态偷偷地欣赏这苦难矿工们的造型细节,我甚至伸手摸摸那个悲伤的孕妇像石头一样硬的肚子,瞬间觉得她忘却了躲闪。我的好奇心以摸摸那个孩子的脑袋作为参观结束,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母亲,这样连苦难都是孤独的。关爱只能从悲痛中而来。
许多情况下,人间灾难消息的发布,最初的确是以"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进行的。一个战友牺牲了,唯独必须相瞒的就是在家乡井边正在提水的他的母亲。所谓悲剧通报的难点就是通报时刻的来临。其他人知晓没有明显的意义,死者的战友们藏着死者的遗物但谁都没有胆量走向老人。
那放下木桶的腰身还没有站直,谁敢破坏母亲此时的无知状态,无知就是宁静。所以欲言又止,说出战友阵亡的事实,那话语中的意味真比蚕丝还细。谁都害怕看见母亲因悲痛而崩溃。
但是艺术家看上去也在呼吁,因为呼吁可以成名。但是,令我尊敬的贺延光先生在说:"直接表现苦难是最简单的,如果仅是为了触目惊心,去展示视觉刺激,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人格的损害,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
因此,要有点忌讳。"这个世界上的艺术家们早已把艺术"要有点忌讳"这个准绳抛到九霄云外。越演越烈的所谓视觉冲击力和听觉冲击力已如同潮水。最早我注意过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刻,竹竿将大红灯笼挑起,在某个屋檐下灯笼悬定,挂钩声咔咔作响。
我想艺术家肯定迷恋这种音响质感,但是也太夸张了。那个"泰坦尼克"号,为了保持灾难的风度和震撼,在下沉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船舷上的灯火辉煌,我们从欣赏艺术和生活里的所谓"小小质感"开始,艺术品位在慢慢上瘾,现在也开始学会欣赏灾难的质感了。
贺延光先生提到的艺术对人格的损害,我甚至理解为艺术正对母亲造成损害,说到底,任何苦难和灾害的当事人不论他们人间的年龄有多大,他们的心中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在爱着他们。生怕母亲受到惊吓这是唯一的宗旨,因此,苦难的写实必须有所忌讳,这才是苦难中人真正的心声。艺术家应当照顾这种心声。
二战期间,当"艺术家"还带着钢盔,手持卡宾枪在战场上服役,那时,他们的行为只是忠实地执行法西斯当局所下达的活埋女孩的命令。任务的程序是:坑已经挖好了,然后将女孩推下去,最后用皮靴踏平泥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行为艺术",这个行为的唯一主题就是宣告残忍。
但是,孩子走到手持卡宾枪的人面前,平静地说道:"叔叔,请不要把我埋得太深,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我们的理解曾经有误,小姑娘不是在报道噩耗而是希望母亲能把她从深埋中拉出来,然后一块儿回家。这是在灭顶之灾面前勇敢地破解活埋的深度、破解所谓视觉震撼,我们人最早的童声。因为人是有母亲的。
永远不惊动母亲的神色,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人心和品质,保持天下母亲和天上母亲那面容的静穆,是我们的守望和责任。而往往,我们看见母亲微微闭目如此安详,却试图惊醒她,所谓朝拜和跪望,此刻人心并不真爱那个端坐的女神形象。
因而,我们日常的人心,贺延光先生看得最透。他要拍张生病小姑娘的照片,却要让小姑娘放心,他说:"你看你的,用杂志挡住脸,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
是为警醒。
关于梁小斌的哲理散文欣赏篇三:阵地上的分娩
红军女战士向前方的敌人射出了子弹,她要把子弹袋的子弹全部打完后她的肚子才能开始疼。她在想,等把蝗虫般扑上来的敌人全部打死后再生孩子也不迟。她不紧不慢地射击,几乎忘记了肚子里还有孩子,但是她是真正的孕妇,她的肚子开始了阵痛。
这样,孕妇被迅速地转移到一个山包的后面,几个女战士围拢过来,围拢成一个临时产房,前方更加密集的枪声现在不是打在产房的背后,而是射在更加英勇的红军战士的前胸。呵护产房的前胸像土墙般一块块倒塌,有一个红军传令兵跑向山包,对着产房大声命令:"那里面的同志快点生,前面快要顶不住了。"
我听到一句回敬铿锵有声:"哪有生孩子还能快的。"一个母亲生下孩子所花的时间究竟该有多长,此时却有前方的枪声在为产程读秒,每一声枪响里都可能会有一个战士倒下,前方在告知:"在最后一声枪声沉寂之前,快把孩子生下。"
那时,谁都恨一个不紧不慢堪称伟大的产程。也许不紧不慢的产程步伐有点过于傲慢,只顾自己有节奏的收缩,甚至产程它自己也有点累,它还要在孕妇的肚子里停顿一会。但战争在流血,当战争的规律和生孩子的规律像两股麻绳搅到一块时,其中将压榨出生孩子的时间必须缩短这个简单道理。
"哪有生孩子还能快的。"革命的助产士难以把这个道理坚持到底。她率领她的同事们齐声向已近昏迷的产妇大声喊:"用劲。用劲。"但是产妇的确在昏迷,为了肚子里的生命她曾经吞糠咽菜,因为她吃的不好,自然会想孩子你愿意在我肚子里呆多长时间我都愿意,吸我的血吧,只是千万不要提前生出来。现在她不清楚,她已经不是孕妇了,而是产妇,她有责任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内务必把孩子从身体内驱除出去。
产妇重新苏醒过来,她在"用劲"的呐喊声中咬住毛巾,尽量做到不让阵痛退潮,革命的助产士眼里流着泪水。她们握住产妇的手,给她输送力量,并在她耳边提醒:"不要睡着。"产妇勉强睁开眼睛告诉大家:"我没有睡着。"
助产士依然在说:"如果实在生不下来,那我们几个姐妹就搀着你走,不,是用担架抬着你走。把你抬到那个催命的枪声之外,我们都是女人,我们知道女人生孩子该用多长时间。""不,不要管我了,你们都走吧,让我自己在这里生孩子。"
这个山包下产房的头顶正哗哗地飞过子弹,女人的议论不足为凭,前方战友的血就这样白流了,用战士生命凝结而成的时间难道就不算数了。前方的传令兵第二次通告所有助产士们:"不要瞎折腾,就在这里生,孩子必须生出来,而且必须是活的,要快!"我们现在肯定要让敌人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打阻击,在最后一个战士倒下之后哪怕敌人冲上来,冲进产房也要让他们看看为了生孩子而流下的满地血污,因而这是光辉的血红。
其实敌人早已从望远镜里发现了红军队伍里的变故,敌人的诡计是:万一把红军逼急了,他们真的能丢下正在生孩子的红军率先撤退?于是向红军阵地射来的炮火反而开始不紧不慢,其用意是,把正在生孩子的红军队伍吸引在这里,要他们动弹不得。敌人在想:生孩子的过程最好是越艰难越好,但也不能生不下来,不然红军也会跑。
现在几个姐妹围拢的产房开始摇晃,产妇仍然不见动静,只是在疼,有曾经生过孩子的战友再发问:"是不是真的要生,产妇的肩膀曾经受过伤,是不是她把肩上的痛误认为是肚子在痛,而且就算肚子在痛,也不一定非要在这个阵地生产不可。"
头上带着八角帽的产妇,你是孤独的,生孩子哪有这么快,但也的确没有那么慢呀。产妇,在你的脊背下面不是战友的衣裳,也不是渗着血的草地,你是躺在一个叫做"分娩"的十字架上面。既然孩子生不下来,那么就赶快把这个十字架像担架那样从背后移开。
但是产妇又进入了昏睡:我快顶不住了,我也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姐妹手腕上的血痕就是证明。可我越是听到枪响就越是没办法把孩子生下。太阳,也请你快点下山,我眼睛里的烛光也快熄灭了,请用那无数根金色绳索把太阳拖到山下去。
连助产士俯身想听听她肚子里是否还有胎音在跳的机会都没有,敌人的迫击炮弹令山谷震荡。没有谁知道这件事的结局。山上的敌人像决堤的洪水涌到山谷之间,早已有炮弹扫荡的草地上遗留的纱布和血污,并有成团的杜鹃花响应着我们快顶不住了的召唤适时地开放,如冰的溪水也奔腾在欣欣向荣的风景途中。啊,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