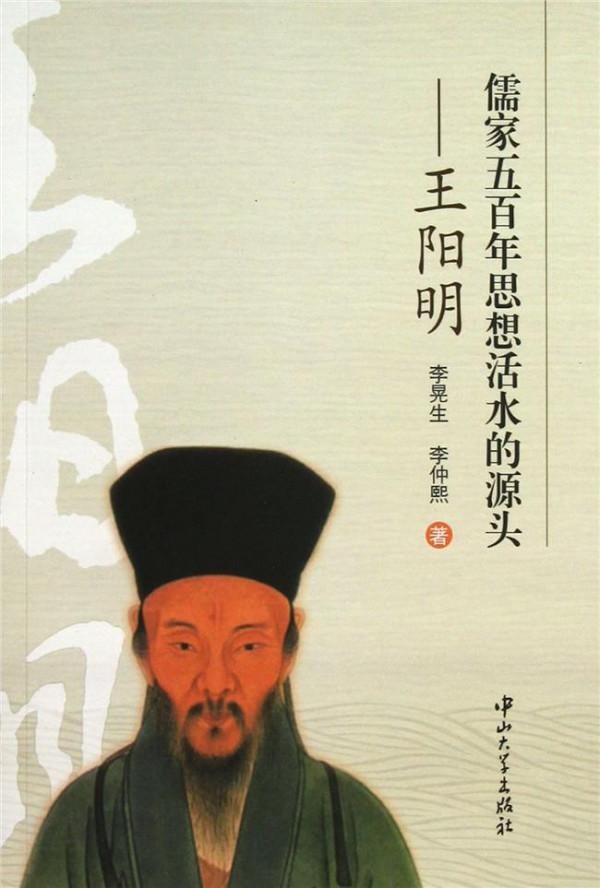张新民画家 【张新民】儒家生死智慧的超越 ——王阳明龙场悟道新论(一)
“龙场悟道”乃是王阳明一生思想发展最重要的飞跃性转折,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具震撼性的生命顿悟事件。“龙场悟道”对个人生命影响之巨大,阳明自己亦曾提及:“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了三十年气力。
”可见他真正步入儒家圣学正途,乃是在龙场“居夷三载”期间。这一点也是当时及后世学者的共识。如王门弟子王龙溪便明白称:“阳明先师崛起绝学之后,生而颖异神灵,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
盖尝泛滥于辞章,驰骋于才能,渐溃于老释,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无内外,无精粗,一体浑然,是即所谓未发之中也。
”与王龙溪同门的钱德洪也持类似看法:“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于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人之旨,是三变而至于道也。”与龙溪、德洪同时的陆澄亦有简明概述:“守仁学本诚明,才兼文武,抗言时事,致忤逆瑾,杖之几死。
谪居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独悟道真。”徐爱同时兼有妹夫与学生双重身份,是阳明最早入门的弟子,熟悉阳明早期思想,他的话显然也值得注意:“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晚近的严复虽未必就完全赞同“心即理”之说,但也强调“阳明居夷之后,亦专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他们的看法都足以证明龙场大彻大悟,乃是阳明一生思想发展的关键性大事。
而阳明“才高气盛,不受汉、唐、宋以来诸儒笼络,故能悬旌立帜,奔走天下”,即使有明一代学术肇自陈白沙,但汇河为海蔚为大观者仍首推阳明,则“终明之世,驯至于昭代,常为学者宗师”,其他所谓大小派,不过附庸而已。
具见“龙场悟道”亦为传统学术由理学折入心学的标志,预示了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重大转向。因此,认真分析“龙场悟道”前后阳明思想的变化轨迹,了解其悟道过程中的先后次第,不仅能够更好地把握其思想发展的整体全貌,同时也有助于全面判识有明一代学术思想调整变动的大端脉络。
龙场悟道从整体上看,固然是阳明精神境界飞跃提升的突发性思想事件,但由于包括佛教等各种思想资源的旁助激荡,他在受害谪居黔地之前,实际已有了与朱子有别的心学发展方向的明显痕迹。如果再追溯他的少年时代的各种行为细节,则可说十一岁时,他以读书学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虽以后时有起伏曲折,多得各种思想资源的触媒,包括出入于释、老,便已有了清晰的人生发展方向的自我设计,踏上了“成德”或“成圣”的修行之路。
而一旦踏上了“成德”或“成圣”的修行之路,则不但“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更重要的是象征着有了人生发展的定盘针,开始迈向了宗教性的终极目标,当然也就意味着“人生不闻道,犹不生也;闻道而未见其止,犹不闻也”。
而弘治十七年((1504)他三十三岁时,痛感“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遂开始向来学者“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便显然是少年志向的继续延伸和发展,当然也为龙场悟道之后“优入圣域”准备了条件。至于他修习释、老工夫,不过是迈向终极目标的方法论的早期尝试,但未必就毫无身心上的受益,显然也引起了知见上的变化,王龙溪(畿)尝有记载说:
(阳明)为晦翁格物穷理之学,几致可殒,时苦其烦且难,自叹以为若于理学无缘。乃始究心于老、佛之学,缘洞天精庐,日夕勤修炼习伏藏,洞悉机要,其于彼家所谓见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义,盖已得其髓矣。自谓尝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同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
具见他是依朱子的治学路径“格物穷理”,甚至以七天的时间“格竹”而引发大病,感觉与理学无缘,才开始潜心修习佛、老之学的。《年谱》载弘治十五年(1502),阳明时值三十一岁,曾由京师“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即有了一定的“神通”。
足证王龙溪所记,必为是年之事。文中既云“自谓”,则当直接闻诸阳明,即阳明亲口所言,显然也足可信据。而阳明在静定至极之境中,自谓“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实即心体灵知之性,在排除纷纭杂念干扰之后,所自动显现出来的常寂光,也可说是人性本体固有之光,而与一般自然之光不同。
适足以说明他已初步接近心性本体,遂有身心内外凝成一片,乃至通体透明之现象学显现,决不可随意扣以神秘主义的大帽。
而“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同体”,更明示他已初步证到“空性”,身心气质遂产生变化。只是从整体上看,所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仍不过是在光景之中,距离真正的悟道,尚有长程的路途要走。
一般说来,心力倘若未能超越动静二相,便不能不往来波动,以致微细念头时有起落,幻境亦随之变现来去,当然便不可妄加执著。阳明不以神通为然,又认为幻相“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诚可谓慧眼如炬,反映他之所以出入于释、老,目的仍为追求人生真谛,与“人生第一等事”有关,必以“悟道”或“得道”为最高标准,决非卖弄世俗时髦小术,亦无任何神秘色彩可言。
不过,阳明之所以放弃“炼习伏藏”,尚有另一原因,即“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如果耽空滞寂,一味执著或贫恋清静,即通常所谓堕入顽空,固然可能“断灭种性”。
但如果真能契入无相静境,久久功力熟透,然后依体起用,如前所说做到“无所住而生其心”,也会焕发无限创造生机,则非但不会“断灭种性”,反而能够“长护种性”。阳明入定工夫甚久且深,乃至有“离世远去”之思,说明他已有了清静、自在、超越的宗教式心灵体验,已开始步入了“结圣胎”的生命存在境域。
阳明因人生最天然纯真的亲情之念而放弃修习,固然不无道理,但不知道依体起用只能激活而非断灭种性,工夫未臻究竟圆熟即主动放弃,也意味着以后必有退转。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他已初步证到了空性,实已为六年后的龙场大悟,准备了必要的前期条件,即所谓“学静入于阳明洞,得悟于龙场”。而他在龙场采用“澄默静一”的方法悟道,悟道后特别是“居滁”期间又曾以“静坐”方法施教,强调一旦有所证悟则必须存养扩充,显然也与这次生命体验经历有关。《传习录》曾载他与学生的一段问答说:
问:“近来用功,亦颇觉妄念不生。但腔子里黑窣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里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浊水,才贮在缸里。初然虽定,也只是昏浊的。须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尽去,复得清来。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责效,却是助长,不成工夫。”
可证龙场大悟之后,即在阳明揭出良知说的晚年,他也并未否定“习定”工夫的重要。只是良知学说彻上彻下,直指本体,不易发生偏颇,乃是有体有用的圆融之说,所以他更突出了“在良知上用功”的方法路径。而静定工夫熟透之后,身心寂然,性光现前,必然气脉流通,精神炯发,腔子里自然便会“打得光明”一片,则是龙场悟道之前,便已具有了的心得经验,当主要受益释、老两家方法论的启迪,得力于多种思想资源吸收内化的增上助缘,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而良知即为天理,天理则可内化为人的价值感,即儒家最为强调的义理:“义理本人心所内具,然非有悟证,不能显现,悟证不是一时可能,根器有利钝,用力有深浅,但知向内体究,不可一向专恃闻见,久久必可得之”。阳明认为只要肯用工夫,“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也表现出他对人性光明的坚信,对生命能够与道合一的自觉,对“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贞定。
然而在求道的路途上,阳明尽管已试尝了各种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资源,但真正要在道境上有所证入,仍要到谪居龙场前后,经历了各种人生苦难,遍尝了非生即死的艰辛折磨,具足了孟子意义上的“动心忍性”的生命体验工夫,才能说一切因缘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检读《年谱》,即不难知道,正德二年(1507)他为营救戴铣等人,触怒阉宦刘瑾,遭谪贵州龙场驿丞,一路追踪阻扼凶险不断,乃佯置衣履于江岸,因假托投江而死,终得以免除罹患,遂不能不追问存在的意义,油然升起强烈的超越性向往。万里投荒,化险为夷,前途依然难测,他曾有诗记其事云: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诗中之“太空”当为心体之隐喻,“浮云”则暗示往来于心中的荣辱得失杂念。“夜静海涛三万里”则指借助于寂静本体的内观察照,愈加清晰地了解到意识瀑流如海涛般汹涌。而“月明飞锡下天风”更表示一切均复归于本体静谧光明,无限超越的胸襟情怀则随之自然显现。
或许迫害之路便是觉醒之路,说明至迟在到达龙场之前,虽只是初步的解悟而非彻悟,但他的确已证到了“空性”,具备了在苦难中升华境界的心智能力。足证苦难乃是极为重要的逆增上缘,动心忍性亦为成就生命价值的必要环节。
阳明一生每一次精神境界的磨砻与提升,均可说是从苦难中陶冶淬励才有所收获。以后他屡用“太虚”比拟良知本体,用“日月风雷山川民物”等象征一切器世间的存在,以为无论器世间的何种存在,均作不得良知流行发用的障碍;又以能够蔽日之云象征七情,强调“天不要生云。
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 最典型者则为“圣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霾天日,虽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则一。
虽昏黑夜里,亦影影见得黑白,就是日之余光未尽处,困学功夫,亦只从这点明处精察去耳!”凡此种种善譬妙喻,要皆不过旁助他人恢复心体良知光明,一如阳光穿透重重云雾阴霾,最终必能步入万里无云万里天的洁净空阔妙境。
如果分析其前后思想渊源流变发展过程,则到达龙场之前已可略见悟道端倪。至于到达龙场后的艰难境况,则更非常人所能想象,当然也就加倍增益其所不能:“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诚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年谱》则载正德三年(15O8)他在龙场悟道的经过情形云:
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
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
“时瑾憾未已”云云,说明政治高压气候对他而言,始终是必须时刻面对的一个严峻事实。而“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不仅象征自然环境的恶劣,而且也暗示政治气候的凶险,具见他的悟道,乃是同时面对政治与自然双重非人化的恶劣生存环境,力求从虽生犹死(日有三死) 的极度困厄处境中卓然超拔挺立,从而将一切痛苦与不幸的负面遭遇,都转化为自我完善的正面力量资源,诚可谓“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无处不为人生领悟生命真谛的实践道场,无时不为体证生命固有美德的最佳机缘。
有关龙场悟道的经过情形,阳明后学罗洪先(念庵,1504-1564)亦曾论及:
(阳明)先生以豪杰之才,迈往之志,振迅雄伟,脱屣于故常,于是一变而为文章,再变而为气节,当其倡言于逆瑾蛊政之时,挞之朝而不悔,其忧思恳欵,意气激烈,议论铿訇,真足以凌驾一时,而托名后世,岂不快哉!及其摈斥流离于万里絶域,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区,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无一可骋者,而且疾病之与居,瘴疠之与亲。
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辗转烦瞀,以成动忍之益。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吾独存而未始加损者,则固有之良知也。
罗氏认为生死利害,根本便无一毫能加损于贯通形上与形下两重世界的良知,亦即阳明所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均指形上超越的心性本体,一旦证入其中,便知人人具足,本无生死流传,更遑论得失荣辱。
这显然是一种反诸已而从其源的方法,所谓“源”固然即内在于人人均有的本心本性之中,但也是一切存在和价值的根源,一旦证取便意味着对人生与宇宙的真实有了彻底的了解,构成生命迈向成圣成贤终极性的“至善”境域源源滚滚不断的上进动力。
。当然,具体到阳明龙场悟道的前后过程,则是先破得失荣辱关,然后再更上层楼,不断进入生命新境,彻底跨越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的大关大隘的。尽管“利、害、毁、誉、称、讥、苦、乐,能动摇人,释氏谓之八风”,欲从其中超拔而出,已属不易,但如果与生死大关大隘相较,则显然后者更具有本根性或本源性,也就更加难以真正做到彻底超越。
盖揆诸古今,旷观东西,均可说是“人生生死亦不易,谁能视死如轻尘?”阳明自己也说:“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
虽修短枯荣,变态万状,而终必归于一尽。君子亦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与终极目标追求的紧迫性,二者之间的冲突更不能不造成生命内部的焦虑或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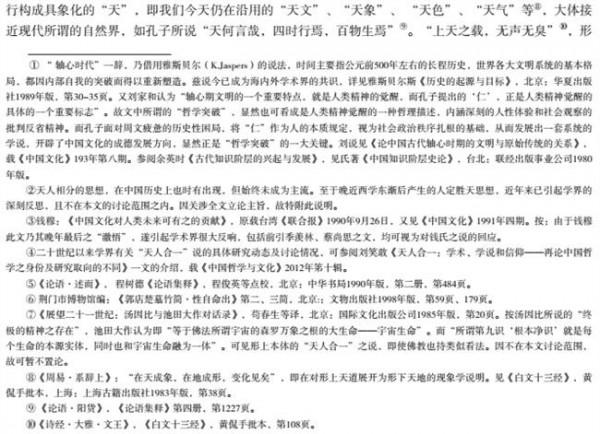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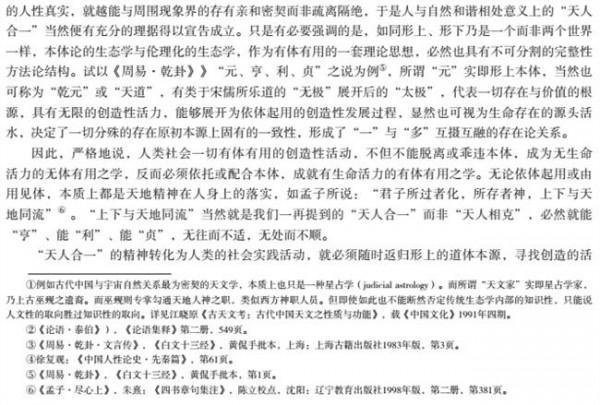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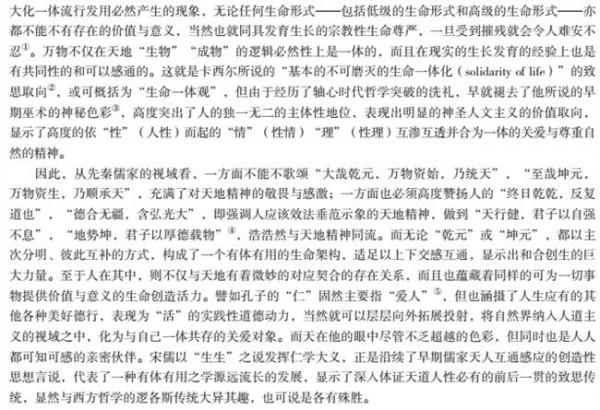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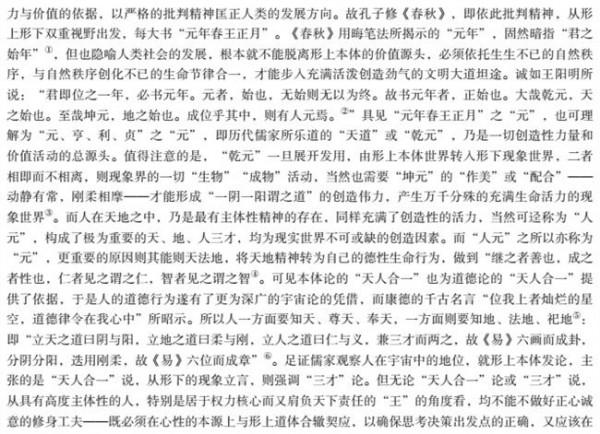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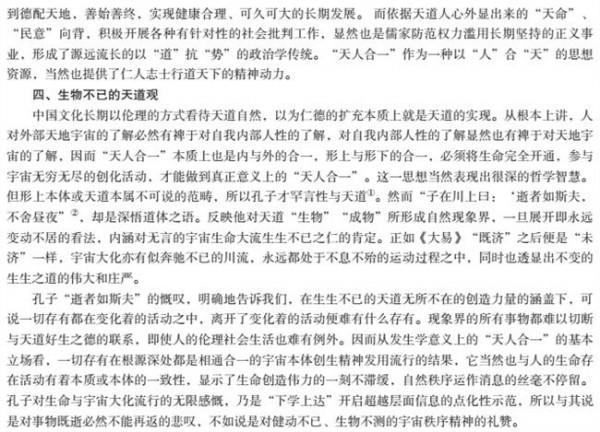








![王阳明心学智慧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全三册)[当当]](https://pic.bilezu.com/upload/c/75/c753a16bd3ff1be068f61ad7ff19b2f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