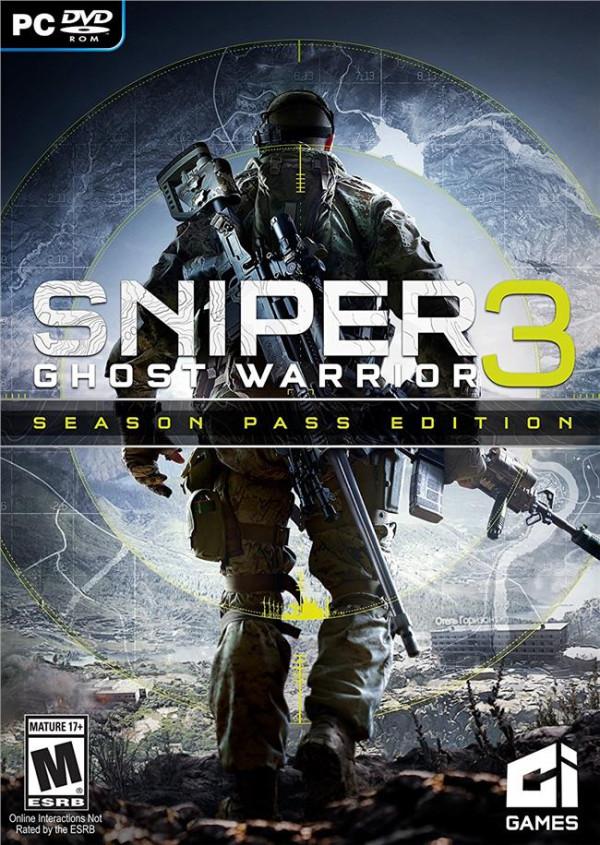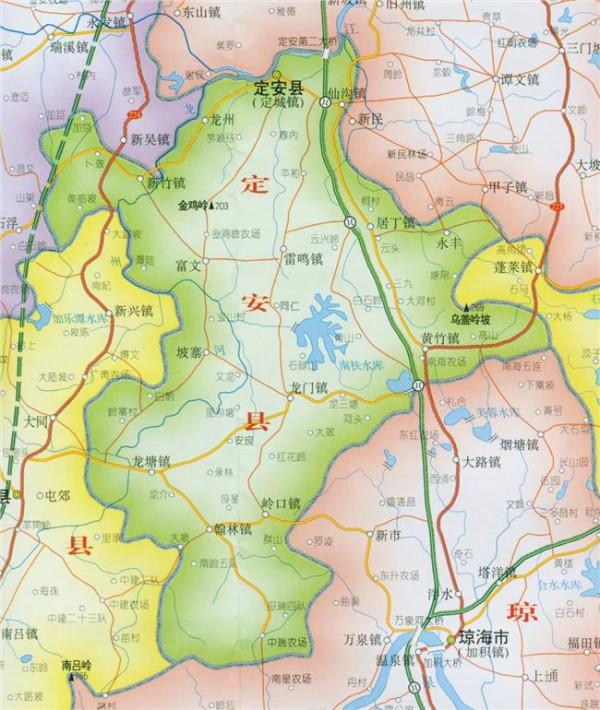台湾王文兴 快读等于未读台湾作家王文兴不慌不忙的50年
南方周末:你在大学里面给学生讲《玩具屋》有九讲,出了本讲义,这个短篇小说你讲了一个学期?
王文兴:是,几千字的一个很短的短篇,我讲了九堂课。我那个时候已经离开台大了,他们说回去再帮个忙。一个学期是18个礼拜,我能帮忙的就是每隔一个礼拜来一次,所以就是9个礼拜,最后选了这篇长度刚够的。我这样做,也是有一点跟学校习惯的办法相抵触的,要不是我年资比较高,恐怕也不可以。
有人会批评,说你过分,一个学期你在那里混时间,你在那里偷懒!年轻老师很怕被人说偷懒,所以尽量要多讲,一下子给学生几百页、几千页,你一个礼拜把几百页书看完上课,谁听呢?
南方周末:你在课堂上讲的时候学生有没有着急?
王文兴:没有,非常好,他们消化得了。很多话不是我讲,我先问他们,学生七嘴八舌讲,讲对了的,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可以采用,当然就是我本来的意思。可见人心都一样,他也有这个看法,所以这种课就变成一种参加的课了,他们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参加。
我这个方法老早就用了,我教书40年第一堂就这么用了。其实在台大的教书经验是很高兴的,学生兴致也很高,以后兴趣也不会改,文学的路就走上台了。最后一堂因为有个学生是报馆的主编,他喜欢记下来,所以他完整地把它记下来出版了。
南方周末:你自己有备教案吗?
王文兴:我要教什么起先当然是眉批过,就会带那本书在课堂上讲,圈点的地方是提醒我自己当时我是怎么解释这句话的。一句一句下来,每一句该解释的就解释,也请学生参加一起解释。一堂课英文常常一页不到,两三段,学生多寡无所谓,一百个人一样,二十个人也一样。
但很奇怪,一百个学生好像注定只有二十几个是真正的好学生,也有兴趣。如果只有二十几个学生的话,那他就是有兴趣才来报名,所以大概每一堂课就那么二十几个人在那儿举手要回答。我到现在还常常回头想念从前的老学生,现在都四五十岁了。现在很多都当系主任了。
南方周末:一部长篇小说你会怎么讲?
王文兴:这个是大困难,我到时候也要应付学校了,所以长篇就是跟他们讲好、讲明白,我是挑选重要的篇章、段落来讲。这难免有一点跳,我也只能够两边应付,我说我中间跳的你们尽量回去自己看。学生看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每次上课针对挑选出来的内容,他们很尽责任,都消化了,其他没有挑出来的就不知道了。
南方周末:你在大学讲授是有一个大纲的,哪些作品、哪些作家是一定要讲的吗?
王文兴:我那个课叫“小说选读”,跟文学史不太一样,我不太喜欢教文学史。选读有自由,而且没有一年的课是一样的,每一年选的课都不一样。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太难,都是大二、大三的学生,你要适合他的兴趣。我考虑会受学生欢迎的、他们能消化的东西,有长篇小说,也有短篇小说。
另外散文、诗、戏剧都在内,都用同样的办法。19世纪沙俄时候的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我都教过;欧洲的福楼拜、莫泊桑,这是我最喜欢的;法国作家中一直延续下来到20世纪的加缪、萨特、莫里亚克;德语的也教一些,托马斯·曼、卡夫卡、黑塞等;英美的很多,美国的海明威、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霍桑、福克纳,近的像厄普代克;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吉卜林、高尔斯华绥等。
这本身是一个乐趣,你喜欢的话再重复一遍也不觉得无聊。
南方周末:你在爱荷华大学读写作课,对于写作来说重要吗?
王文兴:回头来看无所谓,一个人真要写作的话完全在于自己,要学会写作要先学会读书,就这么简单。书要读错的话,走这条路写作也会错。什么是自己创作?无非也是一种模仿。人家做那么高,你看你能不能也跟着学一学,模仿他。
模仿不是抄袭,是对它的方向、它的能力的模仿。写作课是把它从自己私下的阅读跟创作的过程搬到教室里头去,所以你私下可以做到的话,不必到教室里去学。写作课也有好处,可以澄清很多问题。尤其看到同辈的作家身上有很多优点,要跟他有比较,对自己有鼓励的作用,也有警惕的作用。
我还是坚持,任何一个学写作的人自己带一本书,自己读一遍就够了,换着不同的书读绰绰有余。拿写作经验本身来讲,上不上写作课无关紧要,乃至于上不上大学都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