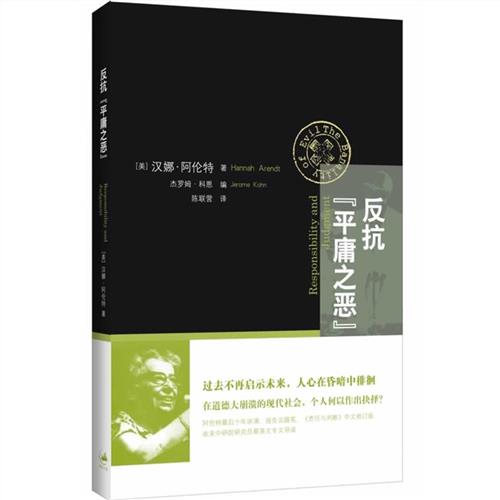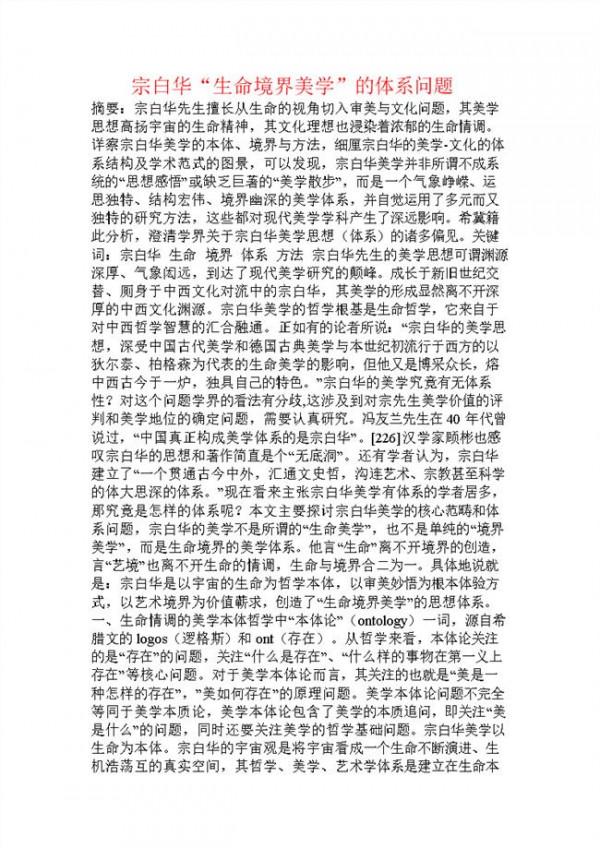阿伦特极权美学 熊平:极权主义美学及其原理
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
——电影《肖克申的救赎》独白
1918—1920年苏维埃国内战争期间,衣食住行等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全部由政府分配,被称作军事共产主义。在这期间,苏维埃政权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一次会议上,主管苏维埃政权粮食调配的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当时的粮食部长)突然饿晕在会场上。
一个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吨粮食权力的部长,却没有从中留下能一些粮食来填饱自己肚子,这个故事令所有人为之动容。列宁亲自给他写信,并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
“疗养食堂”后来逐步扩大到一般领导干部,再进一步扩大到领导干部的家属。革命胜利和经济好转后,“疗养食堂”全国遍地开花,并且由食品扩大到一切可能获得的资源,包括美色、权力和钱财。
论及极权主义,人们更多的是想到汉娜?阿伦特所著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更多地从意识形态对人性的影响这一点来剖析极权主义。如果从人性的本质出发,就会发现极权主义实际上是人性本质的一部分。从瞿鲁巴的美丽故事中我们可以窥视极权主义的起源。
极权主义实质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变异,是人性本质的一部分。如果还不理解,我们可以从红色高棉波尔布特身上寻找。我一直强调,对红色高棉的剖析,价值决不亚于对德国纳粹的剖析。
理想主义的本质是嗜血。这一点在红色高棉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有一次,我看到身边农村穷苦的人们,生了很多孩子,我心里就骂:你们养不活这些孩子,不能给这些孩子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生他们?你们不应该生!
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是个理想主义者。过后我就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有权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们生孩子?我凭什么剥夺穷人生孩子的权力?剥夺穷人的天伦之乐?这个事件对我影响重大。我就是波尔布特。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波尔布特。当我看到BBC关于红色高棉的纪录片,一对中国北京情侣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投奔柬埔寨,脸上洋溢着理想与希望的光辉时,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从心底里我就开始试图原谅他了。
与更加著名的切?格瓦拉相同,波尔布特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但他们都要拯救穷人于水深火热,建立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结果他们都是坑杀了穷人。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完美、标准、美好的社会,一切不美好的、在他们看来丑的、恶的,都应该消失。
规范的、有序的、外表看起来美好的、按照心中所想的、人人都美好幸福的,是他们的追求。理想主义如何变异为杀人机器?因为理想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美学,对美的过份追求,必异化,人由美学目的异化为美学手段,异化为构筑美的一种结构,成为一个器物。极权主义的美学,实际上就是理想主义美学。
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上最壮观最震撼的十万人团体操表演《阿里郎》。《阿里郎》是极权主义美学最通俗的注解。像《阿里郎》这样大型的团体操表演只有在极权体制下才有可能实现。十万人按照既定的控制,一起做机械的动作,成为美学的结构。
但《阿里郎》本身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如何在极权体制下异化为国家意志?如果你对这一点怀疑,你可以回想一下,近期发生在身边的事。为应付上级检查,下级政府用油漆把光秃秃的山坡涂成了绿色。
极权主义追求的是美,至少是视觉上的,或听觉上的。这两点,于国内在文革发挥到极致。于国外,历史上的极致是红色高棉时期,现在的极致是一天吃五顿饭的朝鲜儿童,我看到他们与主席拥抱的照片,泣不成声,不能自控。
极权有多无耻?极权的无耻没有底线。但极权无处不在。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极权都有可能随时存在。曾有报道,奥地利一位父亲,在地下室囚禁并性侵亲生女儿达24年之久,并与之生下7名子女。在法庭上,他辨称自己是一位好父亲。
在他所居住的小镇,事情没有暴露之前,他却是个有口皆碑的居家好男人!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只不过主角是一位公务员李浩,受害者是6名歌女,其中一名被囚女与另一名补囚女还因争风吃醋与李浩合伙杀死了对方,有被解救女子在警察调查时竟对李浩试图袒护。人一旦拥有无限权力,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按排他人的生活。每个人心中都有极权的欲念,追求完美的欲念。
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写道:“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指“生活的设置”,指的就是一种极权主义美学。
“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可以联想到波尔布特、斯大林、当今的朝鲜、现在死不肯放权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等。极权其实随处可见。但极权行使的理由,往往以人民的名义。
极权主义为何还能大行其道?无处不在?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极权主义都潜行存在。面对随处可见的极权主义,我们该如何防范?对理想主义保持警惕。警惕那些以人民的名义行不义的政权和人。柏拉图说:“不行不义于人,亦不被人行不义,这才是那些活在幸福中的人。
这两个条件,前者不难达到,最难的就是如何谋得权力以抵御他人的恶行”。“如何谋得权力以抵御他人的恶行”,但人一旦谋得权力,就不光是“以抵御他人的恶行”,而是还要“施展自己的善行”,设置他人的生活。
极权主义一开始并不是“恶”而是“善”,是“拯救”,最后上升为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并企图设置与按排所有人的生活。极权主义如何从最初的“善”走向最终的“恶”?它的心理动机和逻辑动力从何而来?
极权主义总是从最初的“善”走向最终的“恶”,从已经发生的极权主义社会来分析,就会发现它的心理动机和逻辑动力是它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美学系统。汉娜?阿伦特指出,当极权主义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极权统治才开始,通过对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国家意志形式来构筑他们想象中的“理想社会”。
为了达到这个“理想社会”,权力拥有者自身的身体与权力都可以随时牺牲。至于普通民众的生命,那更是如草芥。多年以来,瞿鲁巴的故事作为一个美丽的、光辉的典型而流传,而事实上从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极权主义的美学原理,那就是“时刻准备着为理想牺牲”。“牺牲自我”还是“牺牲他人”,成为“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的分水岭。
现在是后极权社会。完全的极权主义政权或仅存于朝鲜这样的国家。后极权政权借现代化大行其道,并在科技的进步下掩人耳目。已故思想大师李慎之在《哈维尔文集》序言中写道:“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完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
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
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请原谅我引用了李慎之先生这么一大段文字。而且是原封不动地引用。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他把“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当作极权政权运转的主要动力,特供体系越来越庞大。70年代后期,尽管苏联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但有研究发现,全国百分之70%的资源掌握在1.5%的人手里,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获得应有的改善,极权政权的合法性已彻底丧失,极权主义异化为后“极权主义”。
如果说,在极权社会,极权主义所作的“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后极权社会,后“极权主义”所作的“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则无法饶恕。极权主义有它的美学动力,有最初的“完美”与“善”,并且为了这种“完美”与“善”可以随时牺牲自己。
后“极权主义”则完全抛弃了极权主义的美学思想,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可以随时牺牲的对象,只有他人,是完完全全的、赤裸裸的罪行与暴力。我们的时代进步了吗?可能。
我们今年能享受到全球化琳琅满目的商品,可能更应该感谢的是科技而不是社会的进步。后极权政权通过科技的进步进行现代化化妆,而抛弃了最初的理想,违背了革命初期对民众许下的诺言,实行的是对普通民众进行赤裸裸的剥夺。
国家主义是后“极权主义”最后一块遮羞布。民族主义亦是如此。后极权政权要寻找执政的合法性,只剩下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内裤。因此,谎言与国家叙事、民族叙事,成为政权生活的主题。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
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李慎之认为,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因此,“真相”上升为“国家机密”,“常识”根据极权体制的不同需要成为“国家典型”或“罪行”,甚至某一外国人在国内正常的、合乎常识的行为,极权体制也可以动用国家宣传机器进行毫无廉耻的国家声讨,结果往往是自取其辱。
在这里,我并不是企图为极权主义招魂,因为极权主义是人性本质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极权主义者。而后“极权主义”,则是体制的“恶”,是完完全全的“恶”。“他们要我……”、“他们逼迫我……”、“他们……”,这个“他们”,追究起来,往往很虚无飘渺,最后只能上升到一个人,如波尔布特、斯大林或希特勒。“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被极权体制卷入的千千万万个“我”。
电影《肖克申的救赎》里有一名经典的独白:“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何洛阳警察在调查取证时,有被囚禁少女还试图对李浩进行袒护。不过话也说回来,类似被囚禁少女对李浩进行袒护的活,我们很多人经常在做,或一直在做。结果,“我们”就变成了我们口中的“他们”。
一旦拥有无限的权力,如何避免坠入极权主义的泥潭?不丹国王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从不丹第四代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开始,就开始策划国家权力从世袭君主制向议会民主制的转变,主动还政于民。不丹从君主制走向民主制,不是民众自下而上的要求,而是权力拥有者大力推动的结果。有的民众甚至不理解国王的做法,认为国王不管我们了,感到遭受到了国王的冷落。
到现在第五代不丹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2011年10月13日迎娶平民女子佩玛,轰动不丹和全世界,受到近700万不丹普通民众的衷心祝福。美学有美学原理,极权主义美学属于一种变态美学。不丹国王用实践证明,无限权力的拥有者也可以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同样是英美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但在卡扎菲的子女身上,看不到这种返回正确轨道的任何希望。可见知识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贪欲。结果是,一个受万民祝福,一个已身首异处。
该结束了。一切都该结束了,包括我现在写的这些文字。如果你洞察人性和时代的黑暗而保持沉默,你就会被这黑暗熔化,成为“他们”的一部分,陷入更大的黑暗。我一直都坚信哈维尔的这段话:“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记住,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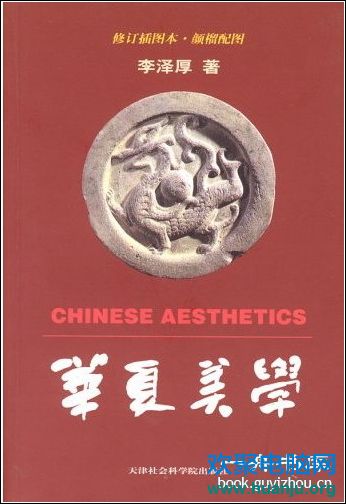



![>1984孙仲旭 1984(奥威尔传世杰作 反极权经典作品 孙仲旭译本)[当当]](https://pic.bilezu.com/upload/3/a1/3a1cf34f35a9f842164a17234fb50d3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