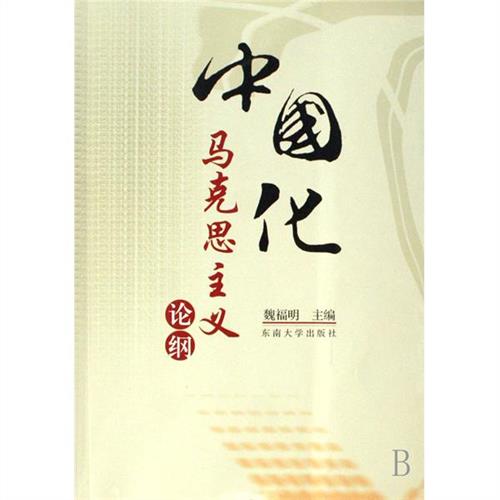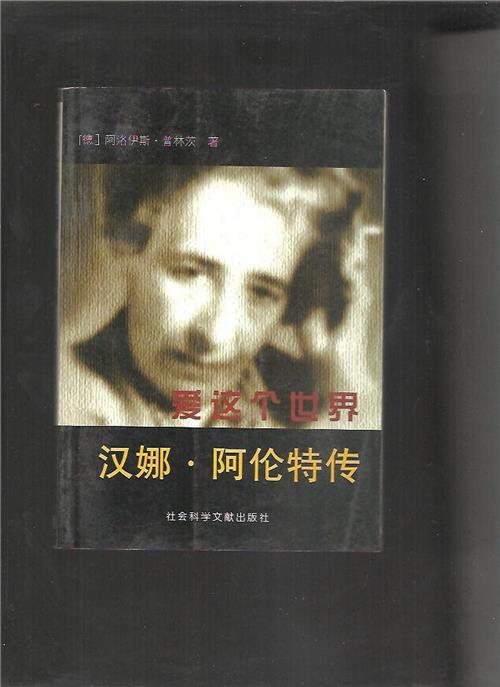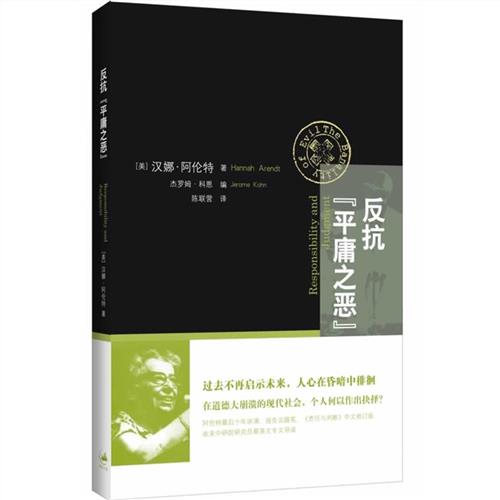阿伦特艾希曼 汉娜·阿伦特:为纳粹恶魔艾希曼辩护
在第三帝国的嗜血群魔中,阿道夫·艾希曼是一个地位不很显赫,但却罪恶滔天的人。作为纳粹秘密警察犹太人处处长,据目击者在纽伦堡纳粹审判法庭供称,经他手就杀了五六百万犹太人。其凶狠残忍的形象,足以使人不寒而栗。1960 年 6 月 14 日,耶路撒冷以色列专设的犹太法庭对阿道夫·艾希曼进行了审判。杰出的犹太法学家汉娜·阿伦特受托为此专程从哈佛去耶路撒u冷为艾希 曼作法庭辩护。
对于审判的法律辩护,阿伦特不愿重走纽伦堡审判的老路。她的责任不是为艾希曼作无罪辩护,而是寻找法律公平与正义的可能性,她不是一个单纯的律师。当然,在耶路撒冷,作为犹太人,为艾希曼作无罪辩护,要承担什么后果,她也是清楚的,她不愿冒这个风险。
阿伦特辩护的中心问题是艾希曼该以什么名义受审,并陈述艾希曼犯罪实质。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法学家,她首先要提出的是问题,而不是路人皆知的结论。审判事关正义,她提出的也正是正义的问题。
阿伦特认为,"审判的目的应该是表现正义,而不是别的。"但这次审判却只表现了其它的东西:痛苦、怯懦、背叛、耻辱,也许尤其是复仇。没有约束的人是野兽,是卢梭和弗洛依德所谓文明秩序或文明前的自然人,根源于良心(或者按基督教的观点,根源于原罪)的道德没有法律的外部力量不足以担负约束人的任务。
因此,审判的正义在最初就有一个可怕的、报复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认为它是非公平的。
其次,正义的概念是根源于自然法,它要求人为了破坏道德秩序本身而受惩罚。尽管如此,正义本身应该是一个普遍的标准。艾希曼应为了他的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受审。"艾希曼是以反人类罪,还是反犹太人罪而受审,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
没有必要提出这种区别。纳粹的罪恶如此巨大,艾希曼在其中的共谋责任,无论大小,都十分清楚。"纪德·哈瑟尔声辩道。他试图把阿伦特引导至"共谋责任"问题上来,继续一场纽伦堡式的辩论。
阿伦特的陈述,很像一场哲学答辩:
"为什么要提出像艾希曼应为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而受审判这样的问题?这里涉及到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和世界概念的问题。在地方性认同人类的普遍标准之间,始终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难解的紧张。尤其是我们犹太民族,它的文化和历史遭遇都使它偏重于地方认同。而忽视了有超越种族与国家之上的单一的普遍标准存在。虽然犹太人复仇的呐喊是可理解的,在这个事件中,如果艾希曼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被直接击毙——一个直接的复仇行动,正义可能被更好地满足了。此案审判的合理性不是因为反犹太人罪,而是因为反人类本性罪。着眼点不仅是受害者,还有行为本身。"让阿伦特担心的不仅是审判的名义问题,而更重要的是隐藏在审判背后的实际究竟是什么?"
从阿伦特对艾希曼所犯罪性质的分析不难看出,她认为以色列人并不理解艾希曼所犯罪行独特的新性质,这表现在他们将艾克曼一案看作是调查反犹太人罪行。对以色列人来说,纳粹是在反犹主义传统中所犯的长长的一系列暴行之一。而在阿伦特看来,纳粹的罪行,理性地屠杀整个种族群,是人类历史上新一种可怕的可能性的开始。但以色列人一开始就试图将艾希曼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象征来审判。在审判前以色列总理本一古里安就说:"在被告席上受到历史审判的不是一个个人,不只是纳粹政权,而是贯穿历史的反犹主义。
阿伦特敏锐地发现了藏在这个目的后面的几个动机,向世界表明犹太人的命运,以俘获世界各国的良心作为保卫以色列国家的一种手段;向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表明作为少数族群生活的悲惨;向以色列人民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对于恢复犹太英雄主义的有效性。
这些动机显然是出于以色列国家生存的考虑,与正义并无关系。以色列领导人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集团,他们对于大国的理想主义几乎不抱幻想。生存是他们的第一原则。
为了生存,他们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和制造挑衅,而无视正义的原则。拉封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艾希曼受审判前些年,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特务放火烧了开罗的美国新闻处大楼,以栽赃于埃及人,在美国煸起反纳塞尔情绪。
当阴谋败露后,以色列情报机构伪造文书,证明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封批准了这次行动,拉封被迫辞职,虽然后来他不顾本一古里安的反对证明自己无罪,但他的政治生涯就此断送。以色列书报检查官有一年多不许讨论此事,全部细节至今仍不清楚。
对于一个心灵上还留着德雷福斯事件伤疤的民族来说,拉封事件令人痛苦地提出了道德与政治权宜之计的关系问题。为了政治的权宜之计践踏正义的原则可以原谅,那么正义最终是否还能存在?在阿伦特看来,以色列用一个普遍要求(正义)来掩盖其地方性目的,说明它的动机是"意识形态"的。
她的结论是:政治利益而不是正义的目的,构成了以色列政府的审判行为。正是这种对以色列政府的诛心之论,激起了以色列人愤怒的风暴。"任何对正义单一的强调都必然要将法律与道德分开;它反而把后者归到人与人之间的私人领域,而给法律一种形式的性质。
"阿伦特看到,在耶路撒冷的这场审判常常是一种"审判表演",甚至时常是一场 "群众大会",而不是正义统治的法庭。"从法律上讲,一个人必须不是因为他是什么或为了他代表什么而受审,而是为了他所做的受审,并只能是这样。
"阿伦特发现,这个案子是建立在犹太人遭受的苦难上,而不是艾希曼所做的事情上,用检查官哈瑟尔说,这种区分是不重要的。因此有五十多个证人的证词只说了自己的苦难,却与艾希曼的特殊行为无关。
审判的气氛就是证人一个接一个试图引起听众对与被告的罪行没有任何联系的事的注意。"正义要求被告被起诉、辩护和判决,所有其它似乎是更重要的问题……应该被暂时搁置。"
因为"审判的只是(艾希曼的)行为,而不是犹太人的痛苦,不是德国人民或人类,甚至也不是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法律之所以不同于纯粹的报复,就因为它有道德的象征意义。"阿伦特进一步陈述:"艾希曼是什么象征?反犹主义的象征,当然。
纳粹主义的象征,的确。这都不成问题。但什么是纳粹主义?什么是这种特殊的反犹主义?某种独特畸变的东西吗?德国民族特性中的一个因素,因此就意味着全体德国人都有罪?非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某一方面,因此就是基督教历史特有的吗?是人类经常发作的攻击性疾病?"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艾希曼似乎是所有这一切。
阿伦特是以她自己的方式把艾克曼作为一个象征的。"他是一个个人,阿道夫·卡尔·艾希曼的儿子;艾希曼只是一个‘普通人’,既不是‘堕落的人也不是施虐狂’,只是‘极度和可怕地正常’。
这个案子引出的问题是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服从罪恶?"对阿伦特来说,虽然由于正义的法则此案应该只处理个人,但艾希曼历史地是一种"新型罪犯",他颠覆了近代司法系统中同行的假定:做错事的企图对于犯罪是必要的,他不能用以色列人试图运用的通行的成文法来审判。
没有做错事的企图并不因为艾希曼是一个不同的法律。但阿伦特关心的还不是审判的方法,而是这个象征的性质。她坚持艾希曼不是像以色列检查官所讲的是一个"堕落的施虐狂",一个"魔鬼",而是一个普通人。但一个普通人如何犯下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这才是阿伦特要迫索的问题。
阿伦特指出,希特勒一次在论修辞学的手册上写道,群众示威"必须给小人物的灵魂烙上自豪的信念,虽然他是一个小人物,但却是一条巨龙的一部分。"艾希曼在纳粹这台机器上既不是齿轮也不是螺丝钉,这种形象是太勉强了,不能理解人们对那种能让他们发泄他们对于重要地位和无限权力的饥渴与妄想的形势的反应。艾希曼在纳粹运动中看到了他的机会并敏捷地把握住了这些机会。他有一个领袖,一种合法性(纳粹的种族优越性思想)和一个允许他表现出他虚夸的巨龙的骄傲。但一个人怎么能如此积极地投身屠杀并那么容易就找到良心的宽慰和平静?他怎么对付由血淋淋的屠杀产生的可怕情感?
对原始人来说,始终有共同的涤罪,但现代人需要巧妙的欺骗。艾希曼的纳粹通过使用"语言规则"来使他们与事件保持距离。例如,在希特勒的第一号战争命令中,"杀戮"一词便被"给予仁慈的死亡"所代替。
在纳粹的 "客观"语言中,集中营用 "经济学"术语来讨论,屠杀是一个 "医学问题"。所有官方通信都遵守这种"语言规则"。阿伦特指出,"很难在文件中找到像‘灭绝’、‘消灭’或‘杀掉’这样大胆的词。
给杀戮规定的代名词是‘最终解决’、‘疏散’和‘特殊处理’。
驱逐出境被称为‘换住地’。但仅仅伪装是不够的。普通人在从事这种触动良心的行为时必须感到一种更高的目的,诸如‘决定命运的战斗’(艾希曼称之为‘中肯话’)这样的口号和警句的作用,就是用从事某种伟大事业的责任来淹没个人的感觉。
"打动这些已成为刽子手的人心的只是正在从事某种历史性的、伟大的、独一无二的事情("一个两千年发生一次的伟大任务),因此它一定是难以承受的。
阿伦待所有这些论证的要点是:像艾希曼这样的普通人,很容易成为一个将全部人口作为多余消灭的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以蒙古游牧部落的方式(那里至少是原始的功利主义在起作用),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由于世俗意识形态无意识冲动的计划。没有任何约束,对于追求观念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个制度就是极权主义制度。
谈到极权主义,阿伦特显得特别激动,这位哈佛大学的自由主义学者,把法庭变成了一个讲演厅:"极权主义不只是破坏私生活,用国家摧毁社会,这可说是决不会完全可能的,很快就会失败,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创造——‘种旅’或‘历史’通过元首或党来说话,它是更高的法律的统治。
老式专制主义是个人专横意志,除了优势力量或传统外没有合法性。
极权主义运动的力量在于创造一种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仅凌驾于普通关于谎言、欺骗和偷窃的道德,而且把对于屠杀的顾忌视为微不足道的资产阶级情感。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对其目的的服从,既不同于军事化的政权,也不同于以前的专制主义。
基督教的罪恶感迫使人们把有罪感内化为良心,用自律来代替外在约束;但极权主义在其追随者中灌输了一种免罪许可,它用更高目的来代替良心。虽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期是极权主义的因为没有某种强烈的忠诚、某个战时的敌人或通过恐怖产生的服从,人的多种多样的欲望是不可能被固定为一个目的的。
但由于现代社会集中权力和国家强制行为提纵多数人的结构性倾 向,极权主义的潜在性将会是一个不时来拜访的幽灵。"
阿伦特最后陈述:"纳粹的罪行不是历史的局部与偶然。史无前例的东西一旦出现,就可以成为未来的先例,所有涉及‘反人类罪’的审判都应该根据一个仍是一种理想’的标准来判决。在大规模屠杀已变为普遍时,法庭再将艾希曼一案作为反犹太人的象征来审判,是以地方的标准未处理昔遍的问题,完全误导甚至掩盖了纳粹罪行对于这个时代的真正意义。何况,如果只承认局部标准而无视普遍标准,任何罪行都可找到堂皇的借口。"
阿伦特清楚,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绑架艾希曼就公然践踏了国际法。这样,将来某个非洲国家就可以去美国绑架一个种旅隔离主义者,然后将他弄回加纳或几内亚审判他的反黑人罪。果真如此,任何正义的事业都将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普遍的原则的标准,人类面临的那些普遍而严重的问题就无法得到深入的认识和解决。
阿伦特的法庭辩护,对法官没能产生任何法律意义,他们把她视为一个学者的思辩。不过,阿伦特也十分清楚,她的法庭辩护是以色列政府需要的一种"表演"。以色列政府需要煽动一种复杂的历史感情。可以把犹太人过去几十年在纳粹铁蹄下所遭受的迫害和屠杀浓缩成一句话,一个结论——复仇!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才能真正深切体味"复仇"这两个字的真正含意。1962 年 5 月底——事隔两年之后,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处死刑。一场曾缠绕了千千万万犹太人的恶梦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