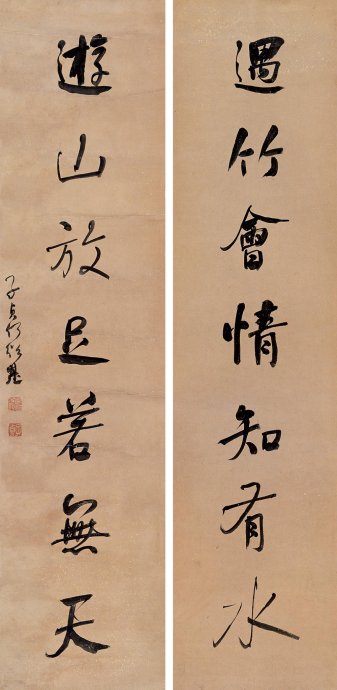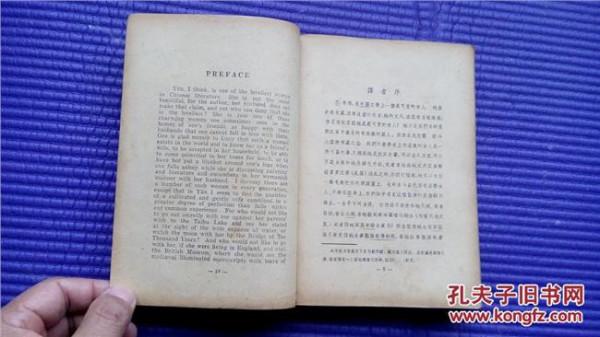董乐山的观点 翻译的共识——读董乐山《翻译的甘苦》
谍战题材总是容易引人入胜,所以看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版本,译者是董乐山。在未看之前已听闻该书人物情节达到非一般的复杂程度,所以对译者又多几分期待,便顺便把他写的《翻译的甘苦》也一并读一读。
这本甘苦谈类似工作随笔,读起来很亲切,有诸多思考,即便是不做翻译也深有同感;如果懂一点翻译,更是能体会书中所提的“甘苦”。
文化差异是翻译的根本困难,也是翻译力图要为读者消弭的理解障碍。做到这点,译者必须对原作和译本持不同语言的国家的文化都非常熟悉。文化一词包罗万象,所指代的事物又不断发展,由此可见译者的认知确实是“无涯”的。就像要砌一堵没有尽头的墙,一块砖一块砖地添加,有些太老旧残缺的砖要换掉,有些砌坏要修补的,有新材料造成的砖要加上或更替,是无止境的功夫。
译名
书中第一篇引起强烈同感的是“译名改革刍议”,说的是其他国家人名翻译成中文的可读性太差。这点从我们小时候读国外原著译本开始就深有体会:记得简爱,却记不住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记得雾都孤儿的作者是狄更斯,却记不住书中主角的全名是奥立弗?退斯特。
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首先是因为译名字数太多,字符太长。中国人习惯的的人名是2个到4个字,超出这个范围便是考验记忆力。偏偏外国人名“从本名、父名到姓,往往长长一连串,佶屈聱牙,读也读不顺口”。
其次译名中的字与我们认知中用于做名字的字相差太多,多数是音译,没有意译,也因此没有可以记住的意义。一本小说中出现的人名少则十几个,多则上百个,教读者如何记得住?老实说我自己有时连区分都出现困难,因为这个原因最终被束之高阁的书也不少。
曾经看过一本台湾翻译的小说,书名和内容记忆都很模糊了,只觉得有趣的是全部外国人名都有类似中文的名字,特别是姓氏,比如林赛罗(只是比喻不是真实书中出现的名字),一下就记住了,起码从姓氏就可以区分不同的人名,而从人名又确实看得出来是外国人。
又如台湾翻译的《悲惨世界》主角叫尚万近,比起国内译的冉阿让,更像我们熟悉的名字。没有研究过台湾的翻译是否确实有这个原则,但从总统译名可以看出确有译成中国人熟悉的姓氏的做法:肯尼迪-甘廼迪,约翰逊-詹森,尼克松-尼克森,里根-雷根(作者后来竟然提到即使按照中国的音译规则是应该译成“雷根”,里根是以讹传讹,又不肯改正,所以变成约定俗成的,悲哉),布什-布希(香港译布殊),克林顿-柯林顿,奥巴马-欧巴马。
个人认为台湾译法挺接地气的。
作者是由杨绛写的一篇序开头,提及杨先生也是认为翻译的名字太“佶屈聱牙”,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应简缩,但翻译大家傅雷不同意;作者后又提及对此鲁迅也是不同意的。可见翻译界对此也有争议。
作者是同意杨绛的。他举了些例子,比如罗斯福Roosevelt,如果按现在新华社拟的译名手册原则,应该译为“罗斯弗尔特”,但大家肯定更接受罗斯福;又如外国人译《红楼梦》,也没有按照音译,都是意译“鸳鸯”、“熙凤”,又自然又有意思。
对于现在的音译缺点,作者指出的其中一点是“外语名字中有些辅音是轻读,一字不漏地译成汉字,与译名中其他几个汉字连起来读,尤其是由广播员字正音圆、有腔有调地读起来,与原来发音就走样了”。不过他也认为这点如果没有文字改革是无法解决的。作为广东学生的我,对其他普通话地区学生把轻音发成音节的读法简直无法容忍;恐怕这只是少数人的洁癖,因为听说外国人听起来毫无压力。
关于译名的无奈林林总总,所以作者写到最后只是希望可以把译名缩减一下字数,简化成只把重读的音节译出。这样做估计也会引起混乱,但如果符合大多数人需要,又何不尝试改革呢。
正名
为一个新名词做定译,也是十分谨慎又充满挑战的。像“导弹”(guidedmissile),50年代初期是译为“定向飞弹”,后又译作“导向飞弹”,最后才定译为简洁明白的“导弹”。所以生出感叹“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看到这里,不禁认为这个“定译”与古人作诗时“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异曲同工,都是要求所选的字词高度符合原意,而又精炼简明。原来,翻译和作诗的乐趣都在于斟词酌句。
勘误
翻译错误几乎不可避免,每个人知识结构不同,绝无完美。但作者认为属于常识性错误的,理应自律纠正,以免出现笑话。选几个印象比较深的记录一下。
1、与历史知识有关
中国有些地名的英文名由于历史原因与现在应用的汉语拼音不同,比如卢沟桥不叫Lugouqiao,而叫MarcoPoloBridge。而Mukden是当时奉天(现沈阳)的满语名称的英译,“九一八事变”再英文历史书中叫“MukdenIncident”。PortArthur是旅顺口,现代电视剧译成“亚瑟港”则是笑话了。
2、与种族歧视有关
在美国警匪片中,经常有出现罪案发生后,警察局长描述嫌疑犯是“非高加索人种”(Non-Caucasian)。翻译有时译为“非高加索人”,作者解释由于在高加索地区,各民族有自己的称呼,如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等,无人会称“高加索人”,所以这样译是错误的。
如果译为“非高加索人种”,就比较好理解。高加索人种一般指白种人,非高加索人种一般指黑人,为了避种族歧视之嫌,不能直接称之为黑人,所以只能说“非高加索人种”。在国内好像没有关于种族歧视的词汇,“黑人”一词的使用比较普遍,有外国人见到我们竟然有“黑人牙膏”大为吃惊。所以在这个语境下,是否可以直接译为黑人比非高加索人更简明易懂?
3、严谨性
有些翻译内容,读者是外行,译者如果不严谨,读者也看不出来,大概读者认为自己见识浅陋,或学习了一个有误的内容而又不自知。这样说起来,译者肩负的重任确实不可轻视,必须严谨对待。
作者专门写了一篇自己的翻译错误的来龙去脉,可见译者也必须心胸开阔,接受批评才能走得更远。
那是作者翻译《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序言中,对于钱币的翻译,被一位哲学家发现有误。原著的钱是“一迈那”,迈那是希腊货币,作者估计为了让读者更明白,译成“一块钱”。哲学家指出按照货币的换算,当时一迈那可以买一个奴隶或等于一个人一年生活的费用,不是小数。原著故意没有解释一迈那的实际价值,是有意让人以为价值很低,如果译成“一块钱”就刚好中了圈套。
确实任何时候对自己不懂的知识都不能掉以轻心。
4、名著书名也有错误?
有一篇名为“积习难改译地名”,作者主要对外国地名汉译的知错不改颇为无奈。
BeverlyHills国内译为比弗利山庄(港译比华利山)。它是洛杉矶的一条街道名,好莱坞明星都在这条大道上购置别墅。作者认为译为“山庄”是误导。
因为上面的比弗利山庄,就有了“国会山庄”。CapitolHill是称呼国会所在的一块隆起的高地,冠以“山庄”也易引起误会。我查了一下,现在CapitolHill几乎用于指代“国会”一词,而且作为旅游景点也译成“国会山”,像作者说译成“山庄”的已经很少了。
作者指出“山庄”一词,还用在另一种高地的地名上,以英国小说WutheringHeights《呼啸山庄》为始。作者认为翻译成山庄是牵强附会的,但也并无给出认为正确的译法。毕竟,文学作品特别是标题意译空间很大,如果译成“呼啸高地”,大概作者也不能满意吧。
《翻译的甘苦》里面的文章,有署时间的都是九十年代的作品,离现今确实有一些年头了。但是里面提到的错误和不严谨,未必今天就不会发生,也许发生的几率更高;里面的思考,未决的疑问,到今天依然很多未能进行改革或解决;里面作为译者的态度和坚持,我相信应该成为每一代译者的态度和坚持。历史总是高度地重演,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治学之道却是永恒的追求。